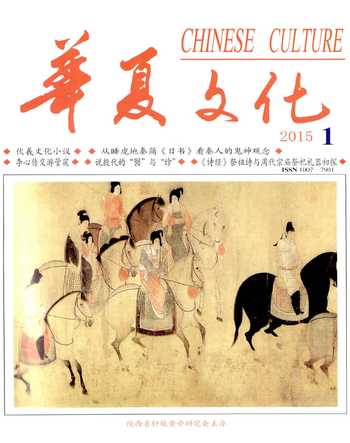從“自然之性”到“道德之性”
張志宏
對于心性道德倫理的探討是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中一個極其重要的構成部分。幾千年來,醉心于此的思想家不汁其數,文章著述更是汗牛充棟、然而學術研究不像教學,貴在創新而非因循教化李友廣博士新近出版的《先秦儒家人性論的演變——以郭店儒簡為考察重點》(陜兩人民出版社,2014年。 以下簡稱《先秦儒家人性論的演變》,不冉一一注叫)一書,洋洋灑灑二十二萬余言,就從新的材料、新的視角、新的思路和新的研究方法川個層面對先秦儒家的人性論進行了深入探討和系統闡述,提出了渚多頗有見地的論點。
一、新的材料
李友廣博十《先秦儒家人性論的演變》一書最人的特色,即基于“郭店簡”這一出土文獻來討淪先秦儒家的人性問題。
郭店簡白上世紀九十年代出土以來,即引起學術界的強烈關注。包括考占學家、古文字學家以及相關的哲學史、思想史研究專家都迅速地投入到對其的整理、考證與研究當中。李友廣博士正是在這一學術背景下.對新出土文獻進行研究的,其著作《先秦儒家人件論的演變》便是其集中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郭店簡雖已公布于世二十年左右,但相對于綿延兒千年的傳統思想義化研究而言,無疑是屬于最新材料。而對之二十年的研究,也當然只是剛剛起步。其804枚竹簡(其中有字簡730枚)。13000楚國漢字,值得當代學者細細體味,而非淺嘗輒止。
二、新的視角
在《先秦儒家人性論的演變——以郭店儒簡為考察重點》一書中,李友廣博士通過對生、眚、性的考辨發現,從甲文“牛”到金義“眚”、再到“性”的字形字體之演變實際上正彰顯了人之主體性與人文主義思潮于春秋晚期、及至整個戰時期的不斷推進。因而,可以說,從牛.到眚、冉到一性的演變,實際上亦彰顯了人之目光由天國一步步下移塵世,進而漸漸傾注于自己內心的演進歷程。這從由生到眚“目”部(其甲骨文字形即為眼狀,實為人目)的增加,再由眚到性“心”部的增加即可明察。因而,對于先秦儒家人性論演變的研究,李友廣博士除了有意增強“史”的意識以外,還著力依據生、眚、性古文字形字體演變的邏輯主線進行刪照。
三、新的思路
在郭店簡等出土材料面世以前,學術界對于孔孟之間這段時期的儒學歷史(尤其是學術傳承及思想理論的演變方面)一直以來都難以說清,更無法對儒家作品在先秦時期的經典化進程進行細致的考察,大多只能采取避而不談的處理方式 同樣,在早期儒家人性論研究方面,以往由于相關義獻材料不足,我們的研究成果所呈現出來的客觀性與綜合性多少有所缺失,對其研究往往以孔、孟、荀為主,而且對同出于儒家、同持有儒家立場的孟、荀二人的人性論為何差異如此之大并沒有給出合理、令人信服的理由與論證。而上博簡、郭店簡的面世,為這些問題的進一步解決,提供了文獻依據和歷史契機。基于此,李友廣博士以郭店簡為文本依據,并由此來審視孔子和孟、荀的人性論思想,進而以早期儒家的人性論為研究視角,對孕育了早期儒家人性思想的人文資源及人性思想演進的歷史過程作出考察。而且在考察的過程中,李友廣博士并不是先人為主的為早期儒家人性論人為的預設一個性善或性惡的共同倫理背景,而是回到當時的歷史情境,力圖將郭店簡還原到早期儒家人性論思想發展、演變的序列當中,從而希冀建構起早期儒家人性論的整體譜系來。當然,誠如作者在書中所言,由于工作量大,任務艱巨,恐怕憑作者一人、一時難以實現,尚需學界同仁繼續探究,共同完成。
四、新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由于李友廣博士是以先秦儒家人性論的演變過程為研究對象,目的在于借助郭店簡來復原儒家人性論在先秦這一歷史階段演變的序列與進程,同時又需要考察儒家人性論思想在郭店簡階段所呈現的內容、樣態與特征,故而勢必繞不開對關涉儒家人性論思想的核心范疇與命題(諸如生、眚、心、志;“眚自命出,命自天降”等)作出必要的考察與辨析,所以李友廣博士首先重點運用文字考辨的傳統研究方法。在此基礎之上,守持文字考辨與義理闡發并重的學術態度,盡量避免出現以文字討論代替思想討論的弊病,從而試圖把文字的討論放在思想、精神的高度來有效地展開。
另外,李友廣博士一方面注重堅持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方法,既注重考察儒家人性論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與歷史條件,使主觀的邏輯認識以客觀的歷史為基礎和依憑,另一方面又不止于對客觀歷史條件與社會特征的考察,而是試圖探索基于歷史之上的邏輯思維規律,以嚴密的邏輯、前后一貫的形式對歷史進行理論形態式的省思。更為重要的是,李友廣博士秉持了“跳出儒家道統論,回到歷史情境中去考察”的學術立場。在郭店簡等地下材料出土以前,由于深受宋明理學家及港臺新儒家的影響,國內學界部分學者在談論儒家人性論的時候往往奉儒家道統論為圭臬,對思孟一系所開創的性善論大為推崇,而對“即生言性”的自然人性論及萄子的性論思想重視不夠。因而,在儒家道統論、道德形上學的影響下,人們容易先人為主,在沒有充分考察文獻材料的前提下,往往預先在頭腦中設立一個主觀色彩過于明顯的思維框架,從而可能會得出不太可靠的結論。有鑒于此,李友廣博士認為,在考察先秦重要儒家人物人性論思想的時候,應該盡量不在人物辯論及思想展開等方面人為地預設一個人性或善或惡的邏輯前提與話語背景,而是從具體文本出發來考察儒家人性論思想產生的思想資源與歷史情境,并以此思路考察郭店簡所代表的孔門七十子及再傳弟子與孟子、荀子的關系,考察自然人性論與郭店簡及孟荀的學術關聯問題等等。應當說,李友廣博士的這種思路是合理的,也在其著作中得到了較為充分的體現。
概言之,《先秦儒家人性淪的演變》一書比較好地體現了李友廣博士的研究目標與學術思路:以郭店簡為考察重點,并以“史”的意識與文字考辨的研究方法來對先秦儒家人性論的演變過程進行梳理與廓清,試圖突破以往學界在先秦儒家人性論探討方面貫之以善惡界定的思維范式,從而向先秦儒家人性論的整體風貌不斷趨近。
正如書中所言,幾千年來,尤其是宋明以降,對儒家人性論的研究雖然成果頗豐,然而研究對象大多集中于孔孟荀及其之后的思想家,而對孔孟荀之前的人性論及相應的文獻資源重視不夠;并且在研究中過多以“善惡”的思維范式來討論人性,而對儒家人性論的演變過程及其相應學理缺少應有的重視與系統研究,對于“即生言性”的思維傳統與理論視角的關注和研究更是不夠。在此學術研究背景之下,李友廣博士此專著的出版,無疑豐富了儒家人性論的研究向度。而且,作為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本科畢業生,又有詩歌散文之好的性情青年,李友廣博士優美的文筆和深厚的傳統文化情懷在此書中也有著充分的體現。
當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研究領域的青年學者,李友廣博士此書中的諸多論點與主張在經過時間的考驗之前,尚屬于一家之言,有些觀點的提出也值得商榷。但這也恰恰正是學術研究的真諦之所在——思想正是在不斷的立論與質疑的循環中得以發展的,正所謂“一枝獨秀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