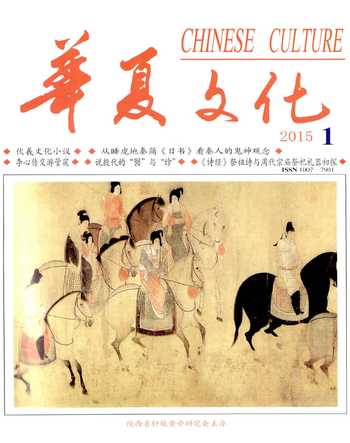從睡虎地秦簡《日書》看秦人的鬼神觀念
魏超
睡虎地秦簡《日書》出土于1975年,作為流行于戰(zhàn)國秦漢時期中下層民眾中間的一部用于選擇時日、趨吉避兇的術(shù)數(shù)類書籍,其涉及的內(nèi)容非常豐富,幾乎囊括了民間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被譽(yù)為反映秦國及秦代社會的一面鏡子(《日書》研讀班《日書:秦國社會的一面鏡子》,《義博》,1988年第5期)。秦人地處西戎,相對于東方六圍,秦人的思想特征更為鮮明。但是限于文獻(xiàn)記載不足,秦人的鬼神觀念歷來是研究的薄弱環(huán)節(jié),《日書》的出土,為我們研究秦人的社會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本文擬通過對秦人信仰中的神、鬼進(jìn)行梳理和比較,并進(jìn)一步分析其鬼神觀念之特征。需說明的是,本文依據(jù)的版本是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睡虎地秦墓竹簡》精裝本。
一、從《日書》中看秦人神的觀念
從《日書》巾可以看出,秦人觀念中的神已經(jīng)形成龐大的規(guī)模,《日書》巾云: “羊日、百事順成、邦郡得年,小夫四成;以蔡(祭)上下群神,鄉(xiāng)(饗)之乃盈志。”(三正貳)可見,在秦人的觀念巾,神靈的構(gòu)成不僅有天上的諸神,還包括地下的諸多神靈。
天神。秦人的天神系統(tǒng)中包括“帝”和星宿神《日書》提及上帝的簡文有:“毋以子卜筮害于上皇”,(三正貳)“鬼恒從人女,與居,曰:‘上帝子下游。”(三八背叁)等等。“上帝”一詞義見于《史記·封禪書》:“秦文公東獵淠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滅下屬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徽,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疇,用三牲郊祭白帝焉”除了上帝之外,秦人的天神系統(tǒng)還有五色帝。如《日書》:“凡是日赤啻恒以開臨卜.民而降其英(殃),不可具百事。” (一二八正)赤帝即五色帝之一,見于《封禪書》中:“秦靈公作吳陽上疇,祭黃帝;作卜畸,祭炎帝”、考察秦人對帝的祭祀,可以發(fā)現(xiàn)。秦人的信仰體系中,“帝”并不是一個至高無上的主宰,也沒有居于眾神的核心和領(lǐng)導(dǎo)地位 秦人“帝”的信仰是從周人那里搬過來的,似是“西周時期周人的上帝居于其他諸類神靈之首。與諸神結(jié)成有秩序的等次關(guān)系與統(tǒng)屬關(guān)系,并對諸神仃使令的權(quán)力。按照現(xiàn)代宗教學(xué)對至上神的定義,周人的上帝應(yīng)當(dāng)是他們的至上神”(朱風(fēng)瀚《商周時期的天神崇拜》,《中國社會科學(xué)》,1993年第4期)。秦人將“帝”搬過來后,卻把他分成了“白帝”、“青帝”、“炎帝”、“黃帝”等,而且四帝均沒有明確的統(tǒng)屬關(guān)系 秦文公接受史敦的建議祭祀上帝,卻作鄜峙,祭祀的是白帝。可見,在秦人的信仰中,上帝應(yīng)當(dāng)是四色帝的泛稱,真正作為至上神的“上帝”并未出現(xiàn)。
除了“帝”之外,秦人天神系統(tǒng)中還有星宿神,具體有角、亢、抵(氐)、房、心、尾、箕、斗、牽牛、須女、虛、危、營室、東辟、奎、婁、胃、卯、畢、觜、參、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相對于“帝”而言,二十八星宿顯然跟秦人的日常生活關(guān)系更為密切,例如“牽牛,可祠及行,吉。不可殺牛,以結(jié)者,不擇。以人,老一。生子,為大犬 ”(七六正壹)可見,人們的出行、婚姻、生子、前途等都要受到星宿神的干預(yù)。
與天神系統(tǒng)相對的是形形色色、數(shù)日繁多的自然神。《禮記·祭法》對神的解釋足: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為風(fēng)雨,見怪物,皆曰神。”正體現(xiàn)了自然神崇拜的特點(diǎn) 秦人信仰體系中的自然神包括地神和各種自然神。
地神。《日書》中的地神主要有“上神”、“地杓神”、“田亳主”、“杜(社)主、“田大人”等。從以下簡文巾可以了解到這些種靈。如“正月亥、二月西、三月未、四月寅、五月子、六月戌、七月巳、八月卯、九月丑,十月申、十一月午、十二月辰,是胃(謂)十神,毋起土攻(功),兇。”(一三二背、一三三背)“正月申、四月寅、六月巳、十月亥、是畏(謂)地杓神以毀宮,毋起土攻(功),兇,月中旬,毋起北南垣及矰之,兇。”(一三八背)“田亳主以乙巳死,杜(社)主以乙西死,雨幣(師)以辛未死,田大人以癸亥死 ”(一四九背)在“土神”、“地杓神”、“田毫主。“杜(社)主”、“田大人”等神靈的忌日這兒天不能動土,否則就會有兇災(zāi),遭受罹難
《日書》中還提到其他一些掌管某- -具體事務(wù)的神靈。如掌管馬交配的神靈馬襟神,秦人向馬裸神祝禱說:“先牧日丙,馬襟合神,東鄉(xiāng)(向)南(鄉(xiāng))向各一馬,口口口中土以為馬襟。”(一五六背)其他還有“馬良日”、“牛良日”、“羊良日”、“豬良日”、“犬良日”、“雞良日”等,在這些吉利的日子,要祭祀相應(yīng)的掌管家畜的神,以求家畜興旺。
祖先神。祖先神主要有父母、王父、驕母等,如“甲乙有病,父母為祟,得之于肉,從東方來裹以漆器”(六八正貳),“丙丁有疾,王父為祟”(七O正貳)。應(yīng)當(dāng)注意的是,《日書》巾雖然未見到秦人祭祀祖先,但是并不代表秦人不崇拜祖先神。從《日書》的性質(zhì)看,“它是古代術(shù)數(shù)學(xué)中的擇日類書籍,具體的說它是目前已知的一本最早的古代選擇通書”(《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422-423頁)。也就是說《日書》是下層民眾用以選擇時日、趨吉避兇的術(shù)數(shù)類書籍,其并不涉及國家級的祭典。黃留珠先生統(tǒng)計了《秦會要》(含訂補(bǔ))中商鞅變法后秦國和實(shí)現(xiàn)統(tǒng)一后的秦王朝禮制,其中吉禮有: “禮、封禪、親郊、祠后土、祠天神、山川(妻河附)、社稷、明堂、宗廟、廟議、廟祭(廢尸祭附)、祠先代帝王、伏祠、臘蠟、雜祭祀、郡縣各祠、幣玉、牲牢、車輅、祭服、巫祝、九鼎、尊浮屠、求仙樂。”(《秦禮制文化述論》,《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學(xué)第五屆學(xué)術(shù)討論會論文集》,陜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頁)其中“宗廟”就是祭祀歷代祖宗的地方,從中可以看出,秦人的祖先神崇拜觀念還是有的。
二、從出土秦簡中看秦人“鬼”的觀念
秦人眼中的鬼主要指的是人死后魂魄所化成的:主要有刺鬼、丘鬼、哀鬼、棘鬼、陽鬼、欦鬼、故丘鬼、兇鬼、暴鬼、游鬼、不辜鬼、粲迓之鬼、餓鬼、遽鬼、哀乳之鬼、天鬼等。也有名中不帶鬼字者,如天、圖夫、大襪等。還有的只是說明了這些鬼的來歷或行為表現(xiàn)的,如幼殤之鬼、人人宮室之鬼、哀乳之鬼、擊鼓之鬼、恒從人女之鬼、當(dāng)?shù)酪粤⒅怼⑶祟^之鬼等。
除了鬼之外,還有各種精怪,它們或常以某種動物或自然現(xiàn)象的形式出現(xiàn),作祟于人。精怪有些是具體的,有神狗、幼蠪、神蟲、會蟲、地蟹、狼、女鼠、地蟲等,有些則是屬于自然現(xiàn)象,有票風(fēng)(大票風(fēng))、寒風(fēng)、恙氣、野火、天火、雷、云氣等。除了自然現(xiàn)象外,精怪多是具體可見的,如“狼恒謼(呼)人門日:‘啟吾。非鬼也。殺而亨(烹)之,有美味”(三三背叁)。這種狼精怪可以被捉住殺死和煮了吃,是可以觸摸到的實(shí)體動物。
“鬼害民罔(妄)行,為民不羊(祥)”(二四背壹),在秦人看來,鬼經(jīng)常危害百姓,恣意妄行,給百姓的生活帶來種種災(zāi)難。鬼給人帶來的災(zāi)害主要有以下幾種:(l)使人或動物得病和死亡。如“一宅中毋(無)故而室人皆疫,或死或病,是是棘鬼在焉”(三七背壹、三八背壹),“人毋故一室皆疫,或死或病,丈夫女子隋須贏發(fā)黃目,是窠窠人生為鬼”(四三背壹、四四背壹)。可見,鬼能使人無緣無故地得瘟疫或者死亡,威脅人的生命安全。鬼不僅會害死人,而且也會害死牲畜,“人之六畜毋(無)故而皆死”(五六背壹)是因?yàn)闄鞴淼年帤膺M(jìn)入了牲畜體內(nèi)。(2)戲弄、騷擾人,給人帶來不安。如刺鬼會無緣無故的攻擊人,“人毋(無)故鬼攻之不已,是是刺鬼”(二七背壹),神狗會偽裝成鬼在夜里“人人室,執(zhí)丈夫,戲女子”(四七背壹),故丘鬼“恒畏人”,狀神會在人的屋里讓“一室之人皆毋(無)氣以息,不能童(動)作”(三六背貳),圖夫會“恒為惡夢,覺而弗占”(四四背貳),這種鬼對人作祟的后果并不嚴(yán)重,似乎只是惡作劇,但也給人的生活帶來了煩惱,讓人不得安寧。(3)奪人財產(chǎn),讓人遭受財產(chǎn)損失。比如暴鬼“恒襄(攘)人之畜”(三七背叁),餓鬼會拿著盛東西的竹器“以人人室,日‘氣(餼)我食”(六二背貳)。從鬼的形象可以看出,鬼的世界是人現(xiàn)實(shí)世界的反映,鬼同人一樣有男女之情、口腹之欲,證明了鬼神人格化和冥域世俗化乃是秦人神秘文化的重要特征(吳小強(qiáng)《略論秦代社會的神秘文化》,《廣州師范學(xué)院報》(社會科學(xué)版)1997年第4期)。
秦人驅(qū)鬼辟邪的東西是多種多樣的,歸納起來主要有:1.植物。如桃弓、桃秉(柄)、桃丈(杖)、桃更(梗)、桃枱、牡棘、牡棘刀、棘椎、牡棘矢、牡棘之劍、牡棘枋(柄)、桑皮、桑心、桑丈(杖)、芻矢、白茅、莎芾、灰生桐、崫、葦。2.動物。如雞羽、豕矢(屎)、犬矢(屎)、六畜鬣毛。3.樂器。如鼓、鐸。4.兵器。如劍、鐵錐。5.日常用品。如女筆(篦)、賁屨、傘、鬈屨。6.礦石類。如白石、沙、土、黃土等。
三、秦人“神”與“鬼”的比較
春秋時期,鬼神二字多是連用的,其含義包括祖先神和天神在內(nèi)的所有神靈,但是仔細(xì)探討起來,二者還是具有一定的差別。 “鬼與神的差別,大而言之,鬼多指先祖;神則多指天神,亦包括山川神靈在內(nèi)。另外,與神的地位相比,則是神高而鬼稍低。就品格來看,神只是主持公道,賞善罰惡的正義化身,但鬼則有好有壞,有良善之鬼,亦有厲鬼。”(晁福林《春秋時期的鬼神觀念及其社會影響》,《歷史研究》 1998年第5期)但是,到了戰(zhàn)同時期,隨著兼并戰(zhàn)爭的日益激烈,各國之間交流的日益頻繁,在各諸侯國交流的過程中,下層民眾的鬼神觀念也發(fā)生了新的變化。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神、鬼之間的差別日益擴(kuò)大,各自的特征日益明顯,顯示出人們已經(jīng)試圖將神與鬼分開來,秦人也不例外。在戰(zhàn)國秦漢時期的秦人眼巾,雖然對于神、鬼的分析還不成熟,但是,神、鬼之間的差別已經(jīng)很明顯了。
首先,神可以給人帶來福利,而鬼只會作祟于人。在秦人眼中,神的形象是正義的,人們可以向神祭祀、祈禱,以求神能賜予其某些好處。主要表現(xiàn)在向神祈求能獲得財富、治愈疾病、如,“戊子以有求也,必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