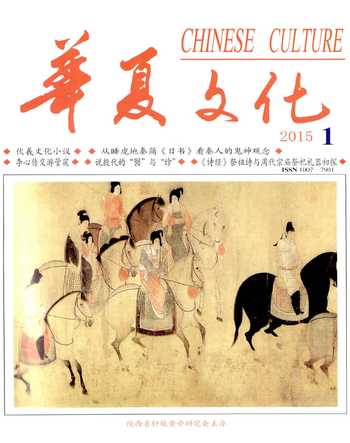五四時(shí)期婦女婚姻觀研究
辛 欣
五四時(shí)期是中國(guó)思想文化大解放的一個(gè)重要時(shí)期,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傳人中國(guó),馬克思主義思想也被引進(jìn)中國(guó),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在陳獨(dú)秀等人的倡導(dǎo)下蓬勃發(fā)展。而對(duì)于束縛中國(guó)婦女的舊式婚姻,學(xué)者們也開(kāi)始了反思與抨擊。作為新文化運(yùn)動(dòng)陣地的《新青年》雜志就有專門探討婦女問(wèn)題的板塊,其巾,對(duì)于婦女婚姻問(wèn)題,學(xué)者們也發(fā)表了各自的意見(jiàn)。此外,諸如《婦女雜志》、《新潮》等五四時(shí)期的報(bào)刊雜志也對(duì)這一問(wèn)題進(jìn)行了討論研究、面塒千百年來(lái)在儒家綱常思想控制F地位卑下的婦女,以及對(duì)待婦女不公正的婚姻行為,隨著中國(guó)文化的大解放,五四時(shí)期婦女的婚嫻觀正在面臨全面的蛻變。
一、新式婚姻觀
這一時(shí)期產(chǎn)生的新式婚姻思想包括:第一,婚姻自主 這里的婚姻自主包括結(jié)婚自由,離婚自由、再嫁自由三個(gè)方面。首先,婚姻應(yīng)該以愛(ài)情為基礎(chǔ),廢除過(guò)去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傳統(tǒng)習(xí)俗。許多學(xué)者對(duì)傳統(tǒng)的父母包辦婚姻、封建的節(jié)烈觀以及傳統(tǒng)社會(huì)中婦女在婚姻中的卑卜.地位進(jìn)行了猛烈地抨擊。認(rèn)為古代之婚姻或因金錢或因肉欲,“女子僅為男子之犧牲,甚焉者男女同為家族主義之犧牲,故所組成之家庭,無(wú)生氣無(wú)精神……結(jié)婚當(dāng)始丁男女之戀愛(ài)。”(高素素:《女子問(wèn)題之大解決》,《新青年》第3卷第3號(hào))由此,如若婚姻中夫妻二人失去了維系婚姻的重要紐帶即愛(ài)情,那么就可以自由離婚,當(dāng)然,對(duì)于長(zhǎng)期處于婚嫻中弱勢(shì)地位的婦女來(lái)說(shuō),離婚自由不僅包括婦女自身有提出離婚的權(quán)利,也有些學(xué)者認(rèn)為在夫要離而妻不愿離婚時(shí),應(yīng)該顧全人道主義而考慮婦女的要求,對(duì)于婦女再婚自由,包括離婚之后的再婚以及丈夫去世后再婚的權(quán)利,這里就涉及到長(zhǎng)期以來(lái)深入人心的婦女應(yīng)該守節(jié)的貞節(jié)問(wèn)題。古代婦女為了守節(jié),丈夫死后不能再嫁甚至殉情而上的做法受到時(shí)人的猛烈批判。他們認(rèn)為,除了寡婦自身不愿再嫁的情況,“倘是為了褒獎(jiǎng)條例,為了貞節(jié)牌坊,那就大錯(cuò)特錯(cuò)了。”(陸秋心:《婚姻問(wèn)題的三個(gè)時(shí)期》,《新婦女》第2卷第2號(hào))總之,現(xiàn)代社會(huì)男女平等,男女都應(yīng)當(dāng)有再婚自由的權(quán)利。
第二,廢婚主義。廢婚主義顧名思義就是廢除婚姻制度,美國(guó)的高曼女十認(rèn)為“婚姻與愛(ài)情,二者無(wú)絲毫關(guān)系,其處于絕對(duì)不能棚容之地位,由南極之與北極也”(高曼女士著,震瀛譯:《結(jié)婚與戀愛(ài)》,《新青年》第3卷第5號(hào))。與婚姻相比,爰情是自由的、獨(dú)立于婚姻之外的一種美好感情。在自由戀愛(ài)中,女子可以“得生育之自由”,擁有牛.或者不生孩子的權(quán)利,而不是因?yàn)椤霸杏秊榕幼罡咛炻殻4婊橐鲋贫取薄堘阅暾J(rèn)為“婚嫻本也是古來(lái)傳留、霸據(jù)、偏狹、欺偽制度中的一種”(張嵩年:《男女問(wèn)題》,《新青年》第6卷第3號(hào)),如果說(shuō)婚姻自主是建立在自由戀愛(ài)的前提下男女所組成的婚姻形態(tài),那么廢婚主義則可以說(shuō)是自由戀愛(ài)發(fā)展到極致的一種婚姻觀。廢婚主義帶來(lái)的一個(gè)重要問(wèn)題就是孩子的教養(yǎng)問(wèn)題。為了兩個(gè)人的愛(ài)情完全不受束縛,減輕婦女撫養(yǎng)孩子的負(fù)擔(dān),五四時(shí)期展開(kāi)了關(guān)于“兒童公育”問(wèn)題大討論,也就是說(shuō)身心健全的人所生的孩子由公共設(shè)立的機(jī)關(guān)撫養(yǎng)長(zhǎng)大,他們的教養(yǎng)費(fèi)用等,應(yīng)該由社會(huì)承擔(dān)。許多學(xué)者對(duì)兒童公育的具體實(shí)施辦法提出了意見(jiàn),沈兼士更是把兒童公育問(wèn)題看作是“徹底的婦人問(wèn)題解決法,處分新世界一切問(wèn)題之鎖匙”(沈兼士:《兒童公育》,《新青年》第6卷第6號(hào))。
第三,倫理的婚姻。隨著人們追求自由戀愛(ài)、婚姻自主思想的發(fā)展,甚至出現(xiàn)了廢婚主義的思想,對(duì)此一些學(xué)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劉延陵提出了一種新的婚姻觀,即“倫理的婚姻”,這種婚姻中婦女可以選擇自己所鐘愛(ài)的對(duì)象,尊重婦女的愛(ài)情自由。但與此同時(shí),又不能發(fā)展至極端的個(gè)人自由主義,婦女在婚姻中仍擔(dān)負(fù)一定的社會(huì)責(zé)任,即繁衍后代之責(zé)任。唯有如此,社會(huì)才得以繼續(xù)發(fā)展,文明才不致滅絕。關(guān)于兒童的教養(yǎng)問(wèn)題,也有學(xué)者指出:首先,兒童教養(yǎng)是父母應(yīng)盡的義務(wù),也是父母對(duì)社會(huì)及家庭應(yīng)負(fù)的責(zé)任,把自己應(yīng)盡的義務(wù)移嫁他人,本來(lái)就是一種不平等的關(guān)系(胡適、藍(lán)志先:《貞操問(wèn)題》,《新青年》第6卷第4號(hào))。其次,兒童的教養(yǎng),在自己手里與在他人手的結(jié)果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孩子還是應(yīng)該由父母自己教養(yǎng)。
二、婦女婚姻觀的嬗變及原因
可以看出,五四時(shí)期的婦女婚姻觀有了巨大的變化.無(wú)論是在對(duì)配偶還是對(duì)婚姻形式的選擇上,都努力的爭(zhēng)取自主選擇的權(quán)利。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diǎn):
首先,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推動(dòng)作用。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倡導(dǎo)西方自由民主思想,提倡以西方的個(gè)人主義來(lái)取代中國(guó)傳統(tǒng)的集體主義,對(duì)于長(zhǎng)期處于家族制度束縛下的婦女產(chǎn)生了思想啟蒙的作用。作為新文化運(yùn)動(dòng)陣地的《新青年》雜志對(duì)于婦女解放的貢獻(xiàn),“在其能具體的指出婦女生活之謬誤,并指導(dǎo)婦女解放的趨向”(陳東原:《中國(guó)婦女生活史》,臺(tái)灣商務(wù)印書(shū)館1990年,第374頁(yè))。該雜志對(duì)于婦女貞操問(wèn)題、愛(ài)情與婚姻問(wèn)題、兒童公育問(wèn)題都有討論,并倡導(dǎo)婦女應(yīng)該獨(dú)立自由,用知識(shí)武裝頭腦,勇敢追求愛(ài)情。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另一方面則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學(xué)說(shuō)特別是儒家學(xué)說(shuō)進(jìn)行了抨擊。長(zhǎng)期以來(lái),作為中國(guó)正統(tǒng)文化的儒家學(xué)說(shuō)樹(shù)立了男尊女卑的思想,強(qiáng)調(diào)女子應(yīng)該遵守“三從四德”的規(guī)定,把婦女的活動(dòng)范圍禁鋼在家庭之內(nèi),要求對(duì)父母、丈夫無(wú)條件的服從.對(duì)于婦女的德行更是有許多的專書(shū)來(lái)規(guī)定,從東漢班昭作第一部關(guān)于婦女的《女誡》,到之后的《女論語(yǔ)》、《內(nèi)訓(xùn)》、《女范捷錄》等,都對(duì)婦德進(jìn)行嚴(yán)格要求,以此鞏固男尊女卑的社會(huì)地位。對(duì)此,五四學(xué)人認(rèn)為首先要解放處于中國(guó)傳統(tǒng)封建家族制下的地位卑下的婦女,號(hào)召婦女走出家庭、公開(kāi)社交、接受教育等。其次,要求重新定義“孝”的意義,反對(duì)孟子所說(shuō)的:“不孝有三,無(wú)后為大”,認(rèn)為“以有后為孝,即必行一夫多妻和蓄妾的制度”(《五四時(shí)期婦女問(wèn)題文選》,第159頁(yè))。所以這一時(shí)期許多學(xué)者認(rèn)為從前講孝的說(shuō)法應(yīng)該改正:“父子母子,不必有尊卑的觀念,卻當(dāng)有互相扶助的責(zé)任。……要承認(rèn)子女自有人格,大家都向‘人的路上走。”(《五四時(shí)期婦女問(wèn)題文選》,第159頁(yè))也就是說(shuō)婦女應(yīng)該摒棄過(guò)去放大了的“孝”的思想,作為一個(gè)有人格的平等的個(gè)人,去選擇自己的婚姻生活。
第二,知識(shí)精英的開(kāi)化作用。任何一種新觀念的產(chǎn)生和傳播必定要通過(guò)一些先進(jìn)知識(shí)分子的領(lǐng)導(dǎo)。思想方面,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的知識(shí)分子開(kāi)始對(duì)處于封建家族制壓迫下的婦女進(jìn)行生活關(guān)懷,陳獨(dú)秀、胡適、劉半農(nóng)、李大釗等人紛紛發(fā)表文章要求解放婦女。此外,西方思想家的文章也被引入中國(guó),周作人翻譯的日本女作家謝野品子的《貞操論》一文,反對(duì)單方面要求女子保持貞操,否認(rèn)貞操即道德,該文在當(dāng)時(shí)引起很大反響。還有如美國(guó)高曼女士的《結(jié)婚與戀愛(ài)》、挪威戲劇家易卜生的劇作《娜拉》都被翻譯引入巾國(guó)。總之,西方女性主義者的女權(quán)主義思想被一些知識(shí)精英宣傳和介紹,他們所關(guān)注的女性婚姻自主權(quán)也成為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先進(jìn)知識(shí)分子關(guān)注的重要領(lǐng)域 此外,許多先進(jìn)的女性通過(guò)自身來(lái)引領(lǐng)自由戀愛(ài)的風(fēng)潮,例如一生巾有著四段刻苦銘心戀情的丁玲,反對(duì)包辦婚姻、逃離家庭的蕭紅等,她們的行為在無(wú)形巾影響著廣大的婦女。
第三,近代社會(huì)婚制改革的延續(xù)性。“從太平天同婚姻生活的變化到洋務(wù)時(shí)期出國(guó)官員和文人們對(duì)歐美婚俗的關(guān)注;從維新派的新式婚姻觀到清末民初婚俗的改造;再到五四時(shí)期婚俗文化的變革,這是婚姻文化變革的一個(gè)歷史延續(xù) ”(梁景和:《五四時(shí)期社會(huì)文化嬗變論綱——以婚姻、家庭、女性、性倫為中心》,《人文雜志》 2009年第4期)而這種歷史的延續(xù)性實(shí)際上也反映了由于社會(huì)的發(fā)展,婦女在社會(huì)巾角色扮演的變化。比如,隨著教育的發(fā)展,女子教育也在先進(jìn)知識(shí)分子的號(hào)召下逐漸受到國(guó)家的重視。 五四之后,中國(guó)自主創(chuàng)辦的女子學(xué)校紛紛建立,1920年,北京大學(xué)開(kāi)放女禁,隨后南京高等師范學(xué)院等學(xué)校也開(kāi)始陸續(xù)招收女生,男女共校也漸漸得到實(shí)現(xiàn)。這使得婦女的地位得以提高,婦女得到了更多受教育的機(jī)會(huì),為更好的接受先進(jìn)的女子解放思想及婚姻自主、自由戀愛(ài)思潮提供了便利,促進(jìn)了婦女思想上的覺(jué)醒。隨著知識(shí)女性的增多,出葉現(xiàn)了一批新式職業(yè),如女醫(yī)生、女記者、女教師、女編輯等等,婦女活動(dòng)的范圍逐漸變大,地位得以提高,在婚姻中也開(kāi)始掌握一定的主動(dòng)權(quán)。此外,經(jīng)濟(jì)地位的提高也對(duì)婦女的婚姻自主權(quán)起了重要作用,魯迅在《娜拉走后怎樣》一文巾尖銳的指出婦女掌握經(jīng)濟(jì)權(quán)的重要姓,否則即使走出了家庭,獲得了婚姻自由,也“只有兩條路:小是墮落,就是回來(lái)”。陶履恭認(rèn)為,中國(guó)古代的社會(huì)是一種“夫耕婦織,夫獵婦炊,婦事養(yǎng)育而夫任保護(hù)”(陶履恭:《女子問(wèn)題——新社會(huì)問(wèn)題之一》,《新青年》第6卷第1號(hào))的生活狀態(tài),婦女被限制在家庭生活中,完拿依賴于丈夫而生活,經(jīng)濟(jì)上不能獨(dú)立,人格自然也由夫家操縱。而由于近代工業(yè)的興起,物產(chǎn)小產(chǎn)于家庭巾,而產(chǎn)于工場(chǎng)中,所以婦女不再操作于家庭,而是受雇于外人,_工廠中出現(xiàn)了大量的女工,婦女此時(shí)不役于父,不役于夫,具有了爭(zhēng)取自身解放和追求婚姻自主的能力以及物質(zhì)條件。
三、婦女婚姻觀嬗變的意義及局限
婦女地位的提高,從父母手中獲得自主選擇婚姻的權(quán)力,開(kāi)始逐漸瓦解中國(guó)傳統(tǒng)的男尊女卑、夫?yàn)槠蘧V的封建家族體制。而家庭是社會(huì)的基本組成單位,婚制的改革也表現(xiàn)出了知識(shí)分子要從家庭著手而徹底廢除封建制,維護(hù)民主共和制的決心。陸秋心在《婚姻自由和德謨克拉西》一文中就將專制婚、同意婚、自由婚三種不同的婚制與君主專制、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三種政體相聯(lián)系,認(rèn)為絕對(duì)白南的婚姻就如同民主共和政體一樣,應(yīng)該受到絕對(duì)的推崇。可見(jiàn),婚嫻自由與政治自由民主是相互影響的。此外,自由婚姻、新式的貞操觀都體現(xiàn)了人倫的解放,中國(guó)自古以來(lái)講求等級(jí)權(quán)威的專制思想開(kāi)始受到摒棄,而個(gè)體的利益受到重視,這種解放對(duì)長(zhǎng)期處于壓迫地位的婦女來(lái)說(shuō)是相當(dāng)重要的。
然而,任何一種思想都不能逃脫所處時(shí)代的圈囿,五四時(shí)期的婦女婚姻觀亦是如此。五四時(shí)期的開(kāi)放文化環(huán)境容易產(chǎn)生出新的思想,然而這種思想或不徹底或過(guò)于激進(jìn)。從婚姻觀來(lái)說(shuō),由于想在短時(shí)間內(nèi)大范圍解放婦女,由此產(chǎn)生出的廢婚主義、兒童公育等思想都稍顯極端,這些政策即使在今天的中國(guó)也難以實(shí)施,所以也由此出現(xiàn)了一些思想上的論戰(zhàn)。此外,這種婚姻觀的影響多體現(xiàn)在知識(shí)女性、學(xué)生和開(kāi)明士紳家庭中,據(jù)當(dāng)時(shí)報(bào)刊記載,民國(guó)二十八年(1939年)中國(guó)義盲率高達(dá)95.1%,廣大農(nóng)村婦女很難接觸到這些新思想,但是在傳統(tǒng)思想容易同守的前提下,當(dāng)時(shí)的知識(shí)分子們敢于提出新的解放性的觀點(diǎn),并且一些知識(shí)婦女由思想到行為方式的改變還是值得肯定的。這也啟示我們,也只有通過(guò)不斷地摸索,才能使得今天的婚姻體制得到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