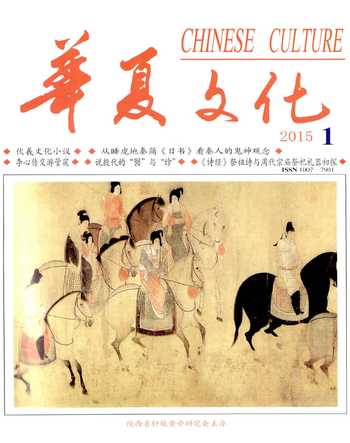李贄的文論思想
閔靖陽(yáng)
一、李贄的雙重人格
李贄(1527-1602)的人生大體可分為兩個(gè)階段,以萬(wàn)歷八年棄官為界。萬(wàn)歷八年54歲之前,李贄的人格和思想盡管怪異,卻依然符合封建士大夫標(biāo)準(zhǔn)萬(wàn)歷幾年之后,李贄以著書(shū)、講學(xué)、避難為主要生活,人格和思想逐漸成熟,作為思想家的李贄才誕生
李贄的人格是雙重人格,狂人是李贄的現(xiàn)實(shí)人格,圣人是李贄的理想人格。作為狂人的李贄,仃為舉止不同于常人。李贄率性自然,待人內(nèi)熱外冷,與投機(jī)之人常整天相處,但往往只是對(duì)面讀書(shū),也不常說(shuō)話(huà);遇不投機(jī)之人,交手禮拜之后,就讓遠(yuǎn)遠(yuǎn)落座。早年兒子死掉,也不納妾生子。當(dāng)了二十年中小官,榮登知府之位,卻于54歲棄官,專(zhuān)職著述講學(xué),并收納一批女弟子。 妻子想念家鄉(xiāng),于是盡遣妻女還鄉(xiāng),自己獨(dú)不回,也不思念傷感 李贄有清癖,當(dāng)官期間每天讓多人輪番掃地,伺候洗澡。62歲因惡頭癢,“蒸蒸作死人氣”,輕易剃去頭發(fā),出家,卻不受戒76歲在獄巾奪剃刀白盡,死前寫(xiě)道“七十老翁何所求” 李贄怪誕的行為源于人格的犴懌。 在他人眼巾李贄是一徹底的狂人,李贄也常以狂人自命,并欣賞狂人。他言:“我從來(lái)不見(jiàn)仃·人果然真正豪杰難得,縱有也不是徹骨地好漢。”(《李溫陵外紀(jì)》卷二《柞林紀(jì)譚》)“大丈夫喜則清風(fēng)朗月,跳躍歌舞;怒則迅雷呼風(fēng),鼓浪崩沙,如三軍萬(wàn)馬”,不可“作婦人女子賤態(tài)”(《焚書(shū)》卷四《豫約》)。李贄眼中的豪杰都是具有獨(dú)立人格、批判意識(shí)和豪爽性情的人他欣賞稍早或同時(shí)的王陽(yáng)明、李夢(mèng)陽(yáng)、何心隱等犴人是源于思想與性情的雙重接近。李贄很清楚白己的人格不能為滿(mǎn)世“依勢(shì)仗寓” “趨勢(shì)諂富”之人所容,“余性好高,好高則倨傲而不能下。……余性好沽,好沽則狷隘而不能容。”(《焚書(shū)》卷三《高潔說(shuō)》)李贄人格中狂狷的維度在萬(wàn)歷幾年之后集中爆發(fā),成為李贊主導(dǎo)的現(xiàn)實(shí)人格。于是士君子眼巾的李贊足“獨(dú)處獨(dú)游,獨(dú)行獨(dú)語(yǔ),目如晨曦,膽如懸瓠,口如雷霆,筆如風(fēng)雨”(《李溫陵外紀(jì)》卷一陶望齡《吊李卓吾文》)。李贄的理想當(dāng)然不是做狂人而是成為圣賢。成圣成賢往往是儒家士人的終極追求。李贄渴望成圣賢之心及其強(qiáng)烈,“晝夜讀書(shū),期與古先圣哲合德而已。”(《續(xù)焚書(shū)》卷一《與周友山》)“丈夫生于天地問(wèn),太上出世為真佛,其次不失為功名之士j若令當(dāng)世無(wú)功,萬(wàn)世無(wú)名,養(yǎng)此狗命,在世何益,不如死矣 ”(《李溫陵外紀(jì)》卷一汪本鈳《哭李卓吾先生文》)李贄理想中的自我是堪與孔子并列的圣人,因此李贄時(shí)刻以圣賢的標(biāo)準(zhǔn)要求自己,并以受圣人教化的民眾的標(biāo)準(zhǔn)衡量別人。然而狂人人格與圣人人格并不相同,現(xiàn)實(shí)中的自我與理想中的自我存在沖突,李贄拿圣人人格苛求自己,拿狂人人格面對(duì)世俗世界,既對(duì)自己不滿(mǎn),又對(duì)世俗不滿(mǎn),加劇了天性巾求全責(zé)備與憤世嫉俗的程度。隨著生命的流逝,李贄成圣賢之心愈加迫切,狂狷的程度愈演愈烈。
二、李贄思想概述
李贄是明代偉大的思想家,思想復(fù)雜,其思想源于陽(yáng)明心學(xué),卻不同于心學(xué),雜取道釋思想,合于一體,以“童心”作為思想本源,形成了獨(dú)特的思想體系。
(一)儒道釋之學(xué),一也
對(duì)生死性命之思是李贄思想的根底 凡為學(xué)皆為窮究自己生死根因,探討自家性命下落。”對(duì)儒道釋學(xué)說(shuō),李贄都接受并能夠融會(huì)貫通,性命思想是其貫通儒道釋的樞機(jī)。李贄認(rèn)為三教的立足點(diǎn)都是大道,三教圣人同以性命為所宗,都是教人如何實(shí)現(xiàn)生命的永恒。“唯三教大圣人知之,故竭平生之力以窮之,雖得心應(yīng)手之后,作用各各不同,然其不同者特面貌爾。”(《續(xù)焚書(shū)》卷一《答馬歷山》)“夫所謂仙佛與儒,皆其名耳。孔子知人之好名也,故以名教誘之;大雄氏知人之怕死,故以死懼之;老氏知人之貪生也,故以長(zhǎng)生引之。皆不得已權(quán)立名色以化誘后人,非真實(shí)也。惟顏?zhàn)又嗜辗蜃由普T二”(《焚書(shū)》卷一《答耿司寇》)李贄認(rèn)為儒道釋三教的本質(zhì)都是三教圣人針對(duì)世人執(zhí)著之物,設(shè)立方法引導(dǎo)之歸于大道的過(guò)程,區(qū)別只在于三教圣人對(duì)世人執(zhí)著之物的認(rèn)識(shí)和引導(dǎo)方法的差異,大道和三教的本質(zhì)并無(wú)差別。大道是真實(shí)自在的,三教的引導(dǎo)方法不過(guò)是權(quán)宜之計(jì),并非真實(shí)的永恒的。基于這樣的思想,在李贄思想體系中,儒道釋三家是同一的。
李贄雖然儒道釋兼收并蓄,但對(duì)龐雜的儒道釋思想都進(jìn)行了取舍。對(duì)于儒家思想,李贄主要接受先秦儒家和心學(xué),批判理學(xué)思想;對(duì)于釋家,李贄禪凈雙修;對(duì)于道家,李贄認(rèn)可老莊思想 儒家思想是李贄貫穿一生的主導(dǎo)思想。李贄服膺孔子,將孔子看做儒家的大圣人,身為芝佛院主持依然懸掛孔子畫(huà)像,認(rèn)可先秦儒家的誠(chéng)意正心的理念,高揚(yáng)儒家的心性論。李贄五十歲后受陽(yáng)明心學(xué)特別是泰州學(xué)派影響甚大。李贄師事王艮之子王襞,兩次面見(jiàn)浙中學(xué)派祖師王畿,同羅汝芳等心學(xué)傳人接觸廣泛。依據(jù)泰州學(xué)派思想,認(rèn)為人人理論上都可為孔子。李贄信仰孔子,但不以孔子的觀(guān)念作為標(biāo)準(zhǔn),也不執(zhí)著堅(jiān)守于孔子的言行。李贄在云南為官期間,同信仰佛教的僧侶和居士來(lái)往密切,對(duì)禪宗的空無(wú)心性論理解甚深,后來(lái)李贄出家為僧,宣揚(yáng)凈土宗思想:禪宗逐漸凈土宗化是明代漢傳佛教的重要變化,僧人往往對(duì)外宣傳凈土思想,爭(zhēng)取信眾獲得布施,對(duì)己持有禪宗主張,追求明心見(jiàn)性。明代有很多僧人禪凈雙修,李贄也是如此,只是李贄不是嚴(yán)格的僧人,不守戒律,而且思想中存在著比重更大的非佛教思想。李贄對(duì)于道家思想的接受源于對(duì)《老子》和《莊子》的研讀和注解。李贄十分認(rèn)同先秦道家慕本真重自然求自由的思想:“真”可以說(shuō)是李贄思想的本體,求真是李贄思想的旨?xì)w,“童心”是李贄思想的本源。
(二)童心本源
李贄將“童心”視作人的本源、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fù)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焚書(shū)》卷三《童心說(shuō)》)在李贄思想中“童心”即是本真合道的狀態(tài),是人心的原初形態(tài),“童心”——“真”——“初”是三位一體的關(guān)系,是李贄設(shè)定的思考言說(shuō)的邏輯前提。李贄的童心說(shuō)受道家思想影響強(qiáng)烈。“嬰兒”在《老子》巾出現(xiàn)了四次。老子認(rèn)為嬰兒的原初狀態(tài)是人天然的最接近道的狀態(tài),所以常以嬰兒來(lái)代指得道。“真”在《莊子》中出現(xiàn)了六十六次,意義極為豐富 莊子所標(biāo)舉的“真”是天道與人性情的同一,是人的自由的存在狀態(tài)。一切仁義道德世俗禮法都是對(duì)人本質(zhì)自由的束縛和遮蔽,都是必須拋棄的要保持本真存在,必須渾然與物同體,“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對(duì)于“童心”的論述也見(jiàn)于儒家,孟子日:“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認(rèn)為作為本體的心無(wú)善惡,但心派生的性本善,最善的性莫過(guò)于嬰兒。先秦儒道兩家都非常重視和肯定“童心”,認(rèn)為道可以通過(guò)童心較完整地顯現(xiàn)。李贄的“童心說(shuō)”繼承了先秦道家和儒家的“童心近道”思想,將“童心”作為自己思想的本源,在本體維度上并無(wú)創(chuàng)見(jiàn)一“童心說(shuō)”有原創(chuàng)價(jià)值的部分在于童心喪失原因與結(jié)果的分析與童心對(duì)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意義.
(三)批判假道學(xué)
人的嬰兒狀態(tài)最接近道.隨著年歲的增長(zhǎng),仁義禮智的侵入,童心漸失.與道愈遠(yuǎn)。李贄對(duì)童心喪失原岡的分析固然沒(méi)有脫離老子的窠臼,但因其強(qiáng)烈的現(xiàn)實(shí)針對(duì)性,依然意義重大、李贄認(rèn)為童心喪失首先源于日常經(jīng)驗(yàn),其次源于所受的教育,再次源于對(duì)聲名的追求?“夫道理聞見(jiàn),皆自多讀書(shū)識(shí)義理而來(lái)也。”李贄重點(diǎn)批判了理學(xué)教育對(duì)童心的遮蔽。李贄認(rèn)為多讀書(shū)識(shí)義理應(yīng)該,但理學(xué)的教育不僅不能使人養(yǎng)護(hù)童心,反而因多瀆書(shū)識(shí)義理喪失童心,使聞見(jiàn)道理取代了童心。“聞見(jiàn)道理”主要是理學(xué)家改造后的儒學(xué)思想。一方面理學(xué)家把四書(shū)五經(jīng)當(dāng)做真理,教化丗人,乃一方面理學(xué)家改造先秦儒家思想使之符合理學(xué)主張,二者郜嚴(yán)重危害童心,是童心喪失的罪魁禍?zhǔn)住<词故撬臅?shū)五經(jīng),“縱出自圣人,要亦有為面發(fā),不過(guò)因病發(fā)藥,隨時(shí)處方,……豈可遽以為萬(wàn)世之至淪乎?”經(jīng)過(guò)理學(xué)、尤其是假道學(xué)的改造,已淪為“道學(xué)之口實(shí),假人之淵藪” 明代巾后期理學(xué)思想喪失了宋代的原發(fā)性,日漸陳腐,義經(jīng)朝廷的宣揚(yáng)、利用與改造,成為國(guó)家意識(shí)形態(tài),淪為統(tǒng)治的工具。士人往往口言理學(xué)思想,作為進(jìn)身之階,陽(yáng)奉陰違,實(shí)則逢場(chǎng)作戲不擇手段,以致于假人、假言、假事盛行。“蓋其人既假,則無(wú)所不假矣。由是而以似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與假人道,則似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wú)所不似,則無(wú)所不喜、滿(mǎn)場(chǎng)是假,矮人何辯也。”(《焚書(shū)》卷三《童心說(shuō)》)陽(yáng)明心學(xué)的出現(xiàn)與盛行就是矯理學(xué)之弊。李贄感于滿(mǎn)場(chǎng)是假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而發(fā)童心之論,批判意味強(qiáng)烈,言同時(shí)人之未言.使有間感者心有戚戚,對(duì)假道學(xué)大加撻伐,社會(huì)影響極大。《童心說(shuō)》的意義不在于理論創(chuàng)新而在于社會(huì)批判。
(四)肯定“私”與“欲”
理學(xué)家將大理視為世界的本原,人欲是天理的塒立面,危害天理的自然流行,因此普遍要求“存天理滅人欲” 王陽(yáng)明則以“致良知”來(lái)去除私欲李贄立足于“童心說(shuō)”,認(rèn)為人的童心作為人之仞的本真心包含了私欲存在,因此復(fù)歸童心的同時(shí)也就肯定了私欲的必然性。李贄獲得較大的社會(huì)影響,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一個(gè)重要維度在于首次肯定私欲的合理性,反對(duì)以人理來(lái)壓制人性巾自在之私與欲。李贄在《減書(shū)》卷二十四《德業(yè)儒臣后論》中稱(chēng):“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見(jiàn),若無(wú)私則無(wú)心矣 ”將私心作為人心的重要維度加以肯定。肯定私心必然同時(shí)肯定由私心派生出私欲,李贄義從陰陽(yáng)平衡易理觀(guān)出發(fā),一方面認(rèn)為人皆公私心俱存,二者都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認(rèn)為男女也應(yīng)該平衡平等,男女之欲也是自然合理的,從而對(duì)情欲的追求也持肯定態(tài)度,因此對(duì)卓文君私奔司馬相如之舉非常贊賞 李贄對(duì)“私”與“欲”的肯定既是時(shí)代風(fēng)氣使然,義引領(lǐng)并深廣地影響了時(shí)代風(fēng)氣。
三、李贄的文論思想
(一)本源論——童心說(shuō)
“童心”是李贄思想的本源,“童心說(shuō)”是李贄文論思想的核心。故李贄曰:“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存有“童心”的作者依據(jù)“童心”創(chuàng)作的文章才有可能成為“至文”,“至文”一律出自“童心”。“童心”也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本源。蘇軾云:“吾義如萬(wàn)斛泉涌,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wú)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dāng)行,從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文說(shuō)》)蘇軾雖未言童心,其寫(xiě)作狀態(tài)卻完全依本真之心任自然而生之情自由流瀉。蘇軾的佳作可稱(chēng)至文,這種自然合道的寫(xiě)作狀態(tài)乃是對(duì)“童心”的完美詮釋?zhuān)欢巴摹敝皇菍?xiě)作至文的本源,并非充分條件,李贄為了樹(shù)立“童心”的本源地位,對(duì)存有“童心”的人與其依據(jù)“童心”創(chuàng)作的文字不加分析地推崇。“茍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jiàn)不立,無(wú)時(shí)不文,無(wú)人不文,無(wú)一樣創(chuàng)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說(shuō)什么六經(jīng),更說(shuō)什么《語(yǔ)》、《孟》乎!”(同上)李贄衡量至文的標(biāo)準(zhǔn)即是否出于童心,出于童心自成典范,四書(shū)五經(jīng)皆不足效法。
在《童心說(shuō)》中李贄對(duì)古今至文流變的淪述同樣具有重大理論價(jià)值。李贄的時(shí)代正是復(fù)古主義文學(xué)思潮興盛的時(shí)代,文壇復(fù)古思想濃郁,除仍以四書(shū)五經(jīng)為最高標(biāo)準(zhǔn)外,文必秦漢詩(shī)必盛唐,特別注重格調(diào)法式。在復(fù)古主義籠罩下,李贄關(guān)于至文流變的觀(guān)點(diǎn)尤為突出。“詩(shī)何必占《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曲》,為《水滸傳》,為今之舉子業(yè),皆占今至文,不可得而時(shí)勢(shì)先后論也。”(同上)李贄認(rèn)為詩(shī)文只要出于童心,即是至文,各時(shí)代都有至文出現(xiàn),而且至文在不同的時(shí)代都有代表性的詩(shī)文尤其難得的是,李贄高度肯定了往往不為正統(tǒng)文人重視、帶有濃重民間色彩的傳奇、院本、雜劇、小說(shuō),對(duì)于當(dāng)世的《水滸傳》尤為贊賞,對(duì)于文人往往當(dāng)做敲門(mén)磚的舉子業(yè)也倍加推崇.李贄的文學(xué)觀(guān)不為時(shí)代所縛,不迷信古人,對(duì)當(dāng)世詩(shī)文也能夠正視并重視,能夠認(rèn)清古今文學(xué)的通變,是復(fù)古思潮籠罩下文壇的重大成就。
(二)作者論——人品決定文品
李贄認(rèn)為“童心者自文”,作者的品格決定文章的品格一李贄對(duì)于文學(xué)作品的觀(guān)照首先審視作者的人格,如果人格狂狷,特立獨(dú)行,那么文章也是好文章;如果人品卑弱,文章決不會(huì)得到稱(chēng)許。明人周暉《金陵瑣事》卷一《五大部文章》載:李贄常云,“宇宙有五大部文章:漢有司馬子長(zhǎng)《史記》,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蘇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滸傳》,明有李獻(xiàn)吉集。”李贄對(duì)五大文章的肯定主要源于對(duì)作者人格的欽佩二如李贄對(duì)蘇軾“心實(shí)愛(ài)公,是以開(kāi)卷便如與之面敘也。”(《續(xù)焚書(shū)》卷一《與焦若侯》)“蘇長(zhǎng)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驚天動(dòng)地。世人不知,只以文章稱(chēng)之,不知文章只彼余事耳。世未有人不能卓立而文章能不朽者。”(《焚書(shū)》卷二《復(fù)焦若侯》)李贄與李夢(mèng)陽(yáng)文學(xué)思想差異頗大,李夢(mèng)陽(yáng)首揭文學(xué)復(fù)古大旗,李贄主張出于童心即是至文,古今至文代代流變。但李贄對(duì)李夢(mèng)陽(yáng)欽佩異常,“李公才最高,其人負(fù)氣,傲睨一世,以是得奇禍,坎懔終其身,世咸疾之如仇。世傳李公雙瞳炯炯如電,論古今終夜不少休一世莫能容,良有故矣。若李公者,安能使無(wú)聞哉!”(《續(xù)藏書(shū)·李夢(mèng)陽(yáng)傳》)“如空同先生與陽(yáng)明先生同世同生,一為道德,一為文章二千萬(wàn)世后,兩先生精光俱在。”(《焚書(shū)》增補(bǔ)一《與管登之書(shū)》)可見(jiàn)李贄的文學(xué)作者論是首先考察作者的人格,如果為人光明磊落狂狷勁節(jié),即使文學(xué)觀(guān)念與李贄不合,或作品因循模擬,都不足影響其在李贄心中的地位。只要李贄認(rèn)為其人存有童心,其文源自童心,其人就是犴狷的豪杰,其文就是天下至文。
(三)作品論——“化工”與“畫(huà)工”
李贄以“童心”為本源,認(rèn)為至義必然出于童心,是童心的自然流溢,岡此李贄的美學(xué)觀(guān)念必然以“真”和“自然”為美。 “以真為美” “以自然為美”的美學(xué)觀(guān)念自然源于道家、道家思想認(rèn)為最高境界的藝術(shù)是“以天合天”的天籟之音,而工巧的人籟只是藝術(shù)的低層次后世受道家思想影響的藝術(shù)家往往推崇自然、天工的作品,“一語(yǔ)天然萬(wàn)古新,豪華落盡見(jiàn)真淳。”李贄的《雜說(shuō)》提出了“化工”與“畫(huà)丁”的差別及其作者維度的原因。
“《拜月》、《兩廂》,化工也;《琵琶》,畫(huà)工也。夫所謂畫(huà)工者,以其能奪天地之化丁,而其孰知天地之無(wú)工乎!……要知造化無(wú)工,雖有神圣,亦不能識(shí)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誰(shuí)能得之?由此觀(guān)之,畫(huà)工雖巧,已落二義矣。”“畫(huà)工”的作品如《琵琶記》,結(jié)構(gòu)工巧、文辭華美,思想上也符合官方意識(shí)形態(tài)的要求,呈現(xiàn)了人工雕琢的最高境界。可是天地自然,本無(wú)工巧。《拜月》、《兩廂》語(yǔ)言流暢自然、感情真摯,雖亦為人工作品,卻少見(jiàn)人工雕琢的痕跡,“化工”的作品接近于大道自然,臻于天籟。二者的區(qū)別主要源于作者的創(chuàng)作方式不同。“畫(huà)工”的作品是作者思考所得。“偉作者窮巧極工,不遺余力,是故語(yǔ)盡而意亦盡,詞竭而味索然亦隨以竭。”思考形成的作品主于人理性維度,可用于教化,可用來(lái)分析、學(xué)習(xí),卻不易深人人心。“《西廂》、《拜月》,乃不如是。意者宇宙之內(nèi)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于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議耳。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此其初皆非有意于為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wú)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shí)時(shí)有許多欲話(huà)而莫可所以告語(yǔ)之處,蓄極積久,勢(shì)不能遏。一旦見(jiàn)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訴心中之不平,感數(shù)奇于千載。既已噴玉唾珠,昭同云漢,為章于天矣。遂亦自負(fù),發(fā)狂大叫,流涕慟哭,不能自止。寧使見(jiàn)者聞?wù)撸旋X咬牙,欲殺欲割,而終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焚書(shū)》卷.《雜說(shuō)》)“化工”的作品是作者情感自然自由流瀉而成,可能形式不甚完美,卻訴諸人心,故感人至深。由于“化工”之作源于“童心”,倍受李贄推崇。李贄對(duì)文學(xué)作品的理解和欣賞依然源于“童心說(shuō)”,側(cè)重于對(duì)作者人品與創(chuàng)造方式的考察,考察作者的真情是否不加限制地自由抒發(fā),塒于文學(xué)本體——形式的觀(guān)照不夠。因此,李贄主要作為思想家流傳于世,他的影響主要在于思想啟發(fā)。
四、李贄的時(shí)代歷史影響
作為明代偉大的思想家之一,李贄對(duì)明代后期的思想界影響深廣,生前死后都?xì)ёu(yù)分明。贊譽(yù)李贄的人認(rèn)為李贄是大圣人,如馬經(jīng)綸言:“李先生,所謂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之人也。”(《李贄研究參考資料》第1輯,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88頁(yè))痛恨李贄者則認(rèn)為其甚于洪水猛獸,如明神宗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降罪李贄。批評(píng)李贄的如東林學(xué)派領(lǐng)袖顧憲成認(rèn)為李贄“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敗為是非而已”(許蘇民:《李贄評(píng)傳》,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6年,第636頁(yè))。認(rèn)同李贄的如李贄好友焦竑的評(píng)價(jià)則是“未必是圣人,可肩一狂字,坐圣門(mén)第二席”(《李贄研究參考資料》第1輯,福建人民出版(1976年,第50頁(yè))。對(duì)于李贄的社會(huì)影響,大啟年問(wèn)的內(nèi)閣首輔朱國(guó)禎憤慨地說(shuō):“最能惑人,為人所推,舉國(guó)趨之若狂”;“今日士風(fēng)猖狂,實(shí)開(kāi)于此。全不讀《四書(shū)》本經(jīng),而李氏《藏書(shū)》、《焚書(shū)》,人夾一冊(cè),以為奇貨、”(許蘇民: 《李贄評(píng)傳》,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6年,第168頁(yè))傅維麟也說(shuō):“后士風(fēng)大都由其染化。”(《明書(shū)》卷一百六十《李贄傳》)朱國(guó)禎、傅維麟的說(shuō)法不無(wú)夸大之嫌,士風(fēng)猖狂自正德年已發(fā)端,愈演愈烈,到萬(wàn)歷年已成普遍之狀,李贄只是猖狂士風(fēng)巾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但朱國(guó)禎的觀(guān)點(diǎn)證明了李贄對(duì)于當(dāng)時(shí)士人的深遠(yuǎn)影響、作為思想家,李贄的影響波及政治、宗教、社會(huì)、文化各個(gè)領(lǐng)域,但李贄影響最大的領(lǐng)域依然在文學(xué)。晚明文學(xué)思潮與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受李贄影響最大的是湯顯祖、公安派和金圣嘆。
湯顯祖是泰州學(xué)派羅汝芳的弟子。萬(wàn)歷十八年湯顯祖見(jiàn)到《焚書(shū)》立即成為李贄的崇拜者李贄大膽肯定卓文君私奔之舉,給湯顯祖極大震撼和啟發(fā),萬(wàn)歷二十六年完成了《牡丹亭》 湯顯祖非常認(rèn)同李贄的“童心說(shuō)”,以此為基礎(chǔ)引申出自己的“情至說(shuō)”。李贄也很認(rèn)可湯顯祖的情至思想,并欣賞杜麗娘追求個(gè)性自由、追求自由戀愛(ài)的反封建精神,于萬(wàn)歷二十七年赴江西拜訪(fǎng)湯顯祖。公安三袁是李贄的私淑弟子。萬(wàn)歷十九年至萬(wàn)歷二十一年,三袁數(shù)次與李贄淪道,往往歷時(shí)數(shù)月。三袁在追求自我價(jià)值與實(shí)現(xiàn)/卜命解脫的維度深受李贄影響,其“性靈說(shuō)”兒乎就是“童心說(shuō)”的演繹。萬(wàn)歷二十四年后李贊思想歸于深沉平靜,三袁也都經(jīng)歷了由狂放走向內(nèi)斂的人生歷程。袁巾道寫(xiě)《李溫陵傳》道出了三袁對(duì)李贄的崇敬和與之的不同,“雖好之,不學(xué)之也。其人不能學(xué)者有五,不愿學(xué)者有三”,對(duì)‘李贄的評(píng)說(shuō)深入、公正而客觀(guān)。李贄評(píng)點(diǎn)過(guò)《水滸傳》、《兩廂記》等小說(shuō)戲曲,坊問(wèn)銷(xiāo)量甚巨,于是偽書(shū)蜂出,托名李卓吾的評(píng)點(diǎn)本比比皆足其中影響最大的一樁學(xué)術(shù)公案是李卓吾坪《水滸傳》之容與堂本與袁無(wú)涯本真?zhèn)沃疇?zhēng)。 明金圣嘆評(píng)點(diǎn)的《水滸傳》、《兩廂記》與李卓吾評(píng)本相似,都貫穿著狂放的精神與自我價(jià)值的追求,部分文學(xué)思想也相近,而且金評(píng)中不時(shí)譏評(píng)李卓吾,幾乎以李卓吾為假想敵,都證明了金圣嘆受李贄影響之深。金圣嘆是明代狂放思潮的殿軍,是晚明精神上最接近李贄的人物。金圣嘆與李贄雖無(wú)學(xué)術(shù)思想的直接傳承,但性情與人生觀(guān)、價(jià)值觀(guān)的相近。導(dǎo)致金圣嘆同李贄一樣走向了悲劇的人生結(jié)局。不過(guò)對(duì)二人而言,或許未必足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