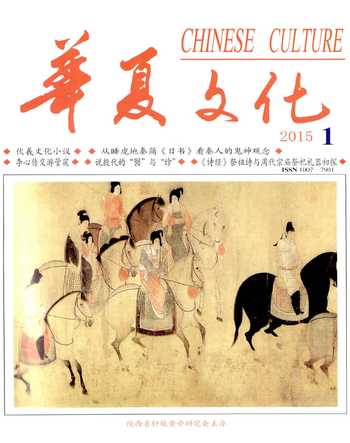兩漢質子制度在外交中的應用——人質外交
張胡玲
質子制度是兩漢時期處理民族關系的重要政治制度,從外交層面看,可以將其理解為只有典型意義的人質外交。人質外交古已有之,春秋時期各國為了昭示信義,多交換王子以為質不光諸侯之間,連周王室也發生過“周鄭交質”的事件,人質外交到戰同時仍很盛行。說到底,外交是為政治、軍事服務的,因此,“人質外交可以說是奉使外交的特例,是為完成某種特殊使命而采取的一種外交手段”(賈繼東:《楚圉人質外交小議》,《中華文化論壇》,1998年第4期)。質子制度形成后所發揮的作用,在漢朝統治階級“以夷制夷”策略和與匈奴爭戰的過程中得到很好的體現。
一、質子制度在“以夷制夷”策略中的輻射
“夷”,泛稱遠離中原的周邊少數民族。“以夷制夷”,簡單說來,就是利用少數民族對付少數民族,即依靠歸順的少數民族尤其足其上層人物完成中央政權對各族的統治。中原政權對付“四夷”的慣用策略是“以夷制夷”,對境外各族進行分化、挑撥、各個擊破。所謂“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漢書·晁錯傳》)。
質子制度確立后,匈奴、南越和西域各國向漢朝遣質、朝貢、服兵役成為基本義務,漢政府利用這些有利條件充分保證證了兩漢在伐叛戰爭中的勝利。樓蘭臣服后,武帝天漢二年(前99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為開陵侯,將樓蘭國兵擊乍師。征和四年(前89年)又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危須等六國兵分別擊車師,迫使車師工投降臣服,這足“以夷伐夷”在實踐中的應用。 該戰略“充分利川了西域國家間的矛盾,維持了各種力量問的平衡,從而使西漢的羈縻統治體系更加穩固”(石少穎《烏孫歸漢與西漢外交》,《湖北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斷匈奴“右臂”是漢通西域的最初動機,漢與烏孫聯合共同夾擊匈奴,使匈奴遭受重創,再加上丁零從北方、烏桓從東方乘機夾攻,斷匈奴“左臂”,匈奴遂不能再與漢對抗,這是“聯夷克夷”的策略實踐。西漢利用質子手段,成功拆散西域與匈奴的聯盟,為進一步利用前者牽制、打擊后者作了軍事和外交上的準備,具有濃厚的實用主義色彩。此外,從劉秀對待南北匈奴、鮮卑、烏桓的政策,可以明顯看出東漢前期“以夷制夷”、“以夷攻夷”的策略思想。東漢歷代皇帝“以夷制夷”策略的出發點是處理當時南北匈奴關系及北匈奴與烏桓、鮮卑的關系,當然這種政策因時代、階級局限性,對后代也有一些負面影響。唐人盧俌在總結兩漢成功經驗的基礎上,主張唐也應更為積極主動地解決突厥問題.他說:“臣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算,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購辯勇之士,班、傅之儔,旁結諸蕃,與圖攻取,此又犄角之勢也”(《舊唐書·突厥傳上》)。這實質上是通過加強與“蠻夷”的聯系,增加對“蠻夷”的影響,逐漸改變華夷對立的局面一。
質子制度是調節民族關系而采取的一種羈縻政策,由于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和風俗習慣等方面的差異,根據少數民族的習俗特點,利用本民族首領治理該地區即“以夷治夷”是一條有效的途徑。班超的“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一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后漢書·班超列傳》),真可謂一語破的,道出“以夷治夷”靈活自治政策的玄機。自從向歸附民族納質后,多個質子被扶立為少數民族的最高首領,任其自治,消除疑慮,既改善了中外關系,客觀上又增強了各同對漢朝的向心力。這種“立其王而綏其人”的自治政策,確實起到“不動中同,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后漢書·班超列傳》)的效果,這也是兩漢在扶植親漢力量方面不斷追求的目標。
總之,質子制度對“以夷制夷”斗爭策略的影響,是它受到統治者推崇的重要因素。民族關系是一個相對敏感的問題,漢朝統治階級既承認民族差異的存在,又能因地制宜,使“懷柔”、“威服”、“分而治之”的羈縻手段得到巧妙地發揮
二、人質外交在漢匈爭奪戰中的體現和實現
自古以來,匈奴就是中國在北方的強勁對手,中原地區為防御匈奴的進攻做出了種種努力秦統一后,為打擊匈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西漢初年,漢朝在漢匈戰爭中一度處于下風,被迫采取“和親”政策,以大量財物換取較多的喘息時間。從漢武帝開始,形勢逆轉,西漢對匈奴發起大規模進攻。公元前119年的漢匈大戰,匈奴軍隊主力及人畜資產都受到相當嚴重的損失,不得不向北遠遁,形成漠南無王廷的形勢。此后很長一段時問內,漢匈沖突的重心集巾在西域地區。漢向西域大量征質與匈奴對該地區的拉攏、爭奪有密切的關系。可以說,兩漢朝貢制度的建立,是漢、匈強弱易位在外交制度上的反映。
早在漢通西域之前,匈奴勢力已擴展到兩域地區,在兩域設置“僮仆都尉”,命諸國交納賦稅,西域儼然成為匈奴的經濟命脈各國懾于匈奴的威力,不敢不低首服從。這樣,匈奴不但在經濟上獲得西域諸國的資助,在政治上也樹立較鞏同的統治地位,“兩域地區自從隸屬匈奴后,一向就是匈奴在物力和人力上的補給線”(安作璋:《兩漢與西域關系史》,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9頁),西域成為匈奴向中原進攻的一個有力的“右臂”。正“由于西域某種程度的臣服于匈奴,所以漢通西域也就表現著與匈奴的斗爭和爭奪”(田繼周:《秦漢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177頁)。漢政府要想鞏同邊境上的勝利,必須打破匈奴在西域的統治。烏維單于死后,匈奴與漢朝的爭奪明顯處于劣勢,但西域地區仍處于其控制之下。大宛戰役后,康居、大宛及“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人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漢書·李廣利傳》),這對于折斷“匈奴右臂”起了很大的作用。隨著西域諸國納質稱臣,漢朝取得西域的統治權,匈奴無法再取富于兩域,進一步削弱了它的國勢,使其在與漢的斗爭中處于更為不利的地位。西漢與匈奴在西域的較量,突出表現在對車師的爭奪上。車師在今新疆吐魯番盆地,自古為通天山南北的重要孔道,如果西漢能取得車師,不儀可以驅逐匈奴在兩域的勢力,而且可以出乍師后庭,進一步襲擊匈奴的有部。正由于這一軍事目的,漢匈之問對兩域統治權的爭奪更加白熱化。 爾漢初年,光武帝出于“攘外必先安內”的考慮,拒絕西域送質子、遣都護的要求,使得鄯善、車師、龜茲諸國投降匈奴。東漢政府要徹底打退北匈奴的進攻,也必須走與西漢對付匈奴相同的路線。為此,雙方義展開新一輪的爭奪。東漢一朝,西域曾三通三絕,一方面說明東漢對民族關系的駕馭能力時優時劣,導致了這種關系的不穩定性,另外也從側面反映了漢匈爭奪西域統治權的激烈,導致西域在兩大勢力之間搖擺不定。
漢匈爭奪西域統治權的激烈義集中反映在雙方對西域各國的利用、控制和競相向其爭取質子。許多小國在漢匈之問搖擺不定,既納質于漢,義納質于匈奴。樓蘭的情況可以作為一個例了 漢武帝時期,漢與匈奴還基本處于勢均力敵的狀態,樓蘭向漢朝遣送一名質子,亦同樣送另一名去匈奴。樓蘭王的話說得最清楚:“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白安”(《漢書·西域傳·鄯善國》),這鮮明反映出小國處于兩大強國夾縫中生存的艱辛與無奈。宣帝即位,派兵擊匈奴,車師復與漢通,“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漢書·兩域傳·車師后國》。東漢初,鄯善、車師前王、焉耆等I8國都派遣質子人侍,獻其珍寶并請復置都護,但光武帝忙于鞏固國內統治無暇外顧,也不愿和匈奴開戰,于是皆還其質子。從這些記載中可知對質子的爭奪足漢匈爭奪西域統治權的一個重要方面。
綜上所述,人質外交是兩漢政治史的有機組成部分,深刻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征 閃漢人質外交在實踐中積累的經驗,有許多值得后丗借監的地方。漢朝這樣做是無可厚非的明智之舉,特別在對匈奴問題上,漢朝通過質子外交“以夷攻夷”取得了抵御匈奴的全面勝利,“漢對屬國以恩德懷柔之,以威嚴鎮撫之,則諸國納質奉貢,助兵助餉,以事上國,共拒匈奴”(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