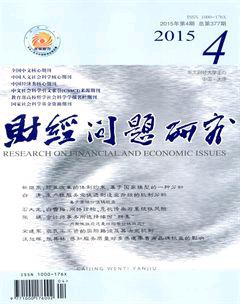農(nóng)民工工資的實(shí)際路徑及其決定機(jī)制



摘 要:劉易斯模型的工資路徑是先平直后上折,但根據(jù)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制成的農(nóng)民工工資路徑圖則是上下波動(dòng)的。形成這種路徑的根本原因是農(nóng)民收入的差異性。本文首先采用收入排序法生成中國(guó)農(nóng)民工的供給曲線,然后在對(duì)比費(fèi)景漢和拉尼斯的兩集合與劉易斯三集合模型的基礎(chǔ)上,提出中國(guó)農(nóng)業(yè)內(nèi)部產(chǎn)業(yè)升級(jí)與農(nóng)村勞動(dòng)力第四集合的概念,并由此形成四集合分析法。四集合分析法說(shuō)明了農(nóng)民工供給曲線的移動(dòng)特征,進(jìn)而解釋了中國(guó)農(nóng)民工工資路徑的特別形態(tài)。
關(guān)鍵詞:農(nóng)民收入;農(nóng)民工工資;勞動(dòng)供給曲線;四集合分析法
中圖分類號(hào):F3236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0176X(2015)04008209
一、引 言
從 1984 年開始,政府準(zhǔn)許農(nóng)民自籌資金、自理口糧進(jìn)入城鎮(zhèn)務(wù)工經(jīng)商,中國(guó)再次開啟了二元經(jīng)濟(jì)向一元經(jīng)濟(jì)的過(guò)渡。2004年后,中國(guó)開始出現(xiàn)了民工荒,農(nóng)民工工資拐點(diǎn)此拐點(diǎn)并非數(shù)學(xué)微積分中的拐點(diǎn)。當(dāng)前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學(xué)界將數(shù)學(xué)中的極值點(diǎn)稱為拐點(diǎn),本文只能跟隨“約定俗成”,將極大值點(diǎn)稱為向下拐點(diǎn),而將極小值點(diǎn)稱為向上拐點(diǎn)。
在何時(shí)出現(xiàn)成為理論熱點(diǎn)。游松[1]研究發(fā)現(xiàn)在拐點(diǎn)的討論中,有23位中國(guó)學(xué)者認(rèn)為劉易斯的二元工資理論適用于中國(guó)。
依據(jù)Lewis[2]對(duì)其模型的表述(如圖1所示):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第一階段,由于農(nóng)業(yè)部門劉易斯對(duì)此部門有多種表述:生存部門、農(nóng)業(yè)部門和傳統(tǒng)部門等,本文采用農(nóng)業(yè)部門。存在著大量剩余勞動(dòng)力,工資的決定機(jī)制是古典機(jī)制:農(nóng)業(yè)部門勞動(dòng)力的收入僅能維持生存,稱為生存工資——它構(gòu)成城市部門的工資下限。當(dāng)城市邊際勞動(dòng)生產(chǎn)率(用曲線N表示)提高時(shí)工資不變,因而工資有一個(gè)水平線段,直到有一天“資本積累趕上人口,以至于不再有剩余勞動(dòng)力時(shí)” [2],經(jīng)濟(jì)進(jìn)入了第二階段,此后,工資由新古典機(jī)制決定。勞動(dòng)力的實(shí)際使用量與工資水平組成的平面散點(diǎn)圖就是圖1的劉易斯模型。這條曲線實(shí)質(zhì)上是工資的時(shí)間路徑,而不是勞動(dòng)供給曲線。
自劉易斯工資理論問(wèn)世以來(lái),學(xué)界在兩個(gè)方向劉易斯模型的所有表述均來(lái)自Fields的總結(jié),請(qǐng)參見參考文獻(xiàn)[3]。對(duì)該理論提出異議:一個(gè)是以Rosenzweig[4]為首,眾多新古典主義學(xué)者參與的對(duì)“無(wú)限彈性”的質(zhì)疑,形成了“勞動(dòng)供給曲線有限彈性”的理論分析和豐富的數(shù)據(jù)實(shí)證文獻(xiàn);另一個(gè)是受到 Fields[5]稱贊的“生存部門的收入將隨著勞動(dòng)力轉(zhuǎn)移而逐步提高”的理論,胡景北Leeson對(duì)此問(wèn)題的見解比胡景北更深刻,請(qǐng)參見參考文獻(xiàn)[6]。
收稿日期:20141201
基金項(xiàng)目:國(guó)家社會(huì)科學(xué)基金項(xiàng)目“二次人口紅利與經(jīng)濟(jì)持續(xù)增長(zhǎng)路徑研究”(12BJL027);教育部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項(xiàng)目“劉易斯模型的中國(guó)動(dòng)態(tài)特征與結(jié)構(gòu)型通脹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機(jī)制”(12YJA790112)
作者簡(jiǎn)介:宋建軍(1955-),男,遼寧大連人,教授,主要從事經(jīng)濟(jì)學(xué)理論研究。Email:songgg110@126com對(duì)這種理論給出了數(shù)理和幾何模型描述。
本文采用盧鋒[7]和童玉芬[8]提供的數(shù)據(jù)制成圖2。比較圖1和圖2筆者發(fā)現(xiàn):第一,中國(guó)不存在劉易斯所設(shè)想的平直工資線段。第二,胡景北對(duì)中國(guó)農(nóng)民工工資曲線的判斷也不成立,工資并不隨農(nóng)民工的規(guī)模增長(zhǎng)而增長(zhǎng)。中國(guó)農(nóng)民工規(guī)模在達(dá)到4 000萬(wàn)人后,工資不僅不上升,反而下降,然后反復(fù)回升和下降,直到1016億人之后才開始緩慢上升。第三,中國(guó)農(nóng)民工工資不僅存在拐點(diǎn),而且有多個(gè)拐點(diǎn);不僅存在向上拐點(diǎn)(4個(gè)),而且還有向下拐點(diǎn)(5個(gè))。
中國(guó)工資曲線向下運(yùn)動(dòng)表明:農(nóng)民工工資在生存工資之上。這一判斷符合實(shí)際,國(guó)家統(tǒng)計(jì)局首次公布的1985年中國(guó)貧困線標(biāo)準(zhǔn)為年收入206元,假定一個(gè)勞動(dòng)力擔(dān)負(fù)三個(gè)人的生活費(fèi)用(按中國(guó)統(tǒng)計(jì)年鑒統(tǒng)計(jì)的人口和勞動(dòng)力數(shù)據(jù)所確定的平均值,中國(guó)勞動(dòng)力平均負(fù)擔(dān)的人口不足兩個(gè)),那么,按貧困線的設(shè)定方法,“生存工資”應(yīng)該在636元之下。而1985年農(nóng)民工年工資可以負(fù)擔(dān)675個(gè)貧困人口,是1984—2010年26年間可負(fù)擔(dān)貧困人口最少的一個(gè)年份。從實(shí)際情況可知,中國(guó)農(nóng)民工工資從1984年開始就一直高于生存工資,即拐點(diǎn)出現(xiàn)在1984年之前,但全世界公認(rèn),21世紀(jì)之前中國(guó)農(nóng)村存在著數(shù)以億計(jì)的剩余勞動(dòng)力。這就是說(shuō),按劉易斯模型,中國(guó)農(nóng)民工在20世紀(jì)的收入最多不應(yīng)超過(guò)生存工資的40%,而現(xiàn)實(shí)的工資卻在生存水平的100%以上!
那么,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中國(guó)農(nóng)民工工資實(shí)際數(shù)據(jù)是支持劉易斯模型,還是支持胡景北模型?中國(guó)農(nóng)民工工資曲線的多個(gè)拐點(diǎn)表明,農(nóng)民工工資在生存工資之上多次反復(fù)升降。由此人們自然要問(wèn):為什么中國(guó)農(nóng)民工的工資曲線有這種特殊的形狀?中國(guó)農(nóng)民工工資決定機(jī)制是不是與現(xiàn)有的二元經(jīng)濟(jì)模型完全不同?
下面,筆者就從中國(guó)的實(shí)際情況出發(fā)來(lái)描述中國(guó)經(jīng)濟(jì)條件的特殊性,并由此提出能夠解釋上述路徑和農(nóng)民工工資決定機(jī)制特殊性的分析框架。
二、中國(guó)農(nóng)村“制度工資”與農(nóng)民工的供給曲線
劉易斯標(biāo)準(zhǔn)模型的農(nóng)民收入是由平均勞動(dòng)產(chǎn)品決定的“制度工資”,特點(diǎn)是在前期(拐點(diǎn)前)勞動(dòng)邊際產(chǎn)值為零,費(fèi)景漢和拉尼斯[9]進(jìn)一步闡述了這種制度,并給出了一些證據(jù)。中國(guó)農(nóng)村在改革開放初期雖然也存在著“制度工資”,但這種制度與劉易斯、費(fèi)景漢和拉尼斯所設(shè)想的制度迥然不同。具體講,中國(guó)農(nóng)村的“制度工資”有五個(gè)基本的經(jīng)濟(jì)內(nèi)涵:第一,基本“工資”由土地?cái)?shù)量Q和質(zhì)量M決定,土地不能買賣。第二,每個(gè)村的土地?cái)?shù)量Q以土地改革時(shí)期本村的土地?cái)?shù)量為限,基本保持不變。每個(gè)家庭的可使用土地規(guī)模(稱為承包土地?cái)?shù)量)由土地?cái)?shù)量Q與分配土地時(shí)(不同村分配土地的時(shí)間不同)全村人口W的比值Q/W確定。第三,在土地上經(jīng)營(yíng)的收入歸承包者所有,承包者具有土地的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和經(jīng)營(yíng)項(xiàng)目的選擇權(quán),他們不僅可以種植,也可以養(yǎng)殖,而且土地表層的礦物也屬于承包者
(深層不屬于)。第四,承包者沒有出售和購(gòu)買土地的權(quán)力,土地不能交易,但有出租的權(quán)力(稱為“流轉(zhuǎn)”)。在中國(guó)農(nóng)村,土地與勞動(dòng)力不能按市場(chǎng)效率結(jié)合。第五,農(nóng)民可以進(jìn)城打工,但農(nóng)民的身份不能改變,因而不能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
這五個(gè)基本內(nèi)涵導(dǎo)致中國(guó)農(nóng)民收入不僅各不相同,而且差距巨大。第一,每個(gè)村的土地面積各不相同,而且不能改變。由于每個(gè)村的人口增長(zhǎng)率和初始的土地面積各不相同,有的村及家庭的土地很多,而另一些村和家庭的土地?cái)?shù)量極少。黑龍江撫遠(yuǎn)縣撫遠(yuǎn)鎮(zhèn)人均良田352畝,而廣東連南瑤族自治縣三排鎮(zhèn)老排村人均耕地兩分[10]。第二,每個(gè)村的土地肥沃程度各不相同。有的地區(qū)是完全的山區(qū)(只能在山上開墾非常瘠薄的土地),有的地區(qū)全部是草場(chǎng),有的地區(qū)全部是沙土。地少和地貧的地區(qū)勞動(dòng)力顯著過(guò)剩,但只要有“地”的村,每個(gè)家庭就都有“地”(有水的地方分水面,有沙的地方分沙地,有草原的地方分草地)。第三,每個(gè)村土地的屬性各不相同。土地這一生產(chǎn)要素不能只理解為具有面積和肥沃程度兩種指標(biāo)的耕地。按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概念,土地是指自然資源。湖北孝感市劉垸村的石膏資源使全村都經(jīng)營(yíng)粉筆加工,一村的粉筆產(chǎn)量占了全國(guó)的80%,年收入3億元。全國(guó)的寶石村、水晶村和玉石村都是聞名的高收入村。除了礦產(chǎn)外,土質(zhì)、氣候和環(huán)境也是“土地”這一要素的內(nèi)容。竹筍、茶葉、銀杏、可可和各種特殊的水果都需要特殊的土壤、環(huán)境和氣候。特殊的土壤、環(huán)境、氣候和土地上的礦產(chǎn)資源也是土地的“質(zhì)量”。
總之,農(nóng)村在改革開放初期確定了一種土地制度,這一制度使各省、市甚至不同鎮(zhèn)和村的農(nóng)民承包的土地?cái)?shù)量和質(zhì)量(肥沃程度與屬性)各不相同。毫無(wú)疑問(wèn),所有農(nóng)民只能按承包土地的實(shí)際產(chǎn)出量獲得產(chǎn)品,也就是說(shuō),這種承包制實(shí)際上是一種“工資制度”。這種工資制度實(shí)行的結(jié)果必然是幾乎所有村的收入各不相同(在一個(gè)鎮(zhèn)或村可能相近)。
眾所周知,劉易斯依據(jù)生存工資制度確定了圖1這樣的工資路徑。那么,為何中國(guó)農(nóng)村這種特殊的“工資制度”會(huì)確定一條像圖2那樣的工資路徑?下面本文就從勞動(dòng)供給曲線的推導(dǎo)開始,展開這個(gè)前提與結(jié)果的分析。
假定貴州德江縣長(zhǎng)堡鄉(xiāng)大坡村是全國(guó)農(nóng)業(yè)產(chǎn)值人均最少的村A,廣西的某個(gè)村B比A的人均產(chǎn)值稍多一些,而云南的C村又比B村稍多一些,以此類推,并假定湖北安陸王義鎮(zhèn)錢沖村是改革開放初期全國(guó)農(nóng)業(yè)產(chǎn)
值最高的村。全國(guó)共有65萬(wàn)個(gè)行政村,100多萬(wàn)個(gè)自然村,100多萬(wàn)個(gè)村按每村人均土地產(chǎn)值的大小進(jìn)行從低到高在圖上按順序排列,得到一個(gè)橫軸為勞動(dòng)力(每個(gè)村的勞動(dòng)力數(shù)量用一段小線段代替,但65萬(wàn)個(gè)小線段在這樣小的圖上只能是一個(gè)點(diǎn)),縱軸為人均土地產(chǎn)值的平面散點(diǎn)圖(如圖3所示)。
圖3曲線上每一個(gè)點(diǎn)對(duì)應(yīng)著一個(gè)村的人均產(chǎn)值和勞動(dòng)力數(shù)量。如果城市工廠給出的年度工資是W,X點(diǎn)前面所有村的土地年收入都小于W,故有L那么多的農(nóng)民工愿意進(jìn)城。可見,圖3實(shí)際上(按定義)就是中國(guó)農(nóng)民工的供給曲線(同時(shí)也是工資曲線一條曲線可以同時(shí)代表兩個(gè)函數(shù):工資函數(shù)和勞動(dòng)力供給函數(shù),其原因是這條曲線是單調(diào)上升的。
由此本文得出:
結(jié)論1:中國(guó)農(nóng)民工的供給曲線是一條向上傾斜的曲線。
顯然,城市對(duì)農(nóng)民工的需求曲線與農(nóng)民工供給曲線的交點(diǎn)決定名義的農(nóng)民工工資。如果我們假定W是生存工資,而L是生存工資所對(duì)應(yīng)的勞動(dòng)力數(shù)量,那么,根據(jù)上述供給曲線傾斜的結(jié)論,超過(guò)L的勞動(dòng)力需求必然要求高于生存工資的工資。即只要農(nóng)民工的規(guī)模超過(guò)了貧困人口中所包含的勞動(dòng)力數(shù)量,農(nóng)民工工資就必須高于生存工資(本文假定為三倍貧困線)。前面我們已經(jīng)證明了中國(guó)農(nóng)民工工資高于生存工資,由此可以推定:城市對(duì)農(nóng)民工的實(shí)際需求超過(guò)生存工資所決定的需求數(shù)量。
據(jù)胡鞍鋼等[12]的統(tǒng)計(jì),1985年中國(guó)貧困人口為1億人(農(nóng)民在1984年才開始自由進(jìn)城,1984年以前因政府對(duì)勞動(dòng)力流動(dòng)的阻止,實(shí)際能進(jìn)城的農(nóng)民工更少),其中的勞動(dòng)力不超過(guò)5 000萬(wàn)人,而這一年的農(nóng)民工規(guī)模6 000萬(wàn)人左右,非農(nóng)勞動(dòng)力轉(zhuǎn)移為6 714萬(wàn)人。可見,結(jié)論1與事實(shí)相符。
三、中國(guó)農(nóng)村勞動(dòng)力Λ集合與工資曲線的左平移
費(fèi)景漢和拉尼斯[13]模型(以下簡(jiǎn)稱費(fèi)-拉模型)沿用劉易斯的基本假設(shè),但有一些修改。他們假定農(nóng)業(yè)部門是一種佃農(nóng)制度下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在這種制度下,土地要素收入全部歸地主所有,農(nóng)民只能拿到勞動(dòng)的邊際產(chǎn)品和由最低生活水平(生存工資)決定的平均產(chǎn)品。該模型還假定,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到任一時(shí)刻,原來(lái)農(nóng)業(yè)的勞動(dòng)力集合Ω將分成兩個(gè)部分:一部分留在農(nóng)業(yè)部門繼續(xù)從事農(nóng)業(yè)勞動(dòng),可命名為集合Ω1;另一部分進(jìn)入城市打工,稱為工人,可將其命名為集合Ω2,由模型的圖4可知Ω1+Ω2=Ω。當(dāng)勞動(dòng)力轉(zhuǎn)移的人數(shù)L在C與L1之間時(shí),人均產(chǎn)值因L的減少本應(yīng)增加,但地主拿走土地要素的增值部分,農(nóng)民因勞動(dòng)的邊際產(chǎn)值仍然等于零,故人均收入保持不變。
胡景北[14-15]不同意費(fèi)景漢和拉尼斯的觀點(diǎn),他認(rèn)為土地要素收入也歸農(nóng)民,農(nóng)民收入是全部農(nóng)業(yè)產(chǎn)出的人均產(chǎn)值Y/L,農(nóng)民離開土地成為農(nóng)民工之后,雖然L減少,但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出不減,故Y/L的分母縮小,平均收入從初始時(shí)刻起就逐步上升(如圖5所示),從而否定了劉易斯拐點(diǎn)理論。
胡景北在首次指出中國(guó)農(nóng)民收入的特殊性,對(duì)二元經(jīng)濟(jì)理論有重大貢獻(xiàn),但他仍然沿用費(fèi)-拉模型的兩集合假定,明確地將農(nóng)業(yè)和工業(yè)的勞動(dòng)力數(shù)量定義為A1和A2,A1+A2=L0。
根據(jù)圖4和圖5的形狀可知:如果一個(gè)農(nóng)民屬于Ω1,則該農(nóng)民的收入s 三個(gè)二元經(jīng)濟(jì)模型的比較(如圖6所示):其中白色方格是費(fèi)-拉模型的農(nóng)業(yè)勞動(dòng)力數(shù)量OL1和總產(chǎn)出OB;劉易斯模型是由白色和陰影兩個(gè)方格組成的整個(gè)長(zhǎng)方格。(1)劉易斯模型在初始時(shí)刻的勞動(dòng)力總數(shù)L0超出了弗-拉模型的L1。(2)集合Ω的人數(shù)L1是一個(gè)固定值;集合Π的人數(shù)L0-L1不僅是人口變量的函數(shù),而且還是婦女、童工以及國(guó)外移民等變量的函數(shù)。(3)費(fèi)-拉模型的短缺點(diǎn)因存在地主階級(jí),在邊際勞動(dòng)大于零時(shí)出現(xiàn)。而劉易斯雖然沒有提到地主階級(jí),但提到了自耕農(nóng),因而短缺點(diǎn)在CH之間。若沒有地主階級(jí),則短缺點(diǎn)與H點(diǎn)重合。
然而,在中國(guó),留在農(nóng)業(yè)部門的農(nóng)民收入未必少于農(nóng)民工工資。2012年,筆者考察了廣東郁南縣種植沙糖橘的農(nóng)民,他們的家庭年收入通常在7—8萬(wàn)元,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打工者的年收入。從全國(guó)看,(1)經(jīng)營(yíng)漁業(yè)和牧業(yè)的農(nóng)民收入超出進(jìn)城打工收入。(2)陜西、新疆和遼寧地區(qū)的水果,山東壽光縣的蔬菜,廣東、廣西和四川種植茘枝等高檔水果的農(nóng)民,收入都高于農(nóng)民工。(3)東北和云南等地種植中藥(人參、田七和當(dāng)歸等)的農(nóng)民收入高于農(nóng)民工。然而,根據(jù)上述Ω1和Ω2兩個(gè)集合的定義,這些收入超過(guò)農(nóng)民工的龐大農(nóng)民群體,既不屬于Ω1,也不屬于Ω2,但同時(shí)他們又是農(nóng)民,因而屬于Ω。這表明,在中國(guó)農(nóng)村勞動(dòng)力中還存在著另一個(gè)集合,本文將其命名為Λ。也就是說(shuō),如果不考慮新增的勞動(dòng)力,那么,中國(guó)的農(nóng)村勞動(dòng)力由三個(gè)集合構(gòu)成,Ω1+Ω2+Λ=Ω。而費(fèi)-拉模型和胡景北模型是Ω1+Ω2=Ω,缺少一個(gè)真實(shí)的農(nóng)民群體Λ。
本文的模型很好地描述了這一群體,在中國(guó)農(nóng)民工供給曲線(如圖3所示)上,收入在W點(diǎn)以下的農(nóng)村勞動(dòng)力都在X點(diǎn)左邊;而X點(diǎn)右邊的所有農(nóng)村勞動(dòng)力收入高于農(nóng)民工,可以稱為“高收入”農(nóng)民,屬于集合Λ。
由此可見,中國(guó)農(nóng)村勞動(dòng)力與上述兩個(gè)模型的勞動(dòng)力不同,他們不是單向流入城市,也“流向”Λ集合。這一運(yùn)動(dòng)方向,導(dǎo)致中國(guó)Λ集合的農(nóng)民總數(shù)和比率都在持續(xù)地變動(dòng)。
從收入差距看,種植蔬菜的收入通常高于種植糧食(對(duì)于地少的農(nóng)民更是如此);種植水果的收入可能高于種植蔬菜;養(yǎng)殖牛羊的收入通常高于種植水果;養(yǎng)殖水產(chǎn)品的收入可能高于養(yǎng)殖牛羊。總而言之,在農(nóng)業(yè)內(nèi)部,事實(shí)上存在著一種不同收入的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如果我們將更高收入的種養(yǎng)品種視做更高級(jí)的產(chǎn)業(yè),那么,可以肯定,在中國(guó)農(nóng)業(yè)內(nèi)部存在著一種非常明顯的產(chǎn)業(yè)升級(jí)運(yùn)動(dòng)。
從歷史過(guò)程看,改革開放前,政府要求“以糧為綱”,絕大部分農(nóng)民種植糧食。改革開放后,農(nóng)民獲得了經(jīng)營(yíng)形式的選擇權(quán),越來(lái)越多的農(nóng)民為爭(zhēng)取更多收入而不斷地改變種植或養(yǎng)殖品種,從低收入產(chǎn)業(yè)轉(zhuǎn)向高收入產(chǎn)業(yè)。農(nóng)村的行政部門也努力推進(jìn)這種產(chǎn)業(yè)升級(jí),許多地區(qū)甚至是政府主導(dǎo)的產(chǎn)業(yè)升級(jí)。
事實(shí)上,農(nóng)民的經(jīng)營(yíng)不僅是土地的管理,還包括對(duì)資本的運(yùn)用。而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學(xué)中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力資本。中國(guó)農(nóng)村的人力資本展現(xiàn)出一種完全不同于舒爾茨描述的人力資本分布結(jié)構(gòu)。由于13億人口的巨大市場(chǎng),與現(xiàn)代技術(shù)和教育無(wú)關(guān)的傳統(tǒng)手工藝,使拉尼斯稱之為Z商品的各種生活和娛樂用品(例如風(fēng)箏、年畫、刺繡和竹制品等)都有可觀的銷路,從而成為致富的來(lái)源。而這種生產(chǎn)并不是現(xiàn)代工業(yè),它仍然在農(nóng)村,實(shí)際上仍然是農(nóng)業(yè)的一個(gè)組成部分,過(guò)去,這個(gè)部分稱為農(nóng)村中的副業(yè)。由于副業(yè)的經(jīng)營(yíng)者也耕種土地,因而在統(tǒng)計(jì)上(按六個(gè)月時(shí)間計(jì)算)絕大部分勞動(dòng)者仍然被統(tǒng)計(jì)在農(nóng)業(yè)中。總之,Λ集合正在持續(xù)地從Ω1集中抽走勞動(dòng)力,產(chǎn)業(yè)升級(jí)在不同的方向展開。
從圖3可以看出,如果在X點(diǎn)前面的中國(guó)農(nóng)民中,有一部分(X-Y個(gè)人)收入提高到W以上,那么,進(jìn)入城市的農(nóng)民工必然相應(yīng)地減少,勞動(dòng)力供給曲線將從Y點(diǎn)而不是X點(diǎn)超過(guò)W,這表明,如果集合Λ的人數(shù)增加,則中國(guó)農(nóng)民工的供給曲線的曲率將增加,但農(nóng)業(yè)的產(chǎn)業(yè)升級(jí)并不是只出現(xiàn)在富裕的地區(qū),貧困地區(qū)依靠升級(jí)致富的例子層出不窮。因此,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升級(jí)對(duì)農(nóng)民工供給曲線變動(dòng)的影響最好理解成向左平移(雖然曲率也會(huì)提高)。
根據(jù)上述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升級(jí)的特點(diǎn),本文得出:
結(jié)論2:Λ集合勞動(dòng)力的增加使中國(guó)農(nóng)民工的供給曲線向左上方平移,從而成為工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隨著農(nóng)村產(chǎn)業(yè)的持續(xù)升級(jí)、土地流轉(zhuǎn)制度的完善和投入農(nóng)業(yè)的金融資本逐漸增多,集合Λ的勞動(dòng)力數(shù)量還將繼續(xù)擴(kuò)大。農(nóng)民工供給曲線將會(huì)加速向左平移。
四、農(nóng)村新增勞動(dòng)力與農(nóng)民工供給曲線的右平移
前面我們討論了中國(guó)農(nóng)民收入與農(nóng)民工供給曲線的關(guān)系,得出供給曲線向左平移的結(jié)論,而隨著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農(nóng)村的產(chǎn)業(yè)不斷升級(jí),人們必然得出工資持續(xù)增長(zhǎng),因而沒有拐點(diǎn)的結(jié)論,但是,中國(guó)農(nóng)民工實(shí)際的工資路徑確實(shí)有許多拐點(diǎn)(如圖2所示),這又是什么原因呢?
前面提到胡景北用農(nóng)民全部是自耕農(nóng)的模型否認(rèn)了劉易斯拐點(diǎn)的存在。其實(shí)劉易斯在1954年、1958年和1972年的三篇文章中都提到了自耕農(nóng)平均收入與城市工資的關(guān)系。可見,劉易斯預(yù)見了胡景北模型情況的發(fā)生。那么,在這種情況下為什么還可能會(huì)出現(xiàn)不變工資和拐點(diǎn)呢?劉易斯[16]指出:“在我的模型中,最初階段非資本主義部門的勞動(dòng)力人數(shù)仍然在增長(zhǎng)……勞動(dòng)力增加的原因可以歸因于人口的增長(zhǎng)、婦女就業(yè)的增加,以及移民”。也就是說(shuō),費(fèi)-拉模型和胡景北模型中,集合Ω中的人數(shù)L1是一個(gè)不變的常數(shù)[6];而劉易斯模型中的勞動(dòng)力除了集合Ω之外,還有一個(gè)新增的勞動(dòng)力集合,本文用Π表示這一集合。劉易斯使用馬克思的概念,將集合Π稱為“勞動(dòng)力蓄水池”,即圖6中的陰影部分。因此,劉易斯模型中的勞動(dòng)力總數(shù)L0是一個(gè)可變量。
劉易斯的觀點(diǎn)很明確,只要Π集合的勞動(dòng)力增長(zhǎng)得足夠快,即使農(nóng)業(yè)部門全部由自耕農(nóng)組成,如果沒有技術(shù)的變革和資本的投入(產(chǎn)業(yè)升級(jí)實(shí)際上也是資本投入的結(jié)果),當(dāng)勞動(dòng)力向城市轉(zhuǎn)移時(shí),也不會(huì)出現(xiàn)農(nóng)民的全要素收入上升。因?yàn)閺霓r(nóng)村轉(zhuǎn)移出的勞動(dòng)力可能直接來(lái)自于新增的勞動(dòng)力集合Π,從而使Ω1集的農(nóng)民沒有減少;或耕種的勞動(dòng)力轉(zhuǎn)移之后,來(lái)自Π的新增勞動(dòng)力又補(bǔ)充到Ω1集,使耕種人數(shù)保持不變,因而平均收入保持不變,水平工資保持不變,模型保持不變。也就是說(shuō),劉易斯認(rèn)為Π集合可以為農(nóng)村補(bǔ)充新的勞動(dòng)力,從而使胡景北的全要素平均收入也不能提高。
那么,中國(guó)農(nóng)業(yè)部門是否存在劉易斯的新增勞動(dòng)力集合Π呢?回答是肯定的,表1表明了這種情況。中國(guó)Π集合人數(shù)(鄉(xiāng)村就業(yè)人員增量)在1990年之前一直處于上升階段,1991年后保持平穩(wěn),但增量仍然維持在200—300萬(wàn)人,1997年之后不再增長(zhǎng),并在1998年后開始出現(xiàn)負(fù)增長(zhǎng)。
從Ω1集(農(nóng)業(yè)勞動(dòng)力)看,除1986年之外,直到1991年都是正增量。即Ω1集的人數(shù)是增加的,盡管在此期間,農(nóng)民工Ω2不斷地從農(nóng)村抽出勞動(dòng)力,但Ω1集仍然維持著正的增量。從圖7可以看出,1987—1992年農(nóng)業(yè)勞動(dòng)力增量和農(nóng)民工就業(yè)增量同時(shí)為正值,即Ω1和Ω2同時(shí)增長(zhǎng),而其勞動(dòng)力的來(lái)源顯然是農(nóng)村勞動(dòng)力總數(shù)的增長(zhǎng),是Π集合同時(shí)向Ω1和Ω2兩個(gè)集合補(bǔ)充新勞動(dòng)力。1989年Ω1集在達(dá)到最高峰的8 611萬(wàn)人后開始減少,但從1997年再次轉(zhuǎn)向正增量,直到2002年才開始出現(xiàn)負(fù)增量。可見,中國(guó)農(nóng)業(yè)部門勞動(dòng)力人數(shù)是變動(dòng)的,集合Ω1不僅能被補(bǔ)充,而且經(jīng)常是過(guò)分地補(bǔ)充。雖然Ω1集的勞動(dòng)力不一定來(lái)自Π集合,農(nóng)民工(Ω2)返回農(nóng)村經(jīng)營(yíng)農(nóng)業(yè)也會(huì)增加農(nóng)業(yè)勞動(dòng)力數(shù)量(Ω1回流Ω2),但只在1981年、1989年和2008年三年出現(xiàn)過(guò)返回,返回的人數(shù)很少。中國(guó)的數(shù)據(jù)驗(yàn)證了劉易斯勞動(dòng)力儲(chǔ)水池理論的正確性。
根據(jù)上述理論和中國(guó)農(nóng)民工工資數(shù)據(jù),本文得出:
結(jié)論3: Π集合勞動(dòng)力的增加是中國(guó)農(nóng)民工的供給增加及供給曲線向右平移的主要原因。
另外,從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看,中國(guó)新增勞動(dòng)力的變化在20世紀(jì)90年代以前只與若干年(15年)前的人口出生率有關(guān),但90年代后出現(xiàn)了城市化對(duì)郊區(qū)農(nóng)民從農(nóng)業(yè)的剝離。1999年開始,中國(guó)高校又開始擴(kuò)招。在計(jì)劃生育效果、郊區(qū)勞動(dòng)力剝離和高校擴(kuò)招的聯(lián)合作用下,鄉(xiāng)村就業(yè)人員增長(zhǎng)率持續(xù)遞減,2002年開始出現(xiàn)負(fù)值并持續(xù)至今。盡管中國(guó)Π集合擴(kuò)張和縮減的原因與劉易斯的設(shè)想略有不同,但對(duì)勞動(dòng)力供給曲線作用的方式和效果是一樣的。
五、供給曲線平移效果與需求曲線平移效果的合成
總結(jié)前面的討論:費(fèi)-拉模型和胡景北模型只將農(nóng)民分為兩個(gè)集合,而劉易斯模型卻是三個(gè)集合。中國(guó)不但存在劉易斯的三個(gè)集合,還有Λ集合,因而中國(guó)農(nóng)村勞動(dòng)力由四個(gè)集合構(gòu)成。四個(gè)集合的變化從不同方向移動(dòng)了勞動(dòng)力供給曲線。
圖8 中國(guó)農(nóng)民工供給曲線的移動(dòng)如果沒有Λ集合的作用,Π集合的增長(zhǎng)會(huì)將勞動(dòng)供給曲線從S0右移至S2(如圖8所示);而如果沒有Π集合的作用,Λ集合對(duì)農(nóng)村勞動(dòng)力的“轉(zhuǎn)移”就會(huì)將勞動(dòng)供給曲線從S0向左移動(dòng)至S1。兩種作用同時(shí)發(fā)生就會(huì)相互抵消其中的一部分。那么抵消之后是向左還是向右呢?
從具體情況看,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升級(jí)速度不是很顯著,而勞動(dòng)力的增長(zhǎng)速度驚人,1985—1990年鄉(xiāng)村就業(yè)人數(shù)增加了1個(gè)億多,1991—1997年,鄉(xiāng)村就業(yè)人數(shù)仍然在增加。因此,1985—1997年Π集合的作用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Λ集合的作用。
但勞動(dòng)力供給不能單獨(dú)決定工資,工資是供給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中國(guó)農(nóng)民工工資由Π集合、Ω1集合和Λ集合三個(gè)集合與一個(gè)需求集Ω2集合(農(nóng)民工規(guī)模)共同決定。1984—1985年,1992—1993年和2007年出現(xiàn)了三次農(nóng)民工規(guī)模的突增,對(duì)應(yīng)于1984年、1992年和2007年工資的三次大幅度增加,顯然這三次都是勞動(dòng)力需求拉動(dòng)的結(jié)果。
雖然Λ集合沒有統(tǒng)計(jì)數(shù)字,但對(duì)工資的影響也有體現(xiàn)。因?yàn)棣虾挺?集合的勞動(dòng)力都從事農(nóng)業(yè),所以兩集合人數(shù)之和才是農(nóng)業(yè)勞動(dòng)力人數(shù)。而在圖7中,1999年農(nóng)民工的工資大幅度上升了60%,但這一年的農(nóng)民工規(guī)模并沒有大幅度上升,這說(shuō)明工資上升的原因不是來(lái)自工業(yè)對(duì)勞動(dòng)力需求的增加。其原因只有兩個(gè):或是農(nóng)村勞動(dòng)力總數(shù)減少,或是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升級(jí)。而從圖7可以看出,這一年農(nóng)村勞動(dòng)力總數(shù)呈正增量,因而工資上升的原因只能是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的升級(jí)。
從歷史過(guò)程看,中國(guó)農(nóng)民工工資路徑明顯地分成兩個(gè)階段:在1998年之前,中國(guó)的Π集合作用力大于Λ集合。將勞動(dòng)供給曲線由S0推至S′0的位置,此時(shí)的工資本應(yīng)該下降,但是,由于工業(yè)擴(kuò)張需要更多的勞動(dòng)力,Ω2集合始終處于正增量,需求曲線D0移至D′0,從而使工資保持相對(duì)穩(wěn)定。因此,在1984—1998年工資在一個(gè)中心點(diǎn)之間擺動(dòng)(如圖7所示)。
但1999年以后,形勢(shì)出現(xiàn)了根本性的變化,Π集合不再發(fā)揮其向右移動(dòng)供給曲線的作用(如表1所示),即農(nóng)民工供給曲線不再向右移動(dòng)。2001年,Π集合不僅不增加供給,反而縮減,當(dāng)年突然縮減200多萬(wàn)人,而就在此時(shí),城市對(duì)農(nóng)民工需求也開始加大增速(見圖7中的棱形點(diǎn)),即農(nóng)民工的需求曲線加速向右移動(dòng)。2003年,Λ集合作用力也突然增強(qiáng),升級(jí)的速度明顯加快,農(nóng)民工供給曲線持續(xù)向左移動(dòng)。這三種運(yùn)動(dòng)合成的結(jié)果就是農(nóng)民工工資加速上升。
六、中國(guó)農(nóng)民工工資機(jī)制的特殊性
我們?cè)谥袊?guó)農(nóng)民工工資高于生存工資和中國(guó)農(nóng)民收入包含土地要素收入和經(jīng)營(yíng)性收入的前提條件下,提出了中國(guó)農(nóng)民工工資機(jī)制的比較靜態(tài)模型。那么,中國(guó)這種農(nóng)民工工資機(jī)制有沒有特殊性,它是不是某個(gè)二元經(jīng)濟(jì)模型的特例呢?下面我們考察二元經(jīng)濟(jì)模型與中國(guó)農(nóng)民工工資機(jī)制的關(guān)系。
1劉易斯模型和費(fèi)-拉模型
劉易斯模型和費(fèi)-拉模型中有一個(gè)基本的原理——“農(nóng)民的平均(或人均)收入決定工業(yè)工資”。而這一原理是建立在農(nóng)民收入是平均產(chǎn)出同時(shí)也是“生存工資”的前提下。顯然,如果存在著部分農(nóng)民收入高于生存工資,那么,平均收入就會(huì)高于生存工資,于是平均收入與生存工資就成為兩個(gè)不同的值,此時(shí)工業(yè)工資應(yīng)該由哪個(gè)值決定呢?
如果農(nóng)民的收入有差距,那么,依據(jù)收入差距必然能夠通過(guò)排序得到遞增的收入曲線,低于平均水平的工資仍會(huì)有愿意就業(yè)的勞動(dòng)力,當(dāng)工業(yè)對(duì)工人的需求少于平均水平?jīng)Q定的勞動(dòng)力數(shù)量時(shí),在低于平均收入工資水平的某一工資上可能已經(jīng)能夠招到足夠數(shù)量的勞動(dòng)力。此時(shí)的工資沒有必要等于平均收入。反過(guò)來(lái),當(dāng)招收工人的數(shù)量較多時(shí),工資又必須高于平均收入,否則,也無(wú)法保證所需要的工人數(shù)量了。可見,在農(nóng)民收入有差距的情況下,平均收入不能決定工業(yè)工資。
平均收入在邏輯上不能決定工業(yè)工資,而中國(guó)農(nóng)民工的實(shí)際工資又遠(yuǎn)遠(yuǎn)高于生存工資,即生存工資在實(shí)際上沒有決定工業(yè)工資。可見,平均收入和生存工資都不能決定中國(guó)農(nóng)民工工資。因此,劉易斯模型完全不能套用中國(guó)的二元經(jīng)濟(jì)。
另外,根據(jù)劉易斯的表述,拐點(diǎn)的出現(xiàn)有兩個(gè)起因:一個(gè)是農(nóng)民的收入提高了,迫使城市的工資提高。另一個(gè)是“資本積累趕上人口,以至于不再有剩余勞動(dòng)力”,即勞動(dòng)力的需求大于供給。前一個(gè)起因是供給曲線的向上移動(dòng),但中國(guó)傾斜的供給曲線即使在初期有平直的部分,其拐點(diǎn)也是由曲線本身形狀決定的靜態(tài)拐點(diǎn)(曲線不移動(dòng),也存在拐點(diǎn))。后一個(gè)起因是工資開始由新古典機(jī)制決定,即(勞動(dòng)力稀缺導(dǎo)致的)勞動(dòng)邊際收入上升,推高了工資。然而,根據(jù)中國(guó)農(nóng)民工供給曲線方程,即使勞動(dòng)邊際收入不變,土地和資本的收入差距本身就要求工資隨勞動(dòng)力需求的增長(zhǎng)而提高!
應(yīng)該說(shuō)明的是:劉易斯模型包含著絕對(duì)真理的部分,即新增勞動(dòng)力集合的擴(kuò)張可能會(huì)使勞動(dòng)力供給曲線與需求曲線的交點(diǎn)(工資)在一段時(shí)期內(nèi)保持基本不變的可能性。正是由于中國(guó)農(nóng)民工工資路徑在20世紀(jì)90年代保持?jǐn)?shù)年的水平狀態(tài),才使很多學(xué)者確信劉易斯模型適用于中國(guó)。
2胡景北模型
胡景北模型雖然引進(jìn)了土地要素收入,但也不符合中國(guó)的實(shí)際情況。這是因?yàn)椋M管中國(guó)的土地要素收入歸農(nóng)民所有,但根據(jù)中國(guó)土地制度的規(guī)定,農(nóng)民外出打工后仍然保留著家庭土地收益權(quán),留守農(nóng)民不能得到家庭以外的土地收益,因而留守農(nóng)民家庭的平均土地收入不會(huì)因此提高。如果留守農(nóng)民租佃外出的農(nóng)民土地,那外出的農(nóng)民扮演的是費(fèi)-拉模型中地主的角色。
真正能夠得到土地要素收入的是家庭內(nèi)部成員,但外出打工人數(shù)增加并不是平均地分?jǐn)偟矫總€(gè)家庭。實(shí)際的情況是,外出的農(nóng)民經(jīng)常是家庭中全體勞動(dòng)力一起出動(dòng)。這種外出的方式導(dǎo)致留守農(nóng)民不能得到其他家庭的土地要素收入,但通過(guò)土地流轉(zhuǎn)能夠得到勞動(dòng)的邊際收入。可見,僅提出農(nóng)民有要素收入這一條件還不能否定劉易斯拐點(diǎn)理論,如果胡景北要否定劉易斯拐點(diǎn),還必須加上一個(gè)條件,即外出打工的農(nóng)民必須放棄土地承包權(quán)。但這也不符合中國(guó)的實(shí)際情況。
另外,目前部分地區(qū)的土地正向種糧大戶集中。由于那些大戶農(nóng)民原來(lái)就在圖3 X點(diǎn)的右邊,不影響X點(diǎn)左邊農(nóng)民的收入,雖然大戶農(nóng)民收入提高會(huì)導(dǎo)致平均收入提高,但愿意接受原來(lái)工資的農(nóng)民工數(shù)量不變,因而農(nóng)民工工資也不應(yīng)該發(fā)生變化。因此,種糧大戶能不能夠得到流轉(zhuǎn)土地的要素收入,與農(nóng)民工工資不是絕對(duì)關(guān)系。可見,胡景北的平均收入提高后工資應(yīng)該上升的結(jié)論還需再增加條件,例如土地不能集中流轉(zhuǎn)。
本文的工資曲線雖然也是單調(diào)向上的,但其原理不同于胡景北模型,單調(diào)遞增是農(nóng)民收入的差異性與農(nóng)業(yè)內(nèi)部產(chǎn)業(yè)的升級(jí)運(yùn)動(dòng)造成的,雖然產(chǎn)業(yè)升級(jí)也會(huì)形成土地要素邊際收入的提高,但不是要素集約使用造成的邊際收益提高。胡景北模型沒有考慮新增的農(nóng)村勞動(dòng)力,也使其解釋力不足。
3喬根森模型
Jorgenson[17]不同意劉易斯的“制度工資”,他認(rèn)為農(nóng)民的勞動(dòng)邊際收入應(yīng)該是正數(shù)。但是,他仍然沿用拉尼斯和費(fèi)景漢的佃農(nóng)制度和農(nóng)業(yè)使用的土地面積不變的假設(shè),土地要素被當(dāng)作一個(gè)常量而隱身于道格拉斯函數(shù)里。如此處理的結(jié)果是人均收入與勞動(dòng)力總?cè)藬?shù)形成函數(shù)關(guān)系,農(nóng)民人均收入在模型中扮演著核心變量的角色。其實(shí)劉易斯的方法也是如此。喬根森實(shí)際上是繼承了劉易斯建模方式。Leeson[17]對(duì)這一方法進(jìn)行了批判根據(jù)《理論與當(dāng)代》1995年第4期安商宣的調(diào)查(《跨越貧困線——來(lái)自兩村民組的調(diào)查》),貴州省德江縣長(zhǎng)堡鄉(xiāng)大坡村村民組20戶人家96人1989年年均收入37元。這一結(jié)果表明,中國(guó)的勞動(dòng)供給曲線也沒有平直的線段。,他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平均的概念可能導(dǎo)致歧途,平均工資可能上升,但最低的不變工資仍能刺激低收入階層進(jìn)行遷移”。
喬根森模型是一個(gè)完全的新古典模型,工資完全由供求決定,而勞動(dòng)力資源是稀缺的,因而農(nóng)業(yè)的勞動(dòng)邊際收入必然隨勞動(dòng)力的轉(zhuǎn)移而上升。然而,根據(jù)中國(guó)農(nóng)民工供給曲線方程,土地和資本收入差距本身也要求工資隨勞動(dòng)力需求的增長(zhǎng)而提高,可見,中國(guó)農(nóng)民工的工資機(jī)制,既不是劉易斯的古典,也不是Jorgenson[17]式的新古典!
事實(shí)上,上述四個(gè)二元理論都暗含了農(nóng)村(或生存部門)在任何時(shí)刻都有統(tǒng)一的勞動(dòng)“工資”,但中國(guó)農(nóng)民在初始時(shí)刻的“工資”就各不相同。這一基本的前提條件決定了中國(guó)現(xiàn)實(shí)的二元經(jīng)濟(jì)與上述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研究的樣本有質(zhì)的差別。
除了上述模型外,周天勇[18]早就指出著名的托達(dá)羅模型不適用于中國(guó),但托達(dá)羅模型研究的不是工資機(jī)制,因此不在本文討論的范圍內(nèi)。
那么,中國(guó)農(nóng)民工的供給曲線向上傾斜是不是證明了Rosenzweig觀點(diǎn)的正確性呢?回答也是否定的。Rosenzweig供給曲線向上傾斜的原因是存在著(查雅諾夫[18]提出的)農(nóng)民家庭勞動(dòng)和休閑替代彈性。雖然中國(guó)農(nóng)民工供給曲線的傾斜可能有替代彈性因素,但主要是生產(chǎn)三要素中的其他兩個(gè)要素的分配不均勻。
應(yīng)該說(shuō)明的是,這種農(nóng)民收入的差異性最早Field考察了這一思想的來(lái)源。由Leeson[6]在1979年提出,但他的農(nóng)村生存經(jīng)濟(jì)差異性指的是資本主義過(guò)程中產(chǎn)生的兩極分化結(jié)果,而不是初始時(shí)刻就由土地限定的產(chǎn)品分配制度。
七、結(jié) 語(yǔ)
本文用確鑿的事實(shí)證明了中國(guó)農(nóng)民工工資高于生存工資;并依據(jù)改革開放后的土地制度提出了中國(guó)農(nóng)民特殊的“工資制度”。在這種制度下,農(nóng)民分配的自然資源和其自身經(jīng)營(yíng)條件的差異性必然導(dǎo)致中國(guó)農(nóng)民收入的差異性,是這種收入差異性將中國(guó)農(nóng)民工工資軌跡塑造成一條單調(diào)遞增的曲線。
在高于生存水平的工資、收入包含土地要素收入和經(jīng)營(yíng)性收入的前提條件下,筆者提出了中國(guó)農(nóng)民工工資機(jī)制的比較靜態(tài)模型。農(nóng)民土地?cái)?shù)量和質(zhì)量的差異性導(dǎo)致了農(nóng)村產(chǎn)業(yè)升級(jí),技術(shù)和資本的使用以及政府的相關(guān)農(nóng)業(yè)政策成為產(chǎn)業(yè)升級(jí)的助推器。產(chǎn)業(yè)升級(jí)使農(nóng)村勞動(dòng)力出現(xiàn)了一個(gè)特殊的集合Λ,它的持續(xù)增長(zhǎng)導(dǎo)致工資曲線持續(xù)地向左上方移動(dòng)。然而在某一特定時(shí)期,由于滯后的人口增長(zhǎng)效果導(dǎo)致的農(nóng)村新增勞動(dòng)力集合Π增長(zhǎng)過(guò)快,農(nóng)民工供給曲線也會(huì)向右平移。供給曲線的形成特點(diǎn)和兩個(gè)方向的運(yùn)動(dòng)圓滿地解釋了圖2農(nóng)民工工資路徑的曲折軌跡。
與劉易斯、費(fèi)景漢和拉尼斯所設(shè)想的資本主義二元圖景不同,中國(guó)的土地制度和農(nóng)村政策讓農(nóng)民能夠在生存工資的200%之上,而不是劉易斯的30%水平上向工業(yè)轉(zhuǎn)移勞動(dòng)力。中國(guó)土地制度及其相聯(lián)系的戶籍制度雖然受到詬病,但它能夠使農(nóng)民的打工收入返回到農(nóng)村,這不僅提高了農(nóng)民整體的消費(fèi)水平(如果在城市安家,那么在農(nóng)村生活的人將較少受益于工資),而且通過(guò)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升級(jí)的吸引,使部分打工收入投向農(nóng)業(yè),提高了農(nóng)業(yè)的生產(chǎn)力水平。當(dāng)城市工業(yè)出現(xiàn)突然萎縮時(shí),承包的土地充當(dāng)了失業(yè)保險(xiǎn),緩解了失業(yè)的壓力。它也阻止了城市貧民窟的產(chǎn)生。可以說(shuō),正是中國(guó)的土地制度和沒有被二元經(jīng)濟(jì)理論所關(guān)注的Λ集合,使中國(guó)經(jīng)濟(jì)能在數(shù)億剩余農(nóng)村勞動(dòng)力條件下沒有出現(xiàn)大規(guī)模的托達(dá)羅式失業(yè),也沒有出現(xiàn)工資被壓低到生存水平的劉易斯“痛苦”轉(zhuǎn)移,正是這兩個(gè)因素使中國(guó)農(nóng)民的生活水平逐步平穩(wěn)地提高,中國(guó)的農(nóng)業(yè)勞動(dòng)力平穩(wěn)地轉(zhuǎn)移到二三產(chǎn)業(yè),從而保證了經(jīng)濟(jì)的高速穩(wěn)定增長(zhǎng)和平穩(wěn)的政治環(huán)境。
參考文獻(xiàn):
[1] 游松關(guān)于中國(guó)劉易斯轉(zhuǎn)折點(diǎn)的進(jìn)一步研究——理論辨析與實(shí)證檢驗(yàn)[D]上海: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碩士學(xué)位論文,2012
[2] Lewis, WA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The Manchester School,1954, 22(2):139-191
[3] Fields, G SArthur Lewiss Contribution to Development Thinking and Policy[J] The Manchester School,2004,72(6):712-723
[4] Rosenzweig, MLabor Markets in Low Income Countries[A] Chenery,H , Srinivasan, TN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ume 1)[C]Amsterdam: North Holland, 1988
[5] Fields, GS Dualism in the Labor Market: A Perspective on the Lewis Model after Half a Century[J] The Manchester School,2004,72(6):724-735
[6] Leeson, PF The Lewis Model and Development Theory[J]The Manchester School ,1979,47(3): 196-210
[7] 盧鋒中國(guó)農(nóng)民工工資趨勢(shì)——1979—2010[J]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2012,(7):47-67
[8] 童玉芬中國(guó)農(nóng)村勞動(dòng)力非農(nóng)化轉(zhuǎn)移規(guī)模估算及其變動(dòng)過(guò)程分析[J]人口研究,2010,(5):68-75
[9] 費(fèi)景漢,古斯塔夫·拉尼斯增長(zhǎng)和發(fā)展:演進(jìn)的觀點(diǎn)[M]洪銀興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4
[10] 劉泰山告別“跛腳”發(fā)展 走向共同富裕 廣東大扶貧帶來(lái)大變化[N]人民日?qǐng)?bào),2011-11-26
[11] 中央電視臺(tái)CCTV4遠(yuǎn)方的家(第58集)[R]北京:2012
[12] 胡鞍鋼,胡琳琳,常志霄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與減少貧困[J]清華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6,(5):105-115
[13] 費(fèi)景漢,古斯塔夫·拉尼斯勞動(dòng)剩余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理論與政策[M]北京:經(jīng)濟(jì)科學(xué)出版社,199215
[14] 胡景北對(d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過(guò)程中工資上升運(yùn)動(dòng)的解釋[J]經(jīng)濟(jì)研究,1994,(3):32-43
[15] 胡景北中國(guó)經(jīng)濟(jì)長(zhǎng)期發(fā)展的一種可能機(jī)制[J]經(jīng)濟(jì)研究,1998,(3):23-57
[16] 威廉·阿瑟·劉易斯對(duì)無(wú)限的勞動(dòng)力的反思[A]二元經(jīng)濟(jì)論[C]施煒譯,北京:北京經(jīng)濟(jì)學(xué)院出版社,1989113
[17] Jorgenson,DW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u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New Series,1967,19(3):288-312
(責(zé)任編輯:劉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