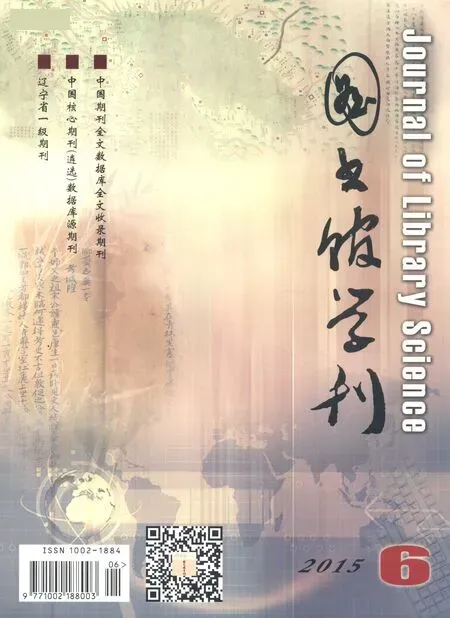我國(guó)學(xué)科館員專(zhuān)題研究高被引論文特征分析
龐德盛 王 芳 張紅梅
(沈陽(yáng)藥科大學(xué)圖書(shū)館,遼寧 沈陽(yáng) 110016)
1 數(shù)據(jù)來(lái)源和特征分析
2014年9月16日,筆者以中國(guó)期刊全文數(shù)據(jù)庫(kù)(CNKI)作為數(shù)據(jù)源,以精確方式檢獲“篇名”中含有“學(xué)科館員”的學(xué)術(shù)論文1969篇。由于研究學(xué)科館員的論文未必在篇名中含有“學(xué)科館員”字樣,而篇名中有“學(xué)科館員”字樣的論文其研究?jī)?nèi)容往往都與學(xué)科館員有著必然的聯(lián)系,因此筆者將檢索結(jié)果作為研究學(xué)科館員的部分論文的樣本[1]。通過(guò)對(duì)這1969篇相關(guān)論文進(jìn)行研究分析,試圖梳理其年代分布、作者分布及高影響力論文的分布情況,從而對(duì)該領(lǐng)域研究的未來(lái)趨勢(shì)進(jìn)行預(yù)測(cè)和展望。
1.1 年代分布
經(jīng)統(tǒng)計(jì)分析,可以清晰得出1969篇論文的年代分布規(guī)律,如圖1所示。關(guān)于“學(xué)科館員”研究的論文從1987年開(kāi)始出現(xiàn),此后逐漸增多,呈持續(xù)增長(zhǎng)態(tài)勢(shì),到2005年突破100篇,2009年更是達(dá)到234篇。而2012年之后,該領(lǐng)域研究論文的數(shù)量急轉(zhuǎn)直下,出現(xiàn)拐點(diǎn),相關(guān)研究成果迅速減少。

圖1 1969篇論文的年代分布
1.2 核心作者分布
透過(guò)該領(lǐng)域研究作者取得成果的數(shù)量及其分布規(guī)律,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該領(lǐng)域研究的核心作者。通過(guò)對(duì)1969篇相關(guān)研究論文的統(tǒng)計(jì)分析發(fā)現(xiàn),所有統(tǒng)計(jì)研究樣本中發(fā)表5篇或5篇以上論文的作者共有9位,見(jiàn)表1。廉立軍、楊玉全等9位作者我們可以確定為“學(xué)科館員”領(lǐng)域研究的核心作者。

表1 發(fā)表5篇及以上學(xué)科館員研究論文的作者

表2 學(xué)科館員研究被引次數(shù)排名前30的論文
1.3 高被引論文
引文規(guī)律是反映與評(píng)價(jià)學(xué)術(shù)研究成果質(zhì)量的重要指標(biāo),而期刊論文的被引頻次更是成為評(píng)價(jià)學(xué)術(shù)成果質(zhì)量的重要制度。被引頻次是指某一論文在正式發(fā)表后于某一時(shí)間段內(nèi)被其他研究成果相繼引用的累積次數(shù),它是衡量學(xué)術(shù)論文質(zhì)量和學(xué)術(shù)期刊辦刊水平的重要指標(biāo)[3]。我們?cè)诖斯们乙脺吠腹镜南嚓P(guān)標(biāo)準(zhǔn),即高被引論文是指10年內(nèi)被引用次數(shù)排在前1%的論文。筆者統(tǒng)計(jì)研究成果樣本產(chǎn)生的時(shí)間跨度約為27年,篩選1969篇研究樣本中被引次數(shù)排在前30位的論文,約占比達(dá)1.5%,將其確定為該主題研究的高被引論文,基本符合相關(guān)文獻(xiàn)學(xué)研究規(guī)律和客觀(guān)實(shí)際。具體情況如表2所示。
2 學(xué)科館員研究高被引論文特征分析
2.1 高被引論文作者的特征
在前30位高被引的論文中,排在首位的是初景利先生于2008年發(fā)表在《圖書(shū)情報(bào)工作》上的《第二代學(xué)科館員與學(xué)科化服務(wù)》,其被引次數(shù)為321次;排在第30位的柯平先生于2011年發(fā)表在《高校圖書(shū)館工作》上的《新世紀(jì)十年我國(guó)學(xué)科館員與學(xué)科化服務(wù)的發(fā)展(上)》,其被引55次。筆者選擇第一作者為統(tǒng)計(jì)對(duì)象,發(fā)文數(shù)量進(jìn)入前30位的高被引論文作者大多數(shù)只發(fā)表1篇論文,只有中國(guó)科學(xué)院國(guó)家科學(xué)圖書(shū)館的初景利、中國(guó)科學(xué)院文獻(xiàn)情報(bào)中心的李春旺、清華大學(xué)圖書(shū)館的范愛(ài)紅以及南開(kāi)大學(xué)圖書(shū)館的柯平老師各以?xún)善撐倪M(jìn)入列表。這4位作者的論文數(shù)量占了30篇高被引論文的27%,可以認(rèn)為是學(xué)科館員研究領(lǐng)域最具影響力的核心作者。
2.2 研究機(jī)構(gòu)的分布
通過(guò)對(duì)30位高被引作者的統(tǒng)計(jì),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些高被引論文作者所在機(jī)構(gòu)的分布情況。排名前30位的高被引論文生產(chǎn)機(jī)構(gòu)中,中國(guó)科學(xué)院國(guó)家科學(xué)圖書(shū)館、中國(guó)科學(xué)院文獻(xiàn)情報(bào)中心、清華大學(xué)圖書(shū)館以及南開(kāi)大學(xué)圖書(shū)館生產(chǎn)的高被引論文所占比例與其排名高度一致,清華大學(xué)圖書(shū)館所生產(chǎn)的高被引論文數(shù)量居首位,遙遙領(lǐng)先于其他機(jī)構(gòu)。這與清華大學(xué)圖書(shū)館在我國(guó)首先試行學(xué)科館員制度不無(wú)關(guān)系[2]。中國(guó)科學(xué)院系統(tǒng)和南開(kāi)大學(xué)也是開(kāi)展學(xué)科館員制度較早的機(jī)構(gòu)。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高被引論文的機(jī)構(gòu)分布特征映襯了我國(guó)學(xué)科館員制度建立和發(fā)展的現(xiàn)狀和規(guī)律性,是學(xué)科館員制度建設(shè)的實(shí)踐不斷推動(dòng)著該領(lǐng)域理論研究的深化發(fā)展。這也基本印證了筆者研究該選題所選取數(shù)據(jù)的合理性。

圖2 學(xué)科館員研究30篇高被引論文的單位分布
2.3 論文發(fā)表期刊的分布
排名前30位的高被引論文所刊載的期刊分布廣泛,分別發(fā)表在14種期刊上。這14種期刊,除了《東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其余均為圖書(shū)情報(bào)學(xué)專(zhuān)業(yè)期刊,而且多為專(zhuān)業(yè)核心期刊,其中以《大學(xué)圖書(shū)館學(xué)報(bào)》載文最多,累計(jì)發(fā)表7篇,其次為《圖書(shū)情報(bào)工作》,供發(fā)表6篇,其余期刊所發(fā)表高被引論文的情況如圖3所示。

圖3 學(xué)科館員研究30篇高被引論文的刊物分布
2.4 論文的年代分布
文獻(xiàn)的被引用情況與該文獻(xiàn)發(fā)表時(shí)間的長(zhǎng)短關(guān)系密切,發(fā)表時(shí)間較短的論文被引用的可能性較小,成為高被引論文的可能性更小。因?yàn)閭鞑チ啃』蛘叱晒晃赵俎D(zhuǎn)化為論文是需要一定時(shí)間的。相反發(fā)表時(shí)間較長(zhǎng)的論文,也必然體現(xiàn)出一定的文獻(xiàn)老化規(guī)律,陳舊過(guò)時(shí)的知識(shí)被其他作者所引用的概率也會(huì)大大降低。30篇高被引論文中多發(fā)表于2002~2008年之間,這一時(shí)期是正是我國(guó)學(xué)科館員領(lǐng)域研究的活躍期,很好地反映了該領(lǐng)域研究理論與實(shí)踐有機(jī)結(jié)合的發(fā)展規(guī)律。具體分布如圖4所示。

圖4 學(xué)科館員研究30篇高被引論文的年代分布
2.5 關(guān)鍵詞分析
文獻(xiàn)所用關(guān)鍵詞能夠直觀(guān)而鮮明地描述文獻(xiàn)所要表達(dá)的主題,便于讀者在閱讀正文之前迅速有效地了解和把握文獻(xiàn)所要論述的主題內(nèi)容[4]。如圖5所示,在30篇文獻(xiàn)中,學(xué)科館員(26次)排在第一位,依次為高校圖書(shū)館(14次)、學(xué)科化服務(wù)(8次)、圖書(shū)館(7次)、文獻(xiàn)信息服務(wù)(6)、讀者服務(wù)(6次)、服務(wù)模式(3次)、隊(duì)伍建設(shè)(3次)。由此可見(jiàn)學(xué)科館員研究主要集中于高校圖書(shū)館,與圖書(shū)館服務(wù)主題密切相關(guān)。

圖5 學(xué)科館員研究30篇高被引論文的單位關(guān)鍵詞分布
3 研究結(jié)論
關(guān)于“學(xué)科館員”的研究,自1987年陳京發(fā)表的第一篇論文《建立一支“學(xué)科館員”的專(zhuān)業(yè)隊(duì)伍》以來(lái),相關(guān)主題的研究成果數(shù)量不斷增加,呈現(xiàn)了日漸上升的態(tài)勢(shì)。這從一定程度上說(shuō)明,學(xué)科館員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問(wèn)題正在引起我國(guó)高校圖書(shū)館界以及相關(guān)文獻(xiàn)服務(wù)機(jī)構(gòu)的重視,各高校及信息服務(wù)機(jī)構(gòu)都在致力于學(xué)科館員及其學(xué)科化研究。但通過(guò)上述研究分析我們也不難發(fā)現(xiàn),發(fā)表超過(guò)5篇該選題研究論文的作者只有9位,他們是學(xué)科館員研究的相對(duì)高產(chǎn)作者,且最高發(fā)文量只有7篇,表明關(guān)于學(xué)科館員研究還比較分散,還沒(méi)有完全形成高產(chǎn)核心作者群。
僅以第一作者作為統(tǒng)計(jì)依據(jù),30篇高被引論文的作者中,只有初景利、李春旺、范愛(ài)紅、柯平各發(fā)表了兩篇論文,其他多數(shù)作者僅發(fā)表了1篇。可見(jiàn),初景利、李春旺、范愛(ài)紅、柯平這4位作者是學(xué)科館員研究領(lǐng)域最具影響力的學(xué)者。從發(fā)文量排名前三位的機(jī)構(gòu)來(lái)看,我國(guó)圖書(shū)情報(bào)界在讀者服務(wù)過(guò)程中首先建立學(xué)科館員制度的是清華大學(xué)圖書(shū)館,除此之外,中國(guó)科學(xué)院系統(tǒng)和南開(kāi)大學(xué)是我國(guó)國(guó)內(nèi)實(shí)施學(xué)科館員制度較早的機(jī)構(gòu)。因此,透過(guò)高被引論文的機(jī)構(gòu)分布特征我們可以看出,清華大學(xué)圖書(shū)館、中科院以及南開(kāi)大學(xué)是我國(guó)開(kāi)展學(xué)科館員理論研究和實(shí)踐探索的核心機(jī)構(gòu),是國(guó)內(nèi)學(xué)科館員制度建設(shè)的拓荒者。
30篇高被引的論文分別發(fā)表在14種專(zhuān)業(yè)期刊上,除《東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之外,圖書(shū)館學(xué)或情報(bào)學(xué)期刊占了13種,而且多為核心期刊。其中發(fā)表高影響力論文最多的期刊是《大學(xué)圖書(shū)館學(xué)報(bào)》,共發(fā)表了7篇。學(xué)科館員研究高被引論文主要集中于高校圖書(shū)館,與圖書(shū)館服務(wù)密切相關(guān)。足見(jiàn),我國(guó)圖書(shū)情報(bào)界是開(kāi)展學(xué)科館員制度研究和學(xué)科館員實(shí)踐探索的主要領(lǐng)域。
引文分析是學(xué)術(shù)評(píng)價(jià)的重要方法。通過(guò)對(duì)高被引論文和熱點(diǎn)論文的統(tǒng)計(jì)分析,便于我們從文獻(xiàn)計(jì)量學(xué)的角度梳理和廓清相關(guān)學(xué)科領(lǐng)域研究脈絡(luò)、研究熱點(diǎn)以及研究趨勢(shì)[5]。筆者選取了學(xué)科館員這一專(zhuān)題研究歷年被引頻次排在前30篇的論文作為高被引論文,并對(duì)其進(jìn)行了分析統(tǒng)計(jì),有利于全面了解高被引論文所具有的特征,為讀者進(jìn)一步了解和研究學(xué)科館員這一專(zhuān)題領(lǐng)域的問(wèn)題提供有力參考。
[1] 常青.情報(bào)學(xué)研究高被引論文的特征分析[J].情報(bào)資料工作,2014(4):100-102.
[2] 姜愛(ài)蓉.清華大學(xué)圖書(shū)館“學(xué)科館員”制度的建立[J].圖書(shū)館雜志,1999(6):30-31.
[3] 李潔,等.我國(guó)20種綜合性農(nóng)業(yè)科學(xué)核心期刊的高被引論文研究[J].中國(guó)科技期刊研究,2014(1):74-78.
[4] 王芳,李薇,楊錯(cuò).我國(guó)學(xué)科館員與學(xué)科服務(wù)發(fā)展研究論文計(jì)量分析[J].圖書(shū)館學(xué)刊,2013(1):127-130.
[5] 劉雪立.基于WebofScience和ESI數(shù)據(jù)庫(kù)高被引論文的界定方法[J].中國(guó)科技期刊研究,2012(6):975-977.
- 圖書(shū)館學(xué)刊的其它文章
- 虛擬現(xiàn)實(shí)技術(shù)在圖書(shū)館服務(wù)創(chuàng)新中的應(yīng)用*
- 高校圖書(shū)館文獻(xiàn)信息資源共享服務(wù)實(shí)證研究
——以福州地區(qū)大學(xué)城圖書(shū)館為例 - 構(gòu)建全民閱讀體系的對(duì)策?
- 基于關(guān)聯(lián)數(shù)據(jù)的數(shù)字圖書(shū)館資源整合模式
- 少兒圖書(shū)館特色文獻(xiàn)資源庫(kù)的建設(shè)模式
- 高校圖書(shū)館樣本書(shū)庫(kù)現(xiàn)狀調(diào)查分析*
——以華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圖書(shū)館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