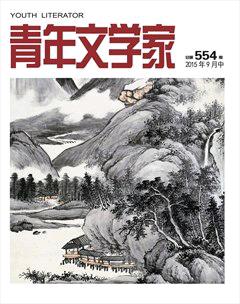淺析杜甫詩歌中菊花意象的情感意蘊
摘 要:菊花意象在古詩詞中有著多種意蘊,杜甫將自己的人生感悟融入到菊花意象中,使菊花意象成為其情感的載體,本文通過對杜甫詩歌中的菊花意象的梳理,從身世之感、思念之情、家國之悲三個角度分析杜詩中菊花意象的情感意蘊,了解杜甫詩歌中感時傷世的悲苦。
關鍵詞:杜甫;菊花意象;情感意蘊;感時傷世
作者簡介:張拓,女(1991-),漢族,黑龍江雙鴨山市人,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在讀碩士,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26-62-02
在我國,菊花已經有了三千多年的種植史,民間的菊花盛會從宋代開始就不曾中斷,菊花不僅有觀賞和藥用價值,還被賦予了長壽、吉祥的含義。菊花,不像花之富貴者牡丹那樣雍容,也不像花之君子蘭花那樣優雅,但它卻能夠抵擋嚴寒,高潔清凈,在詩人的心湖投下一顆石子,蕩起層層漣漪。本文將從杜甫詩歌中菊花意象的內涵入手,探討其深層情感意蘊。
一、菊花意象的幾種普遍內涵
(一)志士的高潔堅貞。屈原是寫菊的第一人,在“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到這位滿懷赤子之心的楚地詩人在汨羅江畔高喊“舉世皆濁我獨清,世人皆醉我獨醒”。即使被放逐,也不會與世俗同流合污,即使去赴死,也絕不向惡勢力低頭,自此,菊花成為高潔人格的象征。
(二)隱士的閑淡悠然。東晉的陶淵明的《和郭主簿》:“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杰。”在他的筆下,菊花成為了花之隱逸者,不與群芳爭艷,不與萬物爭奇,只是靜靜地綻放在霜下,菊花這隱者的風范正是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的悠然心態的體現。
(三)游子的感時傷懷。每逢佳節倍思親,重陽節登高賞菊已經是眾所周知的習俗,古代詩人生涯坎坷,往往與親人分居兩地不能經常相見,在節日時分則更添一份憂愁。就像岑參的詩句:“強欲登高去,無人送酒來。遙憐故園菊,應傍戰場開。”
(四)斗士的堅強不屈。著名農民起義領袖黃巢也深愛菊花,在他的眼中,菊花和自己一樣是戰斗的勇士。著名的《菊花》中寫道:“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 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戴黃金甲”菊花在百花凋敝后猶能綻放,它的芬芳籠罩著整個長安城,就像心中有一顆斗士的靈魂。
(五)思婦的淡淡閑愁。易安居士的一句“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令丈夫趙明誠也甘拜下風,這時的她雖還未經太多風雨摧殘,但閨中女兒的淡淡憂愁仍然透過菊花意象被表達得淋漓盡致,因為獨守幽閨,形容枯槁,竟然比“黃花”還要瘦削。
二、杜甫詩歌中菊花意象的情感意蘊
據統計,菊花在杜詩中出現三十次,杜甫筆下的菊花多種多樣:長安的甘菊,秦州的金菊,梓州的細菊,夔州的菊蕊。杜甫所生活的時代正是安史之亂帶來社會動亂的時代,極盛的唐代自此走向衰落,雖然還有中唐時期的回光返照,但一個王朝的覆滅感卻早就被敏銳的詩人捕捉到了。這個時期詩作中的菊花意象,也染上了感傷的時代色彩。杜甫不僅有著思親憶友的一腔柔情,更是心懷家國天下的大丈夫,所以杜詩中菊花意象的情感意蘊又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身世之感
杜甫這一生是極為坎坷的,仕途不順,飽受憂患,數十年客居他鄉,經常寄人籬下,心里郁積的孤獨憂愁之感常常流露于詩中:“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詩人對自己身世的漂泊感慨萬千,詩歌中的菊花也點染了這樣的情懷。
詩人在《遣懷》中寫道:“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風隨斷柳,客淚墮清笳。”一雙愁眼看盡寒霜白露,滿城蕭瑟中菊花獨自綻放,敗柳被秋風吹起又飄落,詩人身在他鄉,客心驟起,也不禁被清遠的胡笳聲催下淚來。最后的景象更是凄涼,即使有這樣的菊花做伴,也難免心中孤寂。所有的落寞、失意都寄托在了菊花身上,所有的傷感與思念也只有菊花在傾聽,詩人像菊花一樣在寒風中堅守,菊花就成為了杜甫身世的象征。
文藝理論家里普斯曾經說:“審美的欣賞并非對于一個對象的欣賞,而是一個對于自我的欣賞,它是一種位于人自己身上的直接的價值感受。”[1]《嘆庭前甘菊花》詩云:“檐前甘菊移時晚,青蕊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醉盡醒,殘花爛熳開何益。籬邊野外多眾芳,采擷細瑣升中堂。念茲空長大枝葉,皆根失所埋風霜。”因為移植的時間有些遲了,所以重陽時節了,菊花還結著青色的花蕾沒有開放。而過了佳節,醒了醉酒后再也沒有應景的興致了,此時盛放的菊花已經沒有人欣賞了。代替它的是當時野地里籬笆旁的其他鮮花,它們被采擷被裝點在明堂之上,苦苦生長的菊花卻失去了寓所而被埋沒在風霜之中。詩人就像這菊花一樣生不逢時,雖然奮力生長,卻沒能為已經傾頹的國勢盡上自己的一份力量。滿腹詩書雖百無一用,但卻依舊和殘酷的環境抗爭,保持自己的堅守與氣節,不失本心。詩人對國家與時代仍舊存了一分希望,相信有東山再起的一天。
(二)思念之情
杜甫是一位充滿柔情的詩人,極重感情,他一生中大半時間都羈旅異鄉,所以許多作品表達了對故園、親友的思念。菊花盛開在秋季,多值重陽佳節,因此這種思念之情也往往通過菊花意象表現出來。
著名的《秋興》(其一)這樣寫道:“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涌,塞上風云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稱這組《秋興八首》是律詩組詩的巔峰之作也不為過,它們以一以貫之的情懷征服了所有的讀者。詩人此時正經受著離亂之苦,老來多病,菊花的開放引發了他對自己故鄉的思念。又是秋天,又是孑然一身,楓林寒露和江水波濤構成了蕭瑟的景象,在這樣的環境下,叢菊兩開,詩人又一次老淚縱橫了,因為一葉扁舟已經系不住似箭的歸心了,本來可以做伴的菊花也不能解開這樣濃郁的憂愁了。“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在本該萬家團聚,共享天倫之樂的日子里,詩人卻只能獨自一人攜著酒杯登上高臺,遠望著故鄉的方向,品味著杯中的苦酒,賞菊之心本該歡樂,此時卻更顯得悲戚,和家人分離時間的長久,與故鄉空間距離的遙遠都平添了一分寂寥。
這種濃郁的悲苦鄉思在《夜》中更為強烈:“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疏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雁無情。步蟾倚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 這首詩先寫景,再由景入情,從自己臥病榻上、生活困頓寫到對家人的思念,家書不至也歸罪給無情的鴻雁。歸家之日遙遙無期,流落在他鄉的無限悲涼被一句“南菊再逢”描繪得十分到位,因為他鄉的菊花已經又一次開放了,老病的自己卻仍未回歸,這種身體與精神的雙重痛苦更加打動人心。
(三)家國之悲
初唐詩壇就頗負詩名的杜審言是杜甫的祖父,杜家的家庭傳統也是“奉儒守官”,杜甫的思想自然深深打上忠君仁民的烙印。杜甫雖然想要“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但卻仕途坎坷,兩次進士落第后客居長安長達十余年,生活得十分艱難。而后又在異鄉漂泊數十年未曾歸家,親眼看到了人民所遭受的苦難,貧窮、戰爭和疾病使得民不聊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杜甫的一顆憂國憂民之心自此埋下了根,此生從未再改變。因此,菊花這個意象也不能不帶有這樣一份情思。
成都劍南兵馬的變故讓杜甫再度出逃避難,本可以瀟灑地置之不顧的地方官,如今也不得不去與之周旋,庸俗的官場所生的漂泊之感令詩人更加憤怒,思及圣人孔子為推行仁政而四處奔波,累累遭棄,不由覺得自己也是“今如喪家狗”。《秋盡》中寫道:“秋盡東行且未回,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卻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得好開。”隱士陶淵明的東籬菊也老了,詩人也在苦苦掙扎,一片愛國的熱誠無處揮灑,身在他鄉,心懷天下。老驥伏櫪,壯心不已,然而卻無力回天,菊花的零落正如雪嶺上孤獨地看著落日的詩人一樣,雖是不辭萬里常年作客,卻不知何時才有再開懷抱之日了。
杜甫后來曾回到四川定居,不久又被迫離開,途徑嘉州、戎州、渝州、忠州,后居云安,此時詩人心中的熱情已漸漸消退,他深感整個社會不是一人之力就能挽回的衰落了。在《云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中他寫道:“寒花開已盡,菊蕊獨盈枝。舊摘人頻異,輕香酒暫隨。地偏初衣夾,山擁更登危。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在瑟瑟的寒風中,別的花兒早就因為經不住寒冷而零落了,只有菊花還在枝頭盛放,然而本應金樽清酒,悠哉賞花的時節,詩人終究是放不下這天下呵,沒辦法徹底盡興,最終還是在萬國戎馬聲中借著微醺的酒意而垂垂落淚。
杜甫詩歌中菊花意象的情感意蘊雖大體分為以上三種,但這三種情感意蘊有時會融合在同一首詩中,經常是由身世之感和思念之情升華到家國之悲,正所謂“杜陵有句皆憂國”,這種深沉的情感正如菊花綻放,花蕊層層展開,我們便看到那顆沉甸甸的憂國之心。而杜詩沉郁的風格特點也自然展現,沉郁是感情的厚實,它主要來自杜甫悲劇的一生,仕途坎坷,家道衰落,離鄉漂泊,年老多病,飽受戰亂離別之苦,杜詩中自然有著感時傷世的悲苦。
三、小結
梁啟超在《情圣杜甫》中稱杜甫為“情圣”: “因為他的情感的內容,是極豐富的,極真實的,極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極熟練,能鞭辟到最深處,能將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樣子,能象電氣一般,一振一蕩的打到別人的心弦上,中國文學界寫情圣手,沒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2]
杜甫詩歌中的菊花意象幾乎都帶著感時傷世的情感意蘊。感懷自己的人生境遇,他以甘菊自況,感慨自己生不逢時;悲憫生民疾苦,他有“欲淚垂”無力;思念故園,他有“叢菊兩開他日淚”的無奈。然而,杜甫所有的情懷終究要歸結到國家上,他為自己悲,是因為自己看到祖國山河危在旦夕卻無能為力;他為民悲,是將百姓蒼生納入自己眼下,為黎民的生命嘆息苦悶;他為故園悲,是從自己多年流離失所想到天下寒士,亦不能有所歸依的寬廣胸懷。這些特點使杜詩中菊花意象的情感意蘊得到升華,擁有了情感的厚重感,上升到了整個民族的高度,成為他表達自己深厚情感的一個途徑,并由此形成了獨特的代表性意象。
注釋:
[1]伍蠡甫:現代西方文論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第4頁。
[2]梁啟超:情圣杜甫[J],晨報副刊,1922,(5):28-29。
參考文獻:
[1]仇兆鰲:杜詩詳注,中華書局 2004年。
[2]杜甫:杜工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
[3]劉明華:杜甫研究論集,重慶出版社, 2004年12月第2版。
[4]王士菁:杜詩便覽,四川文藝出版社, 1986年4月第1版。
[5]馮至:杜甫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0年3月第2版。
[6]嚴云受:詩詞意象的魅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