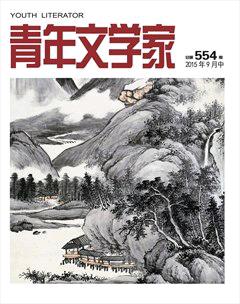《追憶似水年華》中的猶太人形象
摘 要:本篇論文從“猶太人”這個角度入手,利用文史互證的方法,通過虛構的文本試圖分析真實的歷史。利用《追憶似水年華》中的兩個代表性人物——布洛克和斯萬,并結合當時特殊的德雷福斯事件分析猶太人在當時法國社會的現實處境和心路歷程。從家庭教育、成長背景、人物性格等分析猶太人在法國社會遭遇的不同命運,以及他們背負的種族壓力。
關鍵詞:追憶似水年華;猶太人;斯萬;布洛克
作者簡介:丁濛(1987-),女,江蘇如皋人,漢族,學生,學歷:博士,研究方向: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26-81-02
一、以不同方式進入上流社會的兩個猶太人
說起猶太人,種族排斥是一個恒久不變的話題,他們每到一座城市,常常會受到當地人的漠視和敵對,他們渴望融入其中,共同生活,但是人們給予他們的總是異樣的目光。一些猶太人甚至希望通過進入上流社會來改善自己的處境,希望與貴族人士的友好相處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但是,猶太身份的尷尬令他們舉步維艱,尤其是家庭環境背景、個人處事方式會產生不同的影響,他們通過各自的努力以進入上流社會的交際圈。
說起《追憶似水年華》中典型的猶太人形象,人們大多會提到斯萬,斯萬也是《追憶》中被研究得最多的人物之一,他學識淵博、談吐得體、閱歷豐富,作為一名猶太人,他不僅成功融入了當時的法國社會,而且在上流交際圈里也極受歡迎,而與之相反的另一個猶太人物就是不太受關注的布洛克,出身于普通猶太家庭的布洛克非常渴望進入上流社會,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但是他舉止粗俗,方式淺薄,反而是經常受到周圍人的嘲弄。
家庭環境的影響和成長經驗的積累使斯萬自有一套為人處世的巧妙方法,“像斯萬這樣的人,只要從報上看到某次宴會有些人參加,用不著求助于他對社交界的那套知識,立刻就能說出這個宴會是怎樣一種派頭的宴會”[1],這一切都使得斯萬如魚得水,無論是在上流社會還是普通民眾眼里,斯萬都是一個受人歡迎、值得交往的客人,如果不是德雷福斯事件的影響,人們甚至已經忽略了他的猶太身份。而小說里的另一個猶太人物布洛克就顯得較為粗鄙、淺薄,他那不加掩飾的阿諛討好、夸張做作的處事風格、自以為是的態度舉止,時常受到他人的嘲笑諷刺,“無尾禮服光鮮奪目,皮鞋溜光锃亮,但是舉止裝腔作勢,使人想到畫家那些所謂‘聰明的講究”[2]。與處事圓滑、行事大方的斯萬相比,布洛克的交際手段就顯得粗鄙生硬一些,有還會令人嗤之以鼻,他“從小沒有受過好教育,養成了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惡習”[3],甚至在一些重要的場所,他也不加掩飾他種種不禮貌的惡習,“人們將他介紹給別人時,他彎腰鞠躬,既帶幾分懷疑地微微一笑,又帶著過分夸大的恭敬”[4]。另一方面,受家庭環境的影響,斯萬受到過良好的教育,尤其在藝術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詣,他獨特的見解引起大家的關注,人們愿意與他交流和溝通,這無疑是打開通往上流社會大門的有效方式,而相比之下,布洛克的付出則要艱辛許多,由于家境困難,不能提供良好的教育條件,布洛克在文化上有所欠缺,雖然在文學方面他也時而會有自己獨到犀利的個人見解,但是他言語無趣,乏味可陳,缺少與人交流的能力。
二、德雷福斯事件對兩個人的特殊影響
由于兩個人的家庭背景、社交圈有所不同,原先的斯萬并不十分欣賞布洛克,相互之間也沒有過多的交集,但是猶太人的命運將他們聯系在了一起。兩個人在最后的時刻能不約而同選擇站在德雷福斯派的立場,無疑是源于他們自身的猶太血統。德雷福斯事件的爆發雖然導致各種形式的反猶活動,這給猶太人再次帶來了巨大的不幸,令斯萬苦心經營的局面遭到破壞,但同時也激發了猶太人的民族意識,讓客居他鄉、互不想干的兩個人因為民族情結再次聚到了一起。
斯萬雖持有德雷福斯派的觀點,支持德雷福斯重審案,但是他卻拒絕在布洛克為比卡爾請愿的名單上簽名。盡管在事件爆發時他的情感也有所偏激,但他很快清醒地認識到自己處境的尷尬,后來當布洛克問及他對此事件的看法時,他不再明確表露出對德雷福斯重審案的立場,這也一度引起了布洛克的不滿。實際上,斯萬內心的猶太民族情結也很強烈,但同時他又保留著資產階級特有的圓滑和謹慎。而布洛克的做法則顯得相對偏激,他四處找人簽名請愿,打探別人對此事的看法,在整件事上顯得過于焦躁缺乏考慮。這種行為做事的作風差異也與家庭有著很大的關系,斯萬父親是富有的猶太證券商,他們整個家族為融入法國上流社會付出的代價是艱辛的,而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同樣也是殘酷的,因此他們的處事作風更加謹慎細微。
漢娜·阿倫特在其作品中也分析了德雷福斯事件中猶太人的普遍反應,“當德雷福斯事件發生警告他們,他們的安全受到威脅時……一切政治熱情都消融在沉重的社會勢利、大生意以及未知的利潤機會之下”[5],對于猶太資本家來說,他們在接受自己猶太屬性的同時,更多的還是考慮現實權益,尤其是面臨政治危機和利益驅使的時候。
“他(斯萬)的猶太特征隨著年齡的增長與疾病的到來而愈發明顯。他懷著確定但又謹慎的態度重新尋找他的親朋好友們,這一做法在德雷福斯時期遭到了布洛克的指責”[6],德雷福斯事件爆發初期,斯萬和布洛克出于自身考慮和個人因素也許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但是隨著事態的發展,他們都為自己的民族做出了切實和努力。盡管僅憑個體的努力他們無法掌控全局,改變事態的發展,他們甚至都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但是他們仍然團結起來,希望自己民族的命運哪怕能做出稍許的改變。
三、種族的延續性
這些散居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雖然飽受非議,屢遭排擠和打擊,但是他們依然頑強奮斗,在縫隙中掙扎,他們在維持著猶太性的同時,世代拼搏,無畏生存條件的艱辛,努力融入上流社會,把希望延續給每個后代。一部分猶太人甚至比當地的人還能適應城市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他們向世人展現著頑強的生命力,憑借著獨有的智慧和恰當的風度巧妙地緩和了現實的矛盾,“這個種族具有令人驚奇的生命力,世世代代,繁衍生息,把一個完整的手指一直伸到現代的巴黎”[7]。
較之斯萬,普魯斯特筆下的布洛克有著明顯的猶太人特征,“盡管他穿著歐洲人的服裝,卻同德康筆下的猶太人一樣奇特,一樣耐看”。許多猶太人在融入上流社會的同時,行為處事竭力效仿上層貴族,思維談吐也漸漸喪失了猶太人的特點。盡管有一些人在人群中表現得生硬可笑,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這樣一群冷酷做作、附庸風雅的上流貴族中倒也顯現出直率的一面,“人們很快就會承認,即使他們過長的頭發、過大的鼻子和眼睛、做作的不連貫的手勢令人生厭,但單憑這些就對他們做出評價的做法是有幼稚的,他們心胸開闊,心地坦誠,與這些品質相比,圣盧的母親和蓋爾芒特公爵就相形失色,他們冷酷無情,具有虛假的宗教情感”[8]。布洛克一家雖然招人厭煩,但待人處事不掩內心,雖然愚笨,倒也不乏坦誠之情。
德雷福斯事件爆發初始,斯萬和布洛克并沒有因為個人情感而選擇支持德雷福斯,但是隨著事件的嚴峻發展,他們在民族利益與個人處境之間選擇了自己的立場,盡管這給他們帶去了沉重的打擊,“我們只抓住次要的觀念,而意識不到首要的原因(猶太人種,法蘭西家庭,等等)。首要的原因必然產生出次要的觀念來”[9]。雖然背井離鄉、居無定所,但是猶太人之間有著共同的血統、身份和民族情感,這是他們永遠無法忽視的問題和永遠無法規避的羈絆。
注釋:
[1]Marcel Proust, Du c?té de chez Swan, Ed. Gallimard, 2009, p.239.
[2]馬塞爾·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上),李恒基、桂裕芳等(譯),譯林出版社,2008, 第520頁
[3]馬塞爾·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中),潘麗珍、許鈞等(譯),譯林出版社,2008, 第845頁.
[4]同上, 第630頁.
[5]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譯),三聯書店,2008, 第175頁.
[6]Julia Kristeva, Le temps sensible, Ed. Gallimard, 1994, p.48.
[7]馬塞爾·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上),李恒基、桂裕芳等(譯),譯林出版社,2008, 第822頁.
[8]同上,第982頁
[9]馬塞爾·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上),李恒基、桂裕芳等(譯),譯林出版社,2008, 第6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