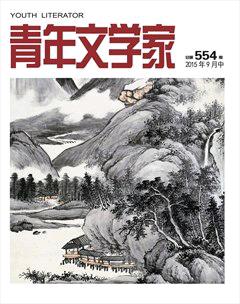淺析門羅小說中的“戍所心理”
孫艷琳
摘 要:作品集《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是門羅出版的第二部作品。小說集內容連貫,一度被認為是作者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門羅在小說中構建了一個完整的小鎮形象,由自然到人文,皆帶有弗萊筆下的“戍所心理”的典型特征。這正是門羅小說所獨具的風格。
關鍵詞:門羅;《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戍所心理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26-82-02
作為加拿大二十世紀屈指可數的文學思想家和理論家,諾斯洛普·弗萊對于本國人民的心理特征曾經有過非常生動而貼切的分析,并將之稱為“戍所心理”。在弗萊對于《加拿大文學史》中的《結論》一章中,他是這樣解釋“戍所心理”的——人數很少而又孤立的居民群被物質的或心理的‘邊界所框著,互相隔離而又被隔離與其美國的及英國的文化源頭:這些居民群向其成員提供了他們所有的一切明確的屬于人類的價值,并且被迫對把它們維系在一起的法律與秩序感到極大的尊重,然而它們卻面對著一個浩蕩無垠,渾渾噩噩,充滿威脅的可怖的物質環境——這樣的居民群必然會滋生出一種(我們可以姑且稱為的)戍所心理。而門羅的小說作為將加拿大文學推向世界文壇的重要工具,其筆下的文學世界也體現出典型的“戍所心理”特征。尤其是在作品集《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中,門羅借助于對其個人生活經歷的提煉和對故鄉的懷念,全方位的描繪出一個具有了完整自然生態和人際交往關系的加拿大典型小鎮——諸伯利。
門羅小說中的“戍所心理”在該作品集中的第一個典型體現在于小鎮居民與自然環境間和諧又充滿敬畏的矛盾關系。《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雖然是一部作品集,但各篇之間內容連貫,大部分是以女主人公黛爾的少女視角來展開敘述。不止一次,門羅都直觀寫出了小鎮人對于深處其中的自然生態的矛盾心態:在開篇的《弗萊茲路》中,大自然是充滿母性的。年幼的黛爾跟隨父母一起住在蜿蜒的瓦瓦納什河邊,跟著鄰居班尼叔叔一起捕魚和抓青蛙,“在泥濘的河岸,在柳樹下,在充滿圓錐花序植物和劍狀葉草的沼澤洞穴,我們光著的腿上留下了不易察覺的劃傷”,無憂無慮的童年浸潤在生機勃勃的自然里,與黛爾等孩子們做伴的則是各種各樣的生物,雪貂,水貂,火狐,浣熊,松鼠等,還有時而閃現的彩虹和流沙坑。人與自認的和諧相處在此間得到充分體現。到了《活體的繼承者》中,大自然突然顯示出其讓人敬畏的一面。埃爾斯佩斯姑媽和黛爾在樹林邊緣偶遇一只鹿,它“靜靜站在梳妝和濃密的蕨類植物中間,……隱入深深的灌木叢”。自然中深藏了諸多如此這般所不能了解的生物與生態,讓懂得它的人心生敬畏。與此相對應的,小鎮則是柔美的,夕陽下林立著的干草垛們投下靜謐的影子,“全都是秘密的一模一樣的紫灰色小屋”。而在《信仰之年》中,寫到諸伯利的冬天,雪差不多都化了,河水流淌,小鎮再次凸顯出它充滿野性的力量,“整個地方都是狐貍的腥臊味兒。……我忘掉然后又記起來”。整部作品集,門羅都在重復這種對于自然生態的印象,它時而溫暖的讓人想要沉醉其中,時而又閃現出其內部掩藏的冰冷又神秘的部分。這種矛盾心理正是“戍所心理”在居民內心的體現。弗萊曾經在《結論》一章中分析過這種心理,認為它既不是對于自然的親近也非是對于神秘的畏害,而是對于以這些東西為表征的某種事物的出自心靈深處的震恐。人類的理智為了保存它的正值完整,除了人道的和道德的價值外,還有矗立在理智面前的自然的巨大無際的無意識。這種無意識,即屬于“戍所心理”。
“戍所心理”在小說集中的第二個體現在于門羅對于筆下人物的人際關系的描寫當中。如同其所身處的自然環境一樣,小鎮居民也分為長居其中的與外來的居民兩種。以《弗萊茲路》中的班尼叔叔為例,他作為已經在諸伯利生活習慣的居民之一,當他駕駛著自己借來的車去城市中尋找莫名離去的妻子時,經受了一次重大的精神挫傷:他在城市當中迷路了,沒有人告訴他正確的地址在哪里,也沒有人愿意收留他,巨大的失落、沮喪與勞累中,班尼叔叔悻悻而歸。這段體驗非常好地體現出小鎮居民長久以來形成的心理和生活慣性。班尼叔叔像每一個普普通通的小鎮居民一樣,生活在他本就習以為常的土地上,他們的周圍都是最天然的自然環境以及相對來說比較簡單的人際關系,現實對于他們而言就是簡單的尋找與獲得。但這種慣性在進入城市的一瞬間都被摧毀了。多倫多有著與諸伯利完全不同的生存法則,讓人感覺不到任何的歸屬與放松。以班尼叔叔為代表的小鎮居民在城市當中所遭遇的迷失與惶恐,正是小鎮居民身上所具備的“戍所心理”的典型體現。在這種心理暗示的指導下,一旦面對外部城市的復雜與迷惑,很容易就讓人選擇了敵意與防備。所以班尼叔叔很快就返回了小鎮,回到那個讓他感到安全的生存環境中。可以說,這種“返回”,同樣屬于“戍所心理”指導下的逃避結果。
除了這種對于以城市為代表的外部世界的恐懼,“戍所心理”的另外一個體現就是小鎮居民對城市里面的人的敵視與排斥。在《活體的繼承者》里面,講到過作為小鎮里面傳統女性的典型代表的格雷斯姑媽和埃爾斯佩斯姑媽,面對以為城里律師的來訪時表現出的是戲謔般的模仿:“他是個貪吃的年輕人,或者只是不知所措,……從桌子對面傾身問道:‘你一直——對鄉下生活——感興趣嗎?”本質上,兩位姑媽并不都是慣于苛責別人的人,她們無微不至的關懷著家人,辛苦勤勉的終年勞作,和所有人到中年的女性一樣喜歡說話和嘮叨,但是,當她們面對城里面來的律師時卻是完全不同又一致的譏誚態度。其原因就在于,在兩位姑媽看來,這種譏誚的態度才是面對小鎮之外的人的正確態度,而她們不過是在維護自身群體的道德秩序。除了這種對于外來人口的敵視,小鎮居民還直觀的排斥外來人口。小說集中有一個人物叫做博奧斯先生,是黛爾學校里面一位普普通通的教師,而他與眾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是一個英國人。國籍的不同使得博奧斯先生在小鎮中顯得有些格格不入。《變遷與儀式》當中,門羅寫到盡職盡責的博奧斯先生向他的學生們播放音樂并詢問感受時,他得到的反饋卻是這樣的:“他總是拿一臺錄音機來教室播放《1812序曲》這樣的東西,……他不高興地看著我們說:‘我想你們不是沒有什么想法,而是不用心去聽。”《1812年序曲》是由柴可夫斯基作于1880年的管弦樂作品,其創作的初衷是紀念1812年俄國人民擊退拿破侖大軍的入侵從而贏得了俄法戰爭的勝利。博奧斯先生深知該序曲背后的故事,并兢兢業業的想要將這種情緒傳達給他的學生,但他的初衷卻得不到學生的體諒,甚至被視為“一個猥褻的問題”。而這一切的原因不是因為學生們聽不懂,而是學生們更在意的是博奧斯老師的身份因此選擇放棄溝通。比樂曲更難懂的是人心,而人心產生隔閡的原因就在于彼此不同的國籍身份。這種隔閡,同樣屬于門羅筆下的“戍所心理”,加拿大傳統文化中對于英國文化的排斥心理由此可見一斑。
弗萊在《加拿大文學史》中的《結論》一章中談及“邊塞戍所”時曾經這樣認為:邊塞戍所作為一個“團結緊密的,……要么是臨陣脫逃。”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兩位姑媽對城市人口的敵視以及孩子們對于英國人身份的博奧斯先生的排斥,恰恰屬于“戍所心理”中的“奮勇向前”的態度,處在戍所中的人堅定的守護著自己長久以來的道德準則,并以此作為評判他人的標準;而班尼叔叔想要在多倫多城市中尋人而不得的經歷,則驗證了諸伯利小鎮居民身上的“臨陣逃脫”態度——因為無力反抗,所以選擇徹底的放棄,回歸故里。合二為一,門羅通過自己筆下的小說世界的細致描繪,體現出了完整的“戍所心理”在加拿大國民心理中的深遠影響。
眾所周知,門羅對于她所生活過的小鎮威漢姆鎮一直都有抱有濃厚的懷念之情,以至于該小鎮的形象頻頻被改寫并出現于作家的多部作品中。作品集《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中的小鎮諸伯利同樣是門羅自身故鄉的一個投射。但是,作為一名稱職的文學創作者,門羅又不止滿足于再現故鄉,而是將更多細膩的研究視角與敘述筆觸投注到更廣闊的加拿大文學當中,其小說中“戍所心理”的展現就是她這種文學努力的表現。文學不止承擔著“講故事”的職能,更成為一種傳承,文脈的傳承,文學精神的傳承。可以說,正是后者的力量推動著門羅在加拿大現當代文壇中的獨樹一幟,并最終作為加拿大文學的代表受到世界文壇的矚目。
參考文獻:
[1]艾麗絲·門羅,《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馬永波、楊于軍譯,譯林出版社,2013.
[2]諾斯洛普·弗萊,《加拿大文學史·結論》,夏祖煃譯,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