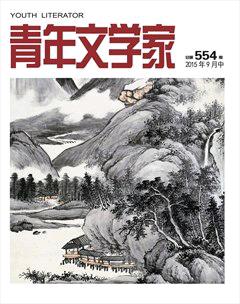簡析文學文體學在小說翻譯中的重要性
李哲
摘 要:文學作品的文學價值體現在內容和呈現內容的形式兩個方面。內容是一部文學作品的血肉,而形式更像是文學作品的骨架,有時,形式甚至比內容更加重要,比如,詩歌。形式可以體現作品的內容,表現作家不同的寫作風格,增強作品的主題意義。傳統的小說翻譯往往重內容而輕形式,忽視形式的意義及其文體學效果。文體學連接了語言學和文學批評,探討作者如何通過對語言的選擇來表達和加強主題意義和美學效果,因此,在翻譯中,我們可以用文體學的方法來探討譯文如何做到既與原文所體現的形式相照應,同時又符合譯文的形式特征。老舍先生的《駱駝祥子》,風格獨特,對于譯者而言,體現原作者的風格與特色具有挑戰性。因此,本論文旨在對《駱駝祥子》文本及其譯本進行比較分析, 考察譯文是否體現了原作的文體特征,并探討從文學文體學的視角對翻譯進行考察的重要性。
關鍵詞:文學文體學;小說翻譯;《駱駝祥子》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26-108-02
1、導言
文學作品的價值既在于內容,又在于文體。然而,在國內,對文體的討論一般不外乎主觀印象式的評論(申丹,2002)。在翻譯方面,特別是小說翻譯方面,人們傾向于主觀印象式的分析,往往認為只要譯文與原文在內容情節方面大致相同,那么,這樣的譯文就是好的譯文。但是,忽略了文體,文學作品的價值將大打折扣,這樣的翻譯是不值得提倡的。
Leech和Short在《小說中的文體》一書中,采用了以下模式來描述形式與內容的關系(1981:24):
意思[內容、事實]+[表達形式的]文體價值 =(總體) 意義
文學文體學家認為同樣的內容可以采用不同的表達形式來表達,內容是不變量,具有不同文體價值的不同表達形式才是變量,才是文體研究的對象。(申丹,2002)而在翻譯中,這兩者都成了變量,這時,人們往往在兩者中選擇內容而放棄形式,這就造成了一種“假象等值”現象,削弱了原文的主題意義和美學價值。村上春樹、老舍、莫言、王小波等就是這樣的作家,他們的小說風格獨特,有極強的文體學價值,若在譯文中不能體現原作的文體而僅僅是內容上的語言轉換,這將使原作的價值大打折扣。
因此,在翻譯小說時,結合文學文體學就變得尤其重要。本文將重點以《駱駝祥子》的施曉菁譯本為例,探討文學文體學在小說翻譯中的重要性。
2 、文學、文學文體學初探與《駱駝祥子》的語言特色
2.1文體、文學文體學
文體:(1)Style as genre or period characteristics.
文體學: Study of the style of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and how it is used to create certain effects.(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文學文體學:文學文體學是西方現代文體學的一個分支。西方文體學走過了一個世紀(20世紀)的發展歷程,近來的發展勢頭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是以社會歷史/文化文體學為代表的緊跟時代潮流的傾向;二是多頭并進,不同的文體學派競相發展,不斷有新的文體學派形成。
“文學文體學”有廣狹兩義:它可泛指所有對文學文本進行分析的文體派別,也可特指以闡釋文學文本的主題意義和美學效果為終極目的的文體學派。但也有人將文體學作為連接語言學與文學批評的橋梁,探討作品如何通過對語言的特定選擇來產生和加強主題意義和藝術效果,這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文體學”(申丹,2000)。
2.2 《駱駝祥子》和老舍
2.2.1《駱駝祥子》
《駱駝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品,小說講述了車夫“祥子”的悲慘的一生,語言幽默,“京味兒”十足,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同類作品中的佼佼者。翻譯此類作品時,除了要在內容情節上下工夫,在譯作中體現原文的語言和文體特色似乎對譯者來說是更大的挑戰。國內對《駱駝祥子》英譯本的研究不多,角度也較單一,多數是對英譯本進行主觀性的評價,缺少客觀性的分析。
2.2.2老舍的語言特色及文體風格
1899年,老舍生于北京的一戶貧民家庭,父親陣亡于八國聯軍侵占北京城的戰爭中。他原名舒慶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筆名。在40多年的創作生涯中,老舍廣泛地涉獵文學創作的各個領域,是位多產作家,一生寫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如《老張的哲學》、《離婚》、《老牛破車》、《駱駝祥子》、《歸去來兮》、《國家至上》、《誰先到了重慶》、《桃李春風》、《貧血集》、《火葬》、《東海巴山集》、《微神集》、《月牙集》、《方珍珠》、《龍須溝》、《老舍選集》、《春華秋實》、《老舍短篇小說選》、《福星集》、《茶館》、《上任》、《四世同堂》。
老舍的語言風格突出,是位語言大家。老舍重視民族性,雖然他有出國留學經歷,但是他的作品并未西化,《駱駝祥子》通篇充滿了北京方言,短小精悍、簡潔明快、風趣幽默。同時,他的作品的語言都非常生動形象,充滿了獨創性。要想將像老舍這樣的文學巨匠譯介到國外,除了要將原作內容傳達出來以外,同時要譯出原作者的風格特色,體現中國文學的文體特征,這些都給譯者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3、簡析《駱駝祥子》施曉菁譯本
3.1 詞匯層面
3.1.1 口語化
(1)我們所要介紹的是祥子,不是駱駝,……隨手兒把駱駝與祥子那點關系說過去,也就算了。(p.1)
Shi: This story is about Xiangzi, not about Camel, because “Camel” was only his nickname. So let us start with Xiangzi, just mentioning in passing how he became linked with camels.
分析:與King的譯本相比,Shi的譯本更加口語化。King和Shi分別將“介紹”譯為“introduce”和“about”,“introduce”稍顯正式,在這樣口語化的語境中不如“about”更加簡潔;原文的后半句十分簡短,Shi簡單地一句帶過,而King譯則稍顯繁瑣,沒有體現原文口語化的特點。
(2) 小心與大膽放在一處,他便越來越自信,他深信自己與車都是鐵做的。(p.12)
Shi: Combined daring and caution increased his confidence and convinced him that they were both indestructible.
分析:施曉菁將原文的三個短句濃縮成英文的一個長句,既表達了原文的內容,同時簡練的傳達出原作簡潔的特色。
(3) 有自己的力氣與洋車,睜開眼就可以有飯吃。(p.4)
Shi:…earning his living would be more childs play. (p.10)
分析:在這一句中,施曉菁用了一個簡單句來翻譯此句,體現原文口語化的特點,簡單明快。
3.2遣詞造句
(4)他的記憶是由血汗與苦痛砌成的,不能隨便說著玩。(p.203)
Shi: His memories, made up of blood, sweat and pain, couldnt be lightly voiced. (p.219)
分析:Shi沒有用“composed of”,而是用“made up of”,她的譯文所體現的口語化不僅表現在詞語方面,還體現在詞組方面。
(5)這些人,生命最鮮壯的時期已經賣掉,現在再把窩窩頭變成的血汗滴在馬路上。(p.2)
Shi: These men have already sold the best years of their lives, and now the maize muffins on which they subsist are transformed into blood and sweat which drip onto the road.
分析:此句中,“賣掉”一詞深深地體現老舍對車夫的同情之心,而Shi直接將其譯為“sold”,簡單明了。
3.3語法層面
(7)一年,二年,至少有三四年;一滴汗,二滴汗,不知道有多少萬滴汗,才掙出那輛車。(p.3-4)
Shi: It had taken him at least three or four years and untold tens of thousands of drops of sweat to acquire that rickshaw of his. (p.10)
(8)車,車,車是自己的飯碗。買,丟了;再買,賣出去;三起三落,象個鬼影,永遠抓不牢,而空受那些辛苦與委屈。沒了,什么都沒了,兩個老婆也沒了!(p.181-182)
Shi: Why, a rickshaw was his rice-bowl! He had bought one and lost or, bought another and lost it. Twice he had attained his ideal only to lose it again, putting up with all those hardships and wrongs for nothing. He had nothing, nothing, even his wife was gone!
分析:漢語的中的重復往往是為了加強效果,渲染感情。而這兩句的翻譯,Shi直接譯出原文意思,而忽略重復的形式,這樣做不利于展現原文特有的語言風格。
4、結論
通過以上文本分析,可看出,“文體”體現在小說的方方面面,在翻譯小說時,要時刻將“文體”的概念銘記于心,最大限度地再現原作的文體。文體是文學作品的第二生命,失去了文體,同樣主題的文學作品的價值將大打折扣,對原作如此,對譯作來說更是如此,甚至對譯作的要求更高,因為譯作不僅要體現原作的文體價值,更要符合譯語的文體規律,因此,翻譯中的文體研究不可忽視,對文體的研究有助于譯者整體把握翻譯進程,且在具體的翻譯操作過程中,對翻譯實踐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參考文獻:
[1]Dan Shen. Literary Stylistics and Fictional Transla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2]Shi Xiaojing. Camel Xiangzi.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1988.
[3]老舍. 駱駝祥子[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5]邵璐. 西方翻譯文體學研究[J].中國翻譯,2012(5).
[6]申丹. 論文學文體學在翻譯學科建設中的重要性[J].中國翻譯,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