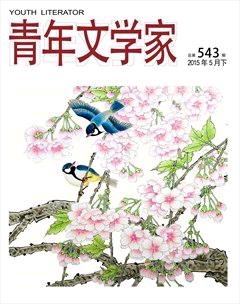漁歌舉棹,谷里聞聲
摘 要:禪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土壤,對宋詩的藝術風貌和審美特征產生了重大影響。宋詩中的禪意,不僅體現在“以俗為雅”風格的形成,也滲透在向內審視,重在“妙悟”的人生態度,以及由禪的開悟所致的人生觀的根本性轉變,即對生命的關注,對生命自由境界的追求。
關鍵詞:宋詩;禪意;以俗為雅;妙悟;生命追求
作者簡介:張云鶴,女,河南平頂山人,1993年6月4日出生,河南大學本科,學生,漢語言文學方向。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15-0-02
兩宋時期,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進一步強化,影響著宋朝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面貌和思想狀況。理學的產生,使宋人的文學精神具有更深厚的內蘊和更寬廣的境界。而宋代禪宗的巨大變化,也促使宋代詩學有著對藝術至境的普遍追求,并且深受禪宗思想的觸發和影響。禪宗文化博大精深,本文僅淺論宋詩中的禪意。
一
再宋代,“以俗為雅”成為廣為流傳的口號。若陳師道《后山詩話》中的記載屬實,則這一觀點最早由梅堯臣提出。而后,蘇軾和黃庭堅不僅對此大力倡導,并且也擴充了“以俗為雅”的內涵。宋詩能突破極盛一時的唐詩,呈現出鮮明的獨特風貌,便與此密切相關。
首先,“以俗為雅”表現在詩歌題材方面的生活化。到了宋代,北宗禪早已消亡,南宗派一系產生出禪門各派,禪宗日益士大夫化。禪宗思想并無重大發展,但這種日用的生活態度和宗教實踐滲透在士大夫的生活與創作中。不論是閱讀公案,還是與禪僧交游,都會接觸并受這種思想的影響。
宋詩在取材上不受限制,“緣情”和“體物”的融合使題材擴大到“無所不包”的程度,除了政治和社會問題題材,生活中隨處而有的詩意都被發掘出來。如賀鑄的“黃草庵中疏雨濕,白頭翁媼坐看瓜”1,寫的就是一對老夫妻坐在瓜棚里看瓜的場景;肖德藻的《采蓮曲》更有韻致:“清曉去采蓮,蓮花帶露鮮。溪長須急漿,不是趁前船。”2說的是采蓮人一大早匆忙劃船去采蓮,怕別人誤會是與情人幽會,就自言自語解釋說是因小溪太長怕誤了干活。題材雖俗,但追求生活本身,發掘生活中的詩意,便是“雅”的行為活動。
其次,還表現在語言的通俗化。文同的詩《早晴至報恩山寺》并未用生僻字詞,詩人用簡淡的筆墨、質樸自熱的語言,營造出具有詩情畫意的意境,簡單而又清新。有的詩人直接用禪籍詞語入詩。黃庭堅在《病起荊江亭即事十首》中直接使用“菩提坊”和“維摩”3等佛籍用語,這些“俗”語透露著禪與詩的融會貫通。無論是詩歌體裁的選取,還是詩歌語言的運用,都與詩人的內在精神相一致,外在形式之下蘊藏的是內在的張力。
二
宋代文化氣氛濃厚。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強化滲透了宋代文人的思想意識,強烈的正統觀念使他們具有憂患意識和民族氣節。統治者對知識的尊重,對知識分子的優厚待遇,對文化建設事業的重視,促使知識分子發奮讀書,他們的學識無論在廣度和深度上都為前代所不及。理學建立了以“理”為核心的新儒學體系,融合佛道思想為其注入新的源泉。以上,不僅使寫實的傳統得以發揚,宋人也將對外搜尋、期盼的目光轉向內在的反省審視,將外在的強制力量轉化為內在的精神力量。
這種內向審視,與取得佛法所必經的修行相吻合。南懷瑾在《禪話》中說“諸佛法印,匪從人得”,他在書中更將“修行”的“行”分析為“‘心行和‘行為兩方面的自我省察、自我修行的實證經驗”4因此,禪重在真參實證,悟是禪的核心和靈魂。
由此,儒家的實踐理性精神和禪宗的參悟方式相結合,宋詩中別有一番禪意。蘇軾的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以及楊萬里的“正入萬山圈子里,一山放過一山攔” 5都是通過“置身其中”的方式闡明道理,可以看出作者的態度是客觀而又冷靜的,這也是向內審視的結果。正如參禪者整日鉆研佛法真諦,反而偏離了禪的智慧。
可以說,“向外”是為了獲得契機,“向內”才能真正將生活體驗與宗教修行實踐相結合,“向內”返觀的關鍵,則在“妙悟”。
“妙悟”一詞出自《壇經》,是說“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是解脫”6。慧能禪宗在宗教實踐上提供的是“頓悟說”,是主觀能動性達到一定程度達到的質變,因此宋詩中的禪意離不開作者的“妙悟”。
下面以陸游的《游山西村》為例進行分析:這首詩記述了他游訪山西村的所見所感,詩中名句“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7不禁讓我們想到“頓悟”,作者看似無意,實則是“妙悟”后的結果,作者在“妙悟”中發現了自己的本心。這里民風淳樸、生活閑適,人民熱情好客,作者在贊美、與農民親近的同時,也與本心相契合,約定他日再來。皎然在《詩式》中提出“苦思”與“自然”的關系:“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見,成篇之后,觀其氣貌有似等閑,不死而得,此高于手”8,他認為“苦思”錘煉才能達到貌似自然的至境。因此,宋詩中的禪意背后,是詩人的良苦用心,體現的是對生命境界的追求。
三
宗白華先生曾在《美學散步》中說:“禪是動中的極靜,也是靜中的極動,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動靜不二,直探生命本源。禪是中國人接觸佛教大乘義后體認到自己心靈的深處而燦爛發揮到哲學境界和藝術境界,靜穆的觀照和飛躍的生命構成藝術的兩元,也是禪的心靈狀態。”9他將禪的特質與哲學、藝術相結合,最后歸結到對生命本源的探尋,可見,禪意中體現的是對生命的關注,對生命自由境界的追求。
蘇舜欽的《淮中晚泊犢頭》詩云:“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10作者從白天行船的場景寫起,看似景動實則船行。天色已晚詩人將小船停在古廟下,風雨交加潮水升高時詩人已穩坐古廟中。動中觀靜,靜中觀動的構思,作者獲得的是作為旅人的孤寂之外的悠閑從容,流露出置身于天地間的超然物外。
蘇軾為《春江晚景》作的題畫詩更具韻致,詩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萎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11簡單四句無一字閑筆。江水回暖的訊息水中嬉戲的鴨子預先感知到了,詩人感知到鴨子的“感知”,可見詩人的思維已經推己及物了,字里行間流露出清新明快的動感。看似是對自然的細致觀察,實則是哲理性思考后對生活、生命本身的關注和享受,盎然春意背后是思維的靈性所在,也是生命的自然流動。
葛兆光曾這樣分析:“生活對于文人士大夫來說總是有雙重意味的:一方面是責任與義務的完成,一方面是對自由與超越的追求。……而對自由與超越的追求則使他們總是在尋找一種思想與實踐,以期在這種思想里找到擺脫俗務的依據,在這種實踐中尋覓人生的輕松與瀟灑。”12他們因現實生活而逃離到禪宗思想中,有通過它的滲透返觀自身和現實生活,這樣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中,詩人的生活態度和生命追求都發生著改變,即越來越關注生命本身、追求超越性的生存方式,也逐漸忘卻了自我,禪意便是無意。
最后,用一段對話作為本文結尾:
問:“亡僧遷化向什么處去?”師曰:“長江無間斷,聚默任風飄。”曰:“還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即不無。”僧曰:“如何祭祀?”師曰:“漁歌舉棹,谷里聞聲。”13
注釋:
[1]喻朝剛. 《宋詩三百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64
[2]喻朝剛. 《宋詩三百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115
[3]喻朝剛. 《宋詩三百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57
[4]南懷瑾. 《禪話》.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16,21
[5]喻朝剛. 《宋詩三百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49,112
[6]郭朋. 《壇經校釋》.中華書局.1983:60
[7]喻朝剛. 《宋詩三百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85
[8]李壯鷹.《詩式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39
[9]宗白華. 《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65
[10]喻朝剛. 《宋詩三百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23
[11]喻朝剛. 《宋詩三百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49
[12]葛兆光. 《中國禪思想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276
[13]釋道元. 《景德傳燈錄》.商務印書館.1963: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