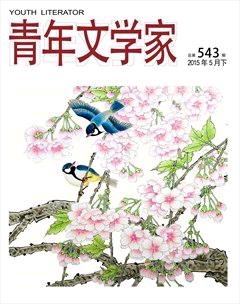對生之可能的試探
摘 要:對卡夫卡作品的解讀歷來爭議頗多,《城堡》更是這種爭議之最。解讀者們總想繞開《城堡》的后十七章中看似不知所云的嘮叨,但這偏偏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要真正理解“城堡”的含義,關鍵就在后十七章之中。從文本細讀入手,可以從對人物關系、對話、敘述方式的分析中找到一種對“城堡”的合理解釋。
關鍵詞:城堡;生存境遇;生存試探
作者簡介:起建飛,女,玉溪師范學院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方向的教學與研究。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15-0-02
迄今為止的《城堡》閱讀史,也是一部“城堡”的解釋史。人們對這部小說尤其“城堡”這一意象做出了種種不懈的解釋,卻無法真正說明,卡夫卡究竟為什么要用占據整部小說(全書二十章)主體的十七章來描寫那些喋喋不休的對話。可以說,對小說后十七章的解讀恰恰是揭開“城堡”之謎的關鍵。不論將“城堡”看作是神的“仁慈”、上帝的權威,是官僚體制的象征,是不可逾越的障礙,還是荒誕世界的形式,或甚至就把它當作卡夫卡真實生活的寫照,每種解釋都有其合理性,但任何的解釋都需要在對文本的解讀中找到佐證。
《城堡》后十七章基本上是對話構成,對話在什么人之間展開、如何展開,就成為理解這些對話的關鍵。
一、隱藏于對話人物中的“個體”與“他者”的關系
在這十七章的對話中,主人公K構成固定的一極,而與之展開對話的主要對象依次大致如下:
第四章——老板娘
第五章——村長
第六章——老板娘
第七章——教師
第八章——女招待佩瑟、馬車夫、城堡的一位老爺(莫穆斯,克拉姆的村秘書)
第九章——莫穆斯、老板娘
第十章——信使巴納巴斯
第十一章——弗麗達
第十二章——男女教師、弗麗達
第十三章——弗麗達、小男孩兒漢斯
第十四章——阿瑪莉婭
第十五章——奧爾珈
第十六章——助手、巴納巴斯
第十七章——兩位城堡老爺、馬車夫
第十八章——弗麗達、秘書畢格爾
第十九章——秘書艾朗格
第二十章——佩瑟、老板娘
這些人(姑且統稱為“他者”)或親或疏,構成了K來到村子后的主要人際關系。
其中,弗麗達與K是情人或更準確說是一度的伴侶,他們甚至想過要結婚,由此構成K最密切的一種“個體”與“他者”的關系。在他們的談話中透露出兩人最初都本著一種“需求”的心態走到一起。但是短暫結合使弗麗達失去了原有的工作、情人克拉姆的眷顧和全部生活,也使K不得已接受了學校雜役的工作來維持二人的生計。但是雙方都沒有得到原本希望的東西。弗麗達想要全部抓住K,但是K卻覺得“從根本上說,事情的關鍵就在于弗麗達,因為使他關心的事都與弗麗達有關。因此,他必須……忍受……通常無法忍受的痛苦,他絲毫不能表示后悔。”【1】 K想通過弗麗達建立與克拉姆與城堡的聯系,可是克拉姆與城堡對他的行為都不予理睬,只是徒然使得弗麗達的生命枯萎,她的活力消失,美色斷送,于是,盡管曾有過結婚的打算,弗麗達還是放棄了這種念頭離開了K。
因為“弗麗達”還曾作為“兒子”未婚妻的名字出現在《判決》中,聯系卡夫卡個人三度訂婚又三度退婚的真實經歷,加上“弗麗達”拼寫首字母F與兩度和卡夫卡訂婚的菲莉斯名字首字母相同,而卡夫卡小說最常見的主人公K(或是名字以K為首字母)又恰好是卡夫卡名字的首字母,很容易讓人認為《判決》、《城堡》有卡夫卡自傳的性質。這些巧合確實存在,而卡夫卡本人也曾多次在日記、書信這些更私人化的文字中表示,是為了在與父親的關系中得到獨立的誘惑促使他想去結婚,他想要借助婚姻擺脫“恐懼、虛弱、自卑”造成的普遍壓力,解除父親的教育帶來的“虛弱、缺乏自信心、負罪感”的性情。但是也不能忽視卡夫卡曾說過:
“我不羨慕個別的夫婦,我羨慕的是所有的夫婦——即使我羨慕的僅是一對夫婦,則實際上我羨慕的是整個婚姻幸福的千姿百態。只生活在一種婚姻的幸福中即使在最有利的情況下說不定也會使我絕望。”
“兩個人在一起時他覺得比一個人時更孤單。如果他同另一個人在一起湊成了兩個人,那第二個人將會來抓他,而他只能聽任擺布。”【2】
在這兩段話里,卡夫卡表達了自己對于婚姻關系的一種看法,他追求的是整個“婚姻”本身的意義,而不是一種具體的婚姻生活。所以,弗麗達(或者說F)與K不是菲莉斯與卡夫卡或者任何一種具體婚姻的寫照,而是卡夫卡借以對婚姻關系進行個體性試探的兩個符號。而這種試探既然落實在了個體之上,其結果必然是令卡夫卡失望的。卡夫卡認為生命存在兩個時鐘,而“兩個時鐘走的不一致。內心的那個時鐘發瘋似的,或者說著魔似的,或者說無論如何以一種非人的方式猛跑著;外部的那個則慢騰騰地以平常的速度走著。……兩個世界是以一種可怕的方式分裂著,或者至少在互相撕扯著。”【3】卡夫卡的生命追求也有兩個,一方面要在孤寂中奮力寫作——“我身上的一切都是用于寫作的”,一方面他也有對于一個“女人”的渴望。如果要將這兩個追求結合,只有一種可能,就是他曾在書信中描繪的:有一個女人在身邊靜靜地看著他寫作。支持卡夫卡寫作的是“內心”的時鐘,而這個時鐘正在激烈的奔跑中驚人地被消耗著。可是,“女人”渴望的卻不僅是進入“外部”那個時鐘,“她”會要努力抓住“男人”的全部,從而也占有“內心”的時鐘。因此,婚姻將會不幸地與卡夫卡追求的目標相抵觸。卡夫卡追求婚姻的最初動因是擺脫被籠罩在父親夢魘之下的“虛弱、恐懼”,K追求弗麗達的動因是為了驅散在“異鄉”的孤獨以及挑戰克拉姆成功的虛榮心,其結果反而都是對最終目標的耽擱。于是,K將一切罪責推到了弗麗達的身上。由此,在這一試探中卡夫卡找到了對待異性與婚姻的辦法:把這一切視為“惡的誘惑”,并本能的拒絕它。
弗麗達之外,其他人可以歸為這樣幾類:(1)奧爾珈、阿瑪莉婭姐妹以及信使巴納巴斯這一家人是多少有與K相似的經歷并對K表示出了最大程度友善的村民。(2)城堡里的官員、村長、教師、助手與K構成工作上的上司、同僚、從屬的關系。(3)老板娘、佩瑟、馬車夫是與K有接觸的普通人。加上那些躲著K,自然也就不大可能與他對話的更大多數的村民,這就是一個完整的人際體系。這些人在話語中對K起到了不同的作用。比如,老板娘揭示了K的真實處境:“不過是個外鄉人,一個多余的、到處礙手礙腳的人”。助手們想讓他開心輕松;教師總對他說些引起他思考的話;漢斯讓他感覺滿足;官員們聽任他為所欲為(在村子范圍內)而不聞不問……在這些“說者”的角度,他們無非在用自己的話語展現各種不同的生存境遇,以及這種境遇的合理性。然而在K看來,這些人的行為都是對自己的妨害。這種心態下,不僅是“別人”在回避K,K自己其實也在切斷與“別人”的聯系。第一章中K來到村子的第一個早上,與教師相遇并談話后,他深深感到結識他人,最終增加了生命的疲憊感。K也不是沒有與他人友好相處的可能,但是,任何的耽擱都可能成為對目標的延宕。偏偏K缺乏對這些延宕的抵制能力,在這一點上,K具有矛盾的性格,他會因為與他人的隔絕而覺得孤獨而痛苦。既體會著與他人隔絕可以獲得的自由,又感受著這份自由所帶來的絕望。
K的這種矛盾與卡夫卡自身的矛盾相關。不具備父親強悍的性格,生性羞怯的卡夫卡只有借助K來試探命運——當目的遇到阻礙時,怎么辦?想達成目的的“內心時鐘”腳步匆匆,而由這些人物關系編織成的外在世界的時鐘卻拖拖拉拉,慢慢騰騰。兩個時鐘彼此分裂撕扯,任何人物所代表的人際關系都成為終極目標的妨礙者。當K在最后一章又把對話對象重新設定為第四章對話開始時的對象,仿佛卡夫卡又開始了借對話者展開對隱藏于人際關系下的生活模式的新一輪探討。
二、“復調式”敘述下的自我辯難
在《卡夫卡的〈訴訟〉和〈城堡〉中敘述的方式與時間的演變》一文中,庫楚斯分析了《城堡》在敘述上最明顯的一個特點:敘述節奏的改變。小說前三章大約占全書的六分之一,所涉及的時間卻與后十七章大致相同。大量引入的對話,使得敘述節奏一下子慢了下來。庫楚斯認為,這種變化說明K為了達成目的的行動越來越少,意味著K進入城堡的可能也越來越渺茫。這個解釋顯得過于簡單了。
如前文所述,對話使得每個人都有機會從自己的視角來展現自己的生存狀態,這就具有了“眾聲喧嘩”的復調性質。而復調式敘述往往代表的是作者內心的自我辯難。因為無法在現實中找到多重生存狀態孰優孰劣的答案,卡夫卡只有讓這些狀態在文學中自己去對話,并用文學來對這些存在之間的“邊界”發起“沖擊”。所以,K就決不可能是卡夫卡自己,而只是卡夫卡用以試探生存可能性的一種存在方式,甚至多少透射出卡夫卡本人生活狀態的影子。此外,敘述的節奏也是一種心理時間的節奏。卡夫卡的兩個“時鐘”也一樣。K受飛速旋轉的時鐘支配,其實是受到了急迫的心情的驅使,而其他人的世界則不緊不慢。前三章里,K還能堅持自己的時鐘,但是他一無所獲,一任時間流逝。到了后十七章,他被拖入了他人的時鐘,不得不放慢了腳步。在這段時間里,K最大的收獲是思考,包括對城堡的思考:
“每當K觀察城堡時,他有時就覺得好像是他在觀察某個人,這個人靜靜地坐在那兒,眼睛看著前方,他不是在沉思,也不是旁若無人,無所顧忌,而是自由自在,無憂無慮……”【4】
“城堡”是K一直想要到達的目的地,可是它真的存在嗎?在小說的開頭有一段對城堡的描寫:“城堡屹立在山岡上,但在濃霧和陰沉沉的夜色籠罩下,不見山岡的一點兒影子,連能夠顯示出那里有座高大城堡的一絲兒燈光也沒有。一座木橋從大路通向村子,K久久地站在木橋上,仰望著虛無縹緲的天空。”【5】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那時K能肯定城堡就在山崗上,可放眼看到的卻是虛無。當第二天早上,K再看城堡,看到的是一堆雜亂的建筑,令人難以置信那就是城堡。而此刻,城堡卻如同一個沉思中的人,安靜不動,你可以看到它,卻無法將視線集中到它之上。一方面,K已經越來越勢單力薄,但同時,他也越來越了解城堡的存在。城堡是他無法撼動的安寧。K兜了個大圈子,又重新回到了起點。當K與老板娘又一次就自己是不是土地測量員而辯解時,小說中止了,K也完成了卡夫卡賦予他的這一輪對于生存境遇可能性的試探。
小說的突然中止,構成了《城堡》在結構上的第二個顯著特點:開放式的結尾。之所以說中止而不是結束,是因為K并沒有到達目的地,而是可能又將開始新一輪的努力。這樣的結尾比讓K真的進入了城堡更加意味深長。沒有達成目標,就將繼續在路上。這是K與他在村子里遇到的所有人的區別,其他人都認為尋找到了合理的目標而停滯于安寧的生活。于是他們住下來了,于是才有了村子,村子延伸了,就有了城堡。K本來也可以停留,比如就老老實實和弗麗達結婚、老老實實做校役,任何一種方式都可以讓他在此定居成為村民——換言之就是進入了城堡。別人早就說過,村子是城堡的,村子和城堡本是一體。然而,K選擇了到不了的城堡,而不是眼前的村子。
經過這番對文本的細讀,“城堡”究竟是什么已經變得不重要了。就像奧爾珈說克拉姆這個與城堡最密切的人的樣子會因為人們的希望而變一樣,“城堡”也因為人們對它的希望的不同而離人或遠或近。也許它就是每個人想要到達的“那邊”,它存在的價值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它決定了跋涉的路有多遠。奧登說:“唯一能說明K走在正道上的跡象是他四處碰壁,如果他成功地到達了他的目的地,那就證明他失敗了。”【6】如果K在這個開放的故事可能的新一輪次中仍然堅持走在路上,那么卡夫卡以小說展開的對生存境遇可能性的試探就將延續下去。
細讀過這十七章,讀者會更加了解卡夫卡一生的孤獨。K也好,書中的任何人也好,他們還有在生存可能性試探中取舍的自由,卡夫卡卻一生都與這種自由無關。他早已放棄了取舍,放棄了懈怠。然而,這世上,畢竟只有一個卡夫卡。
注釋:
[1]《城堡》卡夫卡著,米尚志譯,譯林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149頁。
[2]《卡夫卡集》葉廷芳編選,葉廷芳等譯,上海遠東出版社2003年1月版,553、559頁。
[3]同上,555頁。
[4]《城堡》卡夫卡著,米尚志譯,譯林出版社2003年8月版,96頁。
[5]同上,第1頁。
[6]《論卡夫卡》葉庭芳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9月版,1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