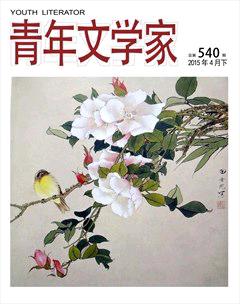格律詩中不應失去的音韻美
于淼
摘 ?要:世界各國語言文化存在著巨大差異和多元化,這便凸顯了翻譯工作的相對性。而一些詩歌的可譯性,例如格律詩,也由很少譯向大部分可譯轉變。在翻譯詩歌的過程中,詩歌的“形式”和“內容”在翻譯是個的過程中,其矛盾也變得越來越明顯。處理好詩歌翻譯中的“形式”與“內容”的關系,便成為詩歌翻譯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詩的音韻美和詩歌本身是互相依賴而存在的。本文從《英詩賞讀與美感再植》此書中,節選出例子,試從詩的音美與形美兩個方面,闡述音韻美在翻譯詩歌過程中的重要性。
關鍵詞:格律詩;翻譯;音韻美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12--02
“翻譯難,譯詩更難,”已經成為很多翻譯家的共識。原詩的音韻和格律,在翻譯詩歌的過程中,很難做到完美呈現。詩歌的音韻美使得詩歌有別于散文,小說,而被稱之為詩歌。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總是把對詩歌的意境和思想作為首要的翻譯對象,而忽視了音韻的翻譯。由于譯者在翻譯詩歌的過程中,忽視了對原詩音韻的再現,而導致譯詩失去原有的節奏和韻腳,使讀者讀起來索然無味,從而失去了原詩的價值。真正的詩,都應該是帶有韻律的。朱光潛先生就曾說:“詩是一種有韻律的純文學”。由此可見,作為譯者,我們應該意識到,再現原詩的音韻美,才是我們在譯詩的過程中的首要任務。
1、詩歌的音美
詩之所以也被稱為詩歌,是因為詩與歌的之間的關系密不可分。“最常見的兩種音韻美就是押韻和節奏(平仄與四聲),和漢語相比較,英語多以多音節作為其音美的基礎。”在翻譯實踐中,我們不可能完全照搬原詩的音韻美,但是譯者可以通過把握英譯詩歌的特點,將原詩的音美“移植”到譯入語中。
例1: ? ? ? ? ? ? ? Spring
Thomas Nash
Spring , the sweet spring , is the years pleasant king;
Then blooms each thing, then maids dance in the rain,
Cold doth not sting, the pretty birds do sing;
Cuckoo, jug-jug, pu-we, to-witta-woo!
The palmand may make country houses gay,
Lambs frisk and play, the shepherds pipe all day;
And we hear aye birds tune this merry lay;
Cuckoo, jug-jug, pu-we, to-witta-woo!
The fields breathe sweet; the daisies kiss our feet,
Young lovers meet,old wives a-suning sit;
In every street these tunes our ears to greet;
Cuckoo, jug-jug, pu-we, to-witta-woo!
Spring, the sweet spring!
該詩屬格律體,每行五音步,抑揚格,每節三行同韻,外加模擬鳥鳴之聲的第四行。此外,行內韻、單音節詞以及疊句等手法被大量使用,對整詩墊下了歡愉的氛圍,朗誦起來朗朗上口。
Version 1: ? ? ? ? ?春
T. 納希
春光,好春光,一年歡樂春為王;
催開百花放,少女翩翩環舞忙,
風停刺骨涼,艷鳥枝頭高聲唱;
咕咕,啾啾,噗喂,吐-喂特-嗚!
棕櫚綠,山楂美,村舍融融頓生輝,
羊羔樂相追,牧人笛兒整日吹;
鳥唱歌聲脆,聲聲入耳人陶醉:
咕咕,啾啾,噗喂,吐-喂特-嗚!
田野上,香氣飄,雛菊親吻人雙腳,
情侶頻頻邀,老婦沐浴陽光照;
鳥鳴遍街道,唱得人心樂陶陶,
咕咕,啾啾,噗喂,吐-喂特-嗚!
春光,好春光!
Version 2: ? ? 春
T. 納希
春,甘美之春,一年中的堯舜,
處處都有花樹,都有女兒的環舞,
微寒但覺清和,佳禽爭著唱歌,
啁啁,啾啾,哥哥,割麥,插一禾!
榆柳呀山楂,打扮著田舍人家,
羊羔嬉游,牧笛兒整日價吹奏,
百鳥總在和鳴,一片悠揚聲韻,
啁啁,啾啾,哥哥,割麥,插一禾!
郊原蕩漾香風,雛菊吻人腳喱,
情侶作對成雙,老嫗坐曬陽光,
走向任何通衢,都有歌聲悅耳,
啁啁,啾啾,哥哥,割麥,插一禾!
春!甘美之春!
鑒賞:這首英語格律詩描述的是一派春意盎然、生機勃勃的景象,兩首詩既壓了腰韻,又壓了尾韻。比如,第一篇中譯文中的“放與忙”,“涼與唱”,“脆與醉”等;第二篇譯文中也同樣用了音韻美的調試與補充,體現在“游與奏”,“雙與光”等,因此不得不說兩個中譯本都是音韻美在詩歌中體現的典范。相比較文學色彩而言,第一首譯的較符合音樂的節奏,讀起來也更貼近我們的生活與語言習慣,給人一種鄰家妹妹唱兒歌的感覺,親切感油然而生,這體現在多用疊字上:翩翩、融融、頻頻等;而第二譯文則給人文學色彩較高的水準平體現,語言不如第一首樸素,多用生僻字與有文言詩感的短語,美學層次雖上去了,但是不符合大眾的口味,讀起來稍稍難理解些,但是詩歌的美感與措辭的尊貴嚴肅性被體現。兩首詩中,對于意象的翻譯也都大相徑庭,沒有遺落原詩的細節。因此,總體評價就是,兩個譯文在翻譯的過程中所強調的點有所不同:一細化了音樂的美感,是音韻美表達的楷模典范,貼近生活;二是語言文學美得表率,凸顯文字運用的博大精深。
英文詩歌押韻形式照比漢語詩歌的押韻形式更為豐富,除了漢語詩歌常見的尾韻,還有頭韻(alliteration)和中間韻(internal rhyme)。在翻譯漢語詩歌的過程中,譯者可以將中國漢詩的音韻轉變為英詩的格律和韻腳并轉變漢詩的格律節奏,使譯文更容易讓英語讀者所接受。
例:
靜夜思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譯文:
Night Thoughts
I wake, and moonbeams play around my bad, (a)
Glittering like hoar-frost to my wandering eyes;(b)
Up towards the glorious moon I raise my head,(a)
Then lay me down- and thoughts of home arise.(b)
——Herbert A. Glies
鑒賞:
李白在其詩中第一、二、四句末最后一個字“光”(guang)、 “霜”(shuang)、“鄉”(xiang),采用的韻都是“ang”; 在這里,我們更多關注的是譯者對音韻的處理。在翻譯過程中,譯者不僅要做到將原詩的意象和思想翻譯出來,還要更多的關注原詩的節奏,韻律,并使譯文能被讀者接受。漢詩常常具有一定的音樂性,讀起來朗朗上口,所以在英譯的過程中,這種節奏性是萬萬不能丟棄的,這種節奏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幫助讀者理解原文。
2、詩歌的形美
這里的“形”指的是詩歌的對仗、詩句的行數、長短和排列。在漢詩英譯的過程中,主要解決的就是譯者對仗文題。對仗,顧名思義,就是要做到兩個句子里面相對應的詞應該結構相同,詞性相同,節奏相同。
例: ? ? ? ? ? ? ? ? ? ? ? ? ? ? 登高
杜甫
風急天高猿嘯哀,
渚清沙白鳥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
不盡長江滾滾來。
譯文:
The wind so swift, the sky so wide, apes wail and cry,
Water so clear and beach so wide, birds wheel and fly.
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
——許淵沖
這兩聯對仗工整,譯頷聯為例,“無邊”對“不盡”,都是形容詞;“落木”對“長江”都是名詞;“蕭蕭下”對“滾滾來”,對仗工整有序。在英譯文中,原詩中有六個意象,譯者均一一對應翻譯出來,這樣的一一對仗,再現了原文的節奏和美感;頷聯中,譯者也是盡最大努力譯出原文的節奏感,使讀者讀起來不失原文的美感。
由此可見,在翻譯英詩的過程中,譯者要有足夠的能力及素養,并且善于運用形象的手段來表現詩歌中蘊含的思想感情,境界、情趣、韻味和色澤等。詩歌的音韻美作為詩歌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翻譯過程中,絕對不能丟棄。譯者應該再現原詩的美感。
參考文獻:
[1]孫寧寧.詩歌翻譯中的音美和形美.海外英語.第10期.2011
[2]許淵沖.文學與翻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3]李云啟.英詩賞讀與美感再植.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