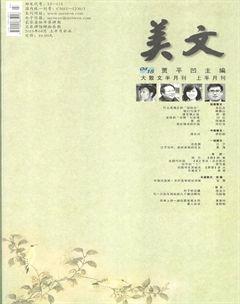目不識“丁”
李守奎
古人論識字喜用“丁”字說事兒,論識字重要,就說起碼得認一個“丁”字。《舊唐書·張弘靖傳》:“今天下無事,汝輩挽得兩石力弓,不如識一丁字。”亂世習武,和平年代就得變變了。四肢發達,一身功夫遠不如習文識字,“汝輩挽得兩石力弓,不如識一丁字”是情急的勸誡,是書中自有黃金玉的另外一種表達方式。罵人沒有文化,就說他連個“丁”字也不認識。明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對于隸變以后的漢字來說,沒有幾個漢字比“丁”字還簡單,而且是使用頻率極高的常用字,如果連“丁”字都不認識,確乎近于文盲了。以“丁”為識字與否的底線是很合適的。
漢字有其悠久的歷史,自甲骨文至今,雖然一脈相承,但每個字都變化多端,其復雜程度超乎想象。以所有漢字為對象,大概自詡“目能識丁”的人就不多了。人生糊涂識字始,把識字當專業,糊涂愈甚,真變成“目不識丁”了。
“丁”因為是個干支用字,自古及今都極常用,甲骨文因為是在龜甲獸骨上刀刻,就刻成一個方框,商代和西周的金文都寫成一個黑色的團塊,有人認為像釘子釘入器物后留在外面的釘頭。丁字又寫作 (古璽文),確實像個釘子形,現在的“丁”字就是這種形體變化來的。這個字在古文字中確實是再簡單不過了。因為簡單,就敢掉以輕心嗎?
清華簡中有一個字寫作下面的樣子:
類似的寫法在戰國古璽中出現過,因為與“丁”字形體相近,用作人名也無詞例可尋,過去釋為“丁”大家也沒有什么異議。清華簡中這個字多次出現,而且作為偏旁參與構字。在討論過程中,我根據一些理由提出是個“丁”字,李學勤先生認同了這個說法,寫了《關于清華簡中的“丁”字》專文討論。材料公布以后,學者紛紛討論,根據其詞例、韻例、書寫筆順等等多方證據,證明它不是“丁”字,是一個倒寫的“山”,倒寫的山是什么字?郭永秉說是顛覆之“覆”的本字。清華簡《芮良夫毖》說“譬之若重載以行崝險,莫之扶導,其猶不顛 (覆)?”用現代話說大意就是:譬如車子載重物行走在險峻的山路,沒有扶持引導,豈能不顛覆?文通字順,好極了!釋字不能看著像什么就是什么,必須讀通文例才算數。
下一個問題是倒山怎么就是“覆”呢?
顛覆就是翻轉,人倒過來是顛,學術界早有定論;山倒過來是覆,這是最近的發現。早期漢字常常利用文字上下方向的正與倒來表意。上文所說的車子顛覆也正是指車子的翻轉。我最近寫了一篇關于倒寫構形的長文,糾正自己的錯誤,申論這種構形方式的規律。
“覆”字上面所從的偏旁不是“西”,《說文》中這個部首,寫作“襾”,許慎解釋其義為“覆也”,分析字形完全不知所云,這里就不引了。這個字形來源自來沒有人弄明白過。郭永秉說,這個“襾”就是倒山的變形。靠譜!這是目前最好的解釋。這些怪字對大部分讀者來說都沒有什么興趣,但對于讀過《說文》的人來說,弄清楚一個部首的來歷,何其爽哉!
上面是我把不是丁的字當成了丁,下面有的學者把偏旁丁不當做丁。
“丁”作為偏旁參與構字,“訂”“盯”“頂”等字中的“丁”我們不僅認識,而且知道它們是表音的。回到古文字,偏旁中的“丁”又常被誤認。舉一個“旦”字來說。
許慎說“旦”是太陽出現在地平線上,只看小篆和隸楷文字,說得太好了。但一看小篆以前的古文字,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這些“旦”的“日”下不是像大地的一橫,而是一個黑疙瘩。這個黑疙瘩弄得許多人遐思飛飛:
吾聞之海人云,日之初出,為海氣所吞吐,如火如花,承日之下,摩蕩既久,日似決然舍去者,乃去海已高。余居土國,日出亦近似所言,但土氣不如水氣之大耳。金刻旦有物承日下,正是氣形,小篆變之,不見體物之精。——王筠《說文釋例》
多么富有想象與情思!
但在漢字系統中,自古及今從來沒有用一個黑疙瘩表達云氣的先例。或許問題并沒有那么復雜,于省吾先生說這個黑疙瘩就是“丁”,在“旦”字中表音而已。許多人不相信,我很以為然。知道了旦從丁聲,我們還弄清楚了戰國時期庖丁與屠牛坦之間的關系。
《庖丁解牛》我們很熟悉。庖丁解牛,神乎其技。類似的故事又見于《管子·制分》:“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發,則刃游于其間也”
最早把二者聯系起來的是陸德明,他在《莊子音義》“庖丁”條下注云:
庖人,丁,其名也。《管子》有屠牛坦,一朝解九牛,刀可剃毛。
庖丁就是屠牛坦,這從文字學上也得到證明。坦從旦聲,旦從丁聲,古代丁和坦讀音很近,可以通假。千萬別以今天人名用字的觀念理解古人,古書中人名用假借字的例子多如牛毛。《莊子》與《管子》,是同一個故事的不同傳本。
一個剛認字就應該認識的“丁”字就惹出這么多麻煩來,成千上萬的漢字都比這個難,如此一個個說下去,豈不煩之又煩?其實也沒那么可怕!例如不論“清醒”還是“糊涂”,四個字都不至讓人太糊涂,一邊表示意義,一邊表示讀音,絕大多數漢字都是這么構成的形聲字。貌似簡單的漢字往往來源更加古老,問題更多。即使最簡單的“一”,變體也很多,有些曾令人困惑多年。漢字的水太深,處處得小心。學者必須有一個好心態)——隨時糾正自己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