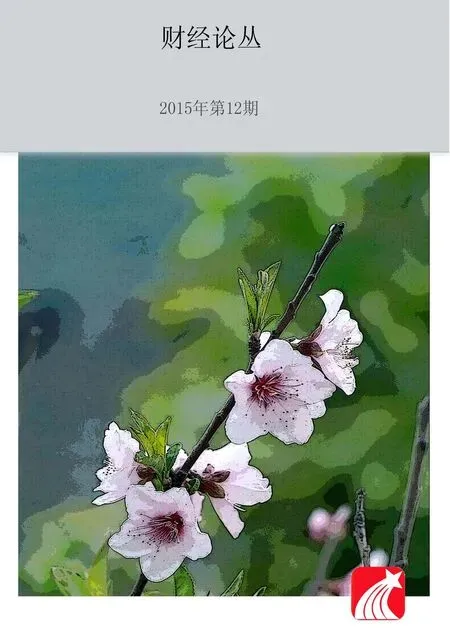食品安全事件的溢出效應與消費替代行為研究——以乳制品系列安全事件為例
靳 明,楊 波,趙 敏,章鑫鑫
(1.浙江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2.浙江財經大學會計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研究背景
被稱為史上最嚴的新《食品安全法》于2015年10月1日起正式實施。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將實施最嚴格的全過程監督管理,從法制層面上切實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近年來,國內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頻發、群發,令社會公眾對食品安全環境充滿不信任態度。其中,對消費者和產業沖擊力最強、影響最為深遠、最具代表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莫過于2008年9月爆發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這次事件不僅對乳制品行業甚至整個食品行業有著不可估量的負面效應,使消費者對國內食品安全問題空前敏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食品安全立法工作的完善。雖然“三聚氰胺”事件已經過去了好幾年,但它在人們的記憶中仍然印象深刻。以“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為標志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頻發嚴重沖擊著消費者的食品消費信心、消費行為,甚至改變了社會消費觀念和生活方式。面對頻發的食品危機事件,消費者隨之應變而產生消費替代行為,即尋找替代品和替代方式來滿足食品消費需求,開始拋棄國產奶粉搶購國外乳制品或尋找其他替代品,進一步對整個乳制品產業鏈及其相關食品行業、政策法規產生溢出效應。
在此背景下,學者們展開了對食品安全事件的研究。大多數學者都是研究某一食品安全事件對市場供求關系和消費者行為的短期影響,而很少涉及食品安全事件帶來的長期影響及其對相關領域的溢出效應分析。本文以頻發的乳制品安全事件為例,研究食品安全事件的長期影響及其對消費者行為、乳制品行業、其他食品行業與相關政策等產生的溢出效應,為分析和緩解危機影響及其相應的監管措施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議。
二、理論研究基礎
(一)消費替代
替代有多種形式,本文僅研究消費替代,即替代性消費行為或消費者選擇替代品的行為。在食品安全事件的嚴重影響下,消費者食品消費行為的轉變不僅局限于品牌轉換,還通過尋找替代品的方式來滿足食品消費需求,我們把這種替代性消費行為定義為消費替代。消費替代是本文新界定的概念,借用邁克爾·波特(1985)在著名的產業競爭“五力模型”中的替代品概念[1],消費替代是指功能或用途基本相同的不同種類的產品,在滿足消費者需求時可相互替代的消費行為。如果替代品在價格或性能上更具有吸引力,消費者會改變購買習慣而去購買替代品,從而產生消費替代行為。波特認為替代是一種過程,通過此過程一種產品或服務取代另一種為買方實現一定的需求,替代分析對產品和過程同樣適用。這里替代的對象通常就是指品類(品類替代),即波特所指的替代品對原來消費產品的替代。例如,在“三聚氰胺”等毒奶粉事件頻發的溢出效應影響下,消費者用進口奶粉來替代國產奶粉。如果再把品類替代向兩端延伸,底層則是品牌轉換,向上是相對無形化的消費方式轉變。因此,根據現有少量研究文獻及其文本分析和探索性調查,本文界定消費替代廣義上包括品牌轉換與品類替代及相應的消費方式替代(如購買渠道遷徙等,Thomos&Sullivan(2005)、賈雷等(2012)對線上線下渠道遷徙等類似替代行為進行的研究)等三個方面,狹義上僅指品類替代[2][3]。品牌轉換已有較多相關研究,而消費替代是一個相對新的概念,現有研究甚少涉及,一般是一種長期性的趨勢性轉換,常常發生在產業層面的變化。本文主要研究消費替代中的品類替代及相應的消費方式替代。
(二)溢出效應
溢出效應(Spill-over)是一種外部性影響現象,當個體(組織)發生某件事后,不僅影響該個體(組織)本身,還影響到個體之外的其他個體(組織)的現象。產品傷害危機對其他對象的溢出效應研究是在已有的品牌間溢出理論的基礎上展開的,認為其實質就是產品傷害危機由對個別品牌的影響連帶涉及到對其他品牌和品類總體的影響。溢出效應會在多個層面上發生,如同一產品中的一個屬性對另一個屬性的溢出、同一品牌的不同產品之間的溢出效應、品牌組合中的一個(類)品牌對另一個(類)品牌的溢出、競爭者之間的溢出效應等。產品傷害危機溢出效應的大小取決于品牌網絡的主要特征、品牌間的相似程度和聯系強度[4][5][6]。Roehm&Tybout(2006)研究發現危機品牌是否會對市場上的整個產品大類產生溢出效應,要視危機品牌在整個產品大類中的代表性及危機產品的屬性是否與整個產品大類有較強的聯系而定,在代表性品牌出現傷害危機的情境中,消費者對整體行業會產生負面感知,從而形成危機在行業內的溢出[7]。另外,危機事件的群發比單發更易影響消費者對該行業其他品牌乃至整個行業的態度評價[8][9]。也有少數學者從利益相關者角度分析溢出效應,特別是對產業鏈的溢出效應。趙宇虹和魏秀芬(2013)提出由于食品傷害危機的發生,乳制品進口持續上升而對我國奶牛養殖業的發展形成壓力[10]。任立肖和張亮(2014)將食品安全事件的利益相關者分為三大類,即核心利益相關者(食品生產經營者、消費者、政府部門和網絡輿情原創者)、邊緣利益相關者(檢驗機構、非政府組織、網絡輿情轉發者和評論者)和潛在利益相關者[11]。
對溢出效應影響機理的解釋主要有激活擴散理論(Spreading Activation Theory)和可接近-診斷理論(Aecessibility-Diagnostieity)。激活擴散理論認為人的記憶是由知識構成的,知識由節點及節點之間的連線構成的網絡表示[12]。同樣地,產品屬性及產品所屬的品類都存在于一個網絡中,當兩者之間的連結較強時,可由一個激活另外一個。當一個品牌發生傷害危機時,有可能從品牌節點激活品類節點,而是否發生這類激活,則取決于品牌和品類之間的連結強度。根據可接近-診斷理論,品牌和品類之間的連結強度取決于信息的可接近性和可診斷性。可接近性是指信息的可獲得性,即消費者是否容易聯想起相關信息。可診斷性是指該信息用于認知判斷的有效性程度。產品傷害危機是否會對整個品類發生溢出效應,這主要是指消費者是否容易獲得、是否容易聯想起相關產品傷害危機信息,并對進一步的決策判斷提供依據。國內頻發的食品安全事件(如“三聚氰胺”等事件的累積刺激)極易向相關品牌和品類發生溢出效應,使消費者由個別品牌聯想到品類,從而發生消費替代行為。
綜上所述,食品安全事件具有明顯的溢出效應,易引發相應的消費替代行為,并對企業品牌、競爭者乃至整個行業品類引發溢出效應,甚至還會波及社會消費方式、相關產業及政策制度等[13][14]。食品危機事件溢出效應的一般激活擴散路線為食品安全事件-消費者-行業-政策法規,本文擬從消費者、行業和政府等三方面來探索乳制品安全事件的溢出效應。
三、食品安全事件的消費者溢出效應——消費替代行為調查分析
2012年初,在“三聚氰胺”事件及其后系列乳制品安全事件(如“多美滋”、“皮革奶”、“金橋”與“熊貓”乳業事件及“三聚氰胺”奶粉重現事件等)基本告一段落后,乳制品產業經過危機爆發下跌、低迷后逐步復蘇,為深入研究危機事件產生的溢出效應與消費替代行為,本課題組進行了消費者問卷調查,選擇浙江省11個地市中具有代表性的城鄉,由企業管理專業研究生現場問卷調查,共回收512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為488份,有效率為95.3%。數據處理采用SSPS17.0統計軟件。在調查樣本中,男女各占50%,年齡段主要為25-59歲(占84.2%),文化程度大專以上53.0%,大專以下47.0%;家庭年收入3-10萬元占50.0%,10萬元以上占38.5%,3萬元以下占11.5%;已婚且有6歲以下子女的家庭占18%,已婚且有7-18歲子女的占20.9%,已婚且有18歲以上未獨立子女的占37.3%,無子女共同生活的家庭占14.4%,單身的占9.4%;居住在城市的占65.0%,鄉鎮的占35.0%。樣本在乳制品消費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下文簡要分析品類替代與消費方式替代(購買渠道遷徙單獨分析)等兩類消費替代行為的消費者調查結果。
(一)品類替代
在國產奶粉替代品的選擇調查中,我們可以發現乳制品系列安全事件后,僅有6.8%的消費者購買行為不變,不選擇任何替代品;而三成用豆奶粉替代奶粉,三成選擇用進口奶粉作為替代品;另有部分用鮮奶替代奶粉。

表1 國產奶粉替代品選擇和境外對中國消費者的奶粉限購政策
由表1可見,進口奶粉對國產奶粉表現了較強的替代作用。據2011年中央電視臺《每周質量報告》,70%的國內消費者仍不敢購買國產奶。2009-2012年乳制品進口額強勁上升,乳制品進口額2010年較2009年漲幅高達90%,2011、2012年漲幅分別為33%和22%。雖然進口乳制品價格節節攀升,但由于對國產乳制品安全擔憂,消費者仍熱衷于通過各種渠道購買國外乳制品作為替代品。據AC尼爾森報告顯示,2012年中國嬰幼兒奶粉銷售額為385億元,僅多美滋、惠氏、雅培和美贊臣等四大洋品牌就占據了42.7%的市場份額,尤其是一二線城市的市場占有率高達80%。國內消費者在國外大量搶購洋奶粉甚至引起了國際奶粉市場的動蕩,不少國家和地區針對中國大陸消費者紛紛實施奶粉限購政策。
(二)購買渠道遷徙
在購買渠道選擇上,傳統食品購買主渠道——農貿市場地位旁落,消費者開始在更有質量安全保障的超市購買,這一傾向在乳制品、食用油、糧食及制品體現得尤為明顯。從2012年初調查后的幾年來看,城市中水果、蔬菜的購買場所向大小超市遷徙的進程大大加快。

表2 消費者食品購買場所單位:%
(三)消費方式轉變
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消費者與消費資料相結合的方式即為消費方式,包括消費者以何種身份、何種形式、何種方法消費消費資料,以滿足其需要。消費方式是生活方式的重要內容,也即狹義的生活方式。消費方式具有剛性和慣性,在一段時期內,消費者一般會維持原有的消費方式不變。然而,由于頻發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不斷刺激,現實生活中各種替代消費方式開始興起,最明顯的是消費者購買渠道遷徙、食品種養加方式的自助化、消費關注因素的變化等。當然,這些消費方式的改變不僅僅是食品安全事件的影響結果,還與社會經濟發展和環境變遷等影響有關。但不可否認的是,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頻現催生和誘發了這些消費方式,如食品加工方式興起自助化,“三聚氰胺催熱了豆漿機”、“塑化劑事件催熟了榨汁機產業”等就是很好的現實寫照。

表3 乳制品安全事件后消費者購買食品時關注因素與關注程度的變化 單位:%
在調查中發現,乳制品系列安全事件后,消費者購買食品時關注因素與關注程度有了不小改變。在選擇商品時,消費者從以往單純的品牌價格主線購買轉為更為復雜的購買過程,消費者開始更加關注食品的產地、營養成分表、標簽、添加劑等信息,除通常高度關注的保質期外,對添加劑的關注度從44.8%大幅提高到80.5%,因為“三聚氰胺”等事件就是由于濫用添加劑或非法添加劑惹的禍。
四、食品安全事件的產業溢出效應
“九五”至“十一五”期間我國乳制品行業發展較快,乳制品生產量每年以10%的速度快速增長。然而,2008年9月我國乳制品行業爆發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給國內乳制品企業和消費者造成了巨大的打擊。2008年10月,我國乳制品月產量為120.1萬噸,同比下降28%。在該事件影響還未完全消除時,接著又相繼爆發了“多美滋”、“皮革奶”、“金橋”與“熊貓”乳業事件及“三聚氰胺”奶粉重現事件,無疑使乳制品行業雪上加霜,導致一段時期內乳制品消費疲軟,國內乳制品消費量在2008-2010年一直都處于低迷狀態中。與此同時,消費者開始紛紛搶購進口奶粉,海外代購逐漸成為一種趨勢。
(一)食品安全事件對乳制品行業的溢出效應
在乳制品系列安全事件影響下,國內乳制品品牌信譽普遍受到質疑。對未公開報道而存在質量問題的乳制品品牌,本課題組的調查顯示六成多的消費者選擇不信任,這說明乳制品安全事件影響溢出到整個行業。
1.奶牛養殖模式轉變。在乳制品事件前,乳制品產業一直存在著一個嚴峻的問題,即忽視原料奶的生產環節。大部分原料奶依靠成千上萬的奶農分散飼養與供應,奶農和乳企之間存在一定的博弈關系。受“三聚氰胺”事件和國際金融危機的雙重影響,國內原料奶價格持續走低,嚴重損害了奶農利益,部分地區甚至出現了殺牛、倒奶現象,導致大量奶農紛紛退出奶牛養殖業。這一形勢倒逼我國奶牛養殖模式轉變,逐漸呈現規模化、集約化和標準化的趨勢,小規模奶戶逐步向規模化牧場過度,部分規模化的牧場買入優質奶牛,增加奶業存欄量,一些地方乳企兼并重組進行規模化經營。2010年11月,蒙牛與君樂寶達成戰略合作協議,投資4.692億元持有君樂寶乳業51%股權。2013年,蒙牛又出資35億元計劃3年內建成自有牧場,飼養可控奶牛30萬頭。完達山入股貝蘭德乳業,持股達51%以上,隨后完達山乳業在天津等15個省市建立核心奶區,建設萬頭天然牧場,形成五大核心奶業基地。伊利兩次融資擴股,花費近20億元人民幣與奶聯社合作來擴大自由奶源。
2.乳制品工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我國乳制品工業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歷經了不到20年的飛速發展,完成了發達國家乳業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發展進程,但超常發展也引發了一系列食品安全問題,亟需進行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2014年,隨著兼并重組工業方案落實,國內乳品企業開始陸續整合,行業集中度明顯提升。2013年,全國嬰幼兒配方乳粉生產企業共有128家,年產量約60萬噸,但僅有3家年產量在3萬噸以上。其中,排名前十的國產品牌企業銷售額共約180億元,市場集中度約為45%。自2013年11月以來,各大乳品龍頭企業開始布局,一個月之內就發生了五起并購。例如,11月15日,蒙牛乳業宣布認購原生態牧業3.657億股份;11月19日,西部牧業宣布與伊利股份合資建設千頭牛場。工信部在《推動嬰幼兒配方乳粉行業企業兼并重組工作方案》規劃中提出,到2015年底,培育10家年銷售收入超過20億元的大型企業,前10家國內品牌集中度達到65%;到2018年底形成3-5家銷售額超過50億元的企業,最終配方奶粉企業整合到 50 家左右[15]。
乳品企業不僅進行行業內部的兼并重組,而且對奶粉全產業鏈也開始了整合。一是收購具有優質牧場資源的企業,如圣元與法國索迪亞集團達成合作建廠協議,一期投資9000萬歐元在法國布列塔尼半島建設一座設計年產能達10萬噸的全新現代化嬰兒奶粉工廠,為產品提供歐洲標準的優質奶源。二是兼并具有優質產品銷售渠道的企業,如圣元在上海宣布公司已與育嬰博士簽訂協議并將對其進行并購重組。
我國乳制品產業升級主要表現在打造中高端品牌的奶粉,積極進軍國際市場。2013年一系列國外品牌奶粉事件的發生導致其品牌的“光環效應”逐漸褪去,國內乳制品企業抓住機遇,立足產品質量,以培育高端品牌為目標,逐步加快了向中高端品類前進的步伐。從2013年9月開始,蒙牛、伊利、雅士利、完達山和飛鶴等眾多國內知名奶粉企業通過媒體廣告向消費者展示其高端品牌的嬰幼兒配方奶粉新產品。
3.奶粉銷售模式改變。國內奶粉銷售主要有超市、母嬰店和網絡等三類渠道,2012年嬰幼兒奶粉的銷售渠道占比分別為零售渠道45%、母嬰專賣店渠道42%和電商渠道13%。而歐美等國的奶粉主要在藥店銷售,從國外經驗來看,藥店系統是管理最嚴、質量與安全最有保障的銷售渠道。2013年6月,國家食品藥品監管總局等九部門聯合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嬰幼兒配方乳粉質量安全工作的意見》,決定試行嬰幼兒配方奶粉藥店專柜銷售。2013年10月16日,商務部確定首批選定10家奶粉品牌于10月底開始試行奶粉藥店銷售,計劃用兩年半的時間實現藥店的奶粉銷售額市場占有率達到20%。然而,從實施情況來看,相比于超市、母嬰專賣店和網絡銷售渠道,被譽為奶粉銷售“第四渠道”的藥店在奶粉質量和價格兩方面并無明顯優勢。雖然政府力推,但藥店短期內很難成為奶粉銷售的主流渠道。
此外,“海淘”奶粉逐漸成為一種趨勢。支付寶發布的2012“海淘”用戶消費數據顯示,2012年境內消費者通過支付寶“海淘”消費的規模同比增長117%,而奶粉則成為“海淘”最火爆的商品,用戶近1/4的“海淘”消費是沖著奶粉而去的。在淘寶網上,搜索“奶粉”一詞,出售奶粉的信息多達60多萬條,銷售奶粉的店鋪多達6萬多家。
(二)食品安全事件對相關食品行業的溢出效應
頻發的乳制品安全事件不僅直接對乳制品行業造成沖擊,其溢出效應也波及其他食品行業,導致消費者對整個食品行業產生信任危機。本課題組的調查顯示,受“三聚氰胺”等事件影響,從消費者對不同食品品類安全性的總體評價來看,乳制品、肉制品、果汁、食用油和糧食等食品品類認為安全的消費者不到50%,只有水果、豆制品、蔬菜的安全性認可度超過60%,水產品和生鮮豬肉的安全性認可度超過50%。
食品安全事件已對食品消費行為方式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除前述的購買渠道遷徙、食品信息關注因素變化及加工方式自助化等外,消費者在種養加與流通方式上也紛紛展開了自助化運動,本地綠色生態食品直銷模式開始流行。以有機食品為例,發達國家生產者與消費者互動的、直銷形式的非主流渠道替代傳統渠道已成為主要的流通渠道之一。國外學者將提攜系統(Teikei)、社區支持農業(CSA)、箱式計劃(Box Scheme)、農夫市場(Farmers’Market)等非主流渠道形式統稱為替代食物網絡(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AFNs)。在國內,有機農夫市集和社區支持農業(CSA)是AFNs的主要形式,包括小毛驢模式、城鄉共建模式、NGO組織模式、代購模式等,這些模式具有的共同點是:農民和消費者都是農場的所有者,農民只需專注于種田,消費者則承擔配送、運輸、包裝及招幕會員等其他經營性的工作。這些新供給模式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周立認為:“當整個社會的公信力越來越低時,人們反而更愿意相信私人的、小眾之間的關系,他們不相信工業化的食品生產,而相信能與他們面對面交流的農民[16]。”
五、食品安全事件的政策溢出效應
面對頻發的乳制品安全事件及其乳制品“市場失靈”的狀況,政府“看得見的手”的規制顯得尤為重要。政府通過不斷出臺和完善針對乳制品行業的產業政策、法律法規和標準,從奶源、乳制品加工、乳制品消費和乳制品國際貿易等方面引導乳制品產業的規范發展。
1.奶源政策。國家對奶源的監管力度隨著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頻發而逐漸加大,有關奶源政策分別從奶牛養殖基地建設、奶牛養殖風險補貼、生鮮乳質量安全標準制定、奶粉質量監管、奶源供應等角度分別制定了詳細的規定、提出了針對性的指導意見,對全國奶牛的優勢區域進行劃分,選擇全國313個奶牛養殖基地進行重點建設,鼓勵企業自建自控養殖場,還特別強調了嬰幼兒奶粉的奶源控制。
2.乳制品加工政策。有關乳制品加工政策,從原料奶收購的財政扶持、乳制品生產質量安全體系構建、嬰幼兒奶粉生產管理體系建立、加工企業整改等角度加強乳制品加工過程中的質量安全管理,杜絕可能存在的安全隱患,有效解決乳品加工的質量安全問題。
3.乳制品消費政策。為促進公眾對國產乳制品的消費需求,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同時,加強公眾對乳制品營養的正確認知,貫徹實施“學生飲用奶計劃”,培育年輕一代的乳制品消費群,以不斷擴大我國乳制品市場的有效需求。同時,開始試行奶粉藥店銷售,規定網店賣奶粉必須有營業執照等政策[17]。
4.乳制品國際貿易政策。在一些進口奶粉檢測出現質量安全問題后,國家開始陸續實施進口奶粉新規及嚴控進口嬰幼兒配方乳粉的政策,以提高進口奶粉的門檻,使進口品牌奶粉整體質量進一步提升。例如,國家發改委進行的反壟斷調查(如對合生元、雀巢、惠氏、多美滋、美贊臣、雅培等國外乳粉企業的反壟斷調查);國家質檢總局對進出口乳品實施最嚴檢測,境外食品生產企業實施注冊制度等;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提高乳制品出口退稅率,關稅免征額度調低,提高郵購奶粉價格,對代購奶粉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六、主要結論建議
根據危機溢出效應的激活擴散線索,本文分析了系列乳制品安全事件對消費者、乳制品行業及相關食品行業和政策的影響,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1.食品安全事件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在頻發的食品安全事件刺激下,消費者不斷地改變其消費行為,發生品類替代、渠道遷徙和消費行為方式的替代。因此,哪怕是在消費習慣比較頑固的食品行業中,消費習慣也并非一成不變,一旦環境刺激足夠強烈,同時又有可供選擇的具有吸引力的替代品,消費者也會改變消費習慣轉而選擇消費替代品與替代方式。
2.食品安全事件對相關產業與政策的影響。食品安全事件的沖擊影響不僅局限在危機品牌和危機產品,而且對產業鏈及相關行業的溢出效應也不可忽視。危機企業出現產銷危機,其他乳制品企業也遭遇信任危機,這種溢出效應延伸到整個國內乳業與進出口貿易甚至影響到對其他食品行業的信任。在乳制品安全事件頻發的刺激下,乳制品行業的產業結構開始改變,奶牛養殖和原料奶加工方式的調整、企業發展方式的轉變、兼并重組和產業升級是必然趨勢;奶制品銷售模式開始轉變,奶粉出現在藥店銷售,進口乳制品對國內市場形成較大沖擊。同時,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也會及時啟動,通過完善產業政策法規和標準建設,加強安全監管,規范企業行為和產業發展,以引導乳制品市場的健康發展。這些方面的轉變是潛移默化的,也是在一系列乳制品事件及其他食品安全事件的影響下逐步形成和完善的,這也可以說是食品安全事件影響所產生的積極效果。
乳制品行業發展前景廣闊,在經歷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后正逐漸復蘇。然而,在奶源基地建設、養殖與加工水平提升、質量安全監管和國際市場拓展等方面仍面臨嚴峻的挑戰。乳制品行業要保持持續穩定的發展,還需企業、行業、政府和消費者付出巨大努力。
[1][美]邁克爾·波特著,陳麗芳譯.競爭戰略[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5.
[2] Thomas J.S.,Sullivan U.Y.Managing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with multichannel customers [J] .Journal of Marketing,2005,69(4):239-251.
[3]賈雷,周星,韋荷琳.消費者渠道遷移行為影響因素研究[J].現代市場營銷,2012,(2):18-25.
[4] Siomkos G.J.,Kurzbard G.The hidden crisis in product- harm crisis management[J]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1994,28(2):30-41.
[5]王曉玉,晁鋼令,吳紀元.產品傷害危機響應方式與消費者考慮集變動——跨產品類別的比較[J].中國工業經濟,2008,(7):36-46.
[6]余偉萍,莊愛玲.品牌負面曝光事件分類及溢出效應差異研究[J].商業研究,2013,(2):21-27.
[7] Roehm M.L.,Tybout A.M.When will a brand scandal spillover and how should competitors respond?[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2006,43(8):366-373.
[8]崔聰.群發性產品傷害事件對產品品類負面溢出效應研究[D].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9]汪興東,景奉杰,涂銘.單(群)發性產品傷害危機的行業溢出效應研究[J].中國科技論壇,2012,(11):58-64.
[10]趙宇虹,魏秀芬.我國乳制品進出口貿易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對外經貿,2013,(4):21-26.
[11]任立肖,張亮.我國食品安全網絡輿情的研究現狀及發展動向[J].食品研究與開發,2014,(18):166-169.
[12] Collins A.M.,Loftus E.F.A spreading-activation theory of semantic processing[J].Psychological review,1975,82(6):407 -410.
[13]靳明,張英.肯德基速生雞事件危機公關廣告與公眾態度變化——基于新浪微博的內容分析[J].財經論叢,2014,(8):70-77.
[14]靳明,楊波,趙敏.食品安全事件對我國乳制品產業的沖擊影響與恢復研究——以“三聚氰胺”等事件為例 [J].商業經濟與管理,2015,(12).
[15]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推動嬰幼兒配方乳粉行業企業兼并重組工作方案[Z].2013.
[16]陳倩兒.保衛餐桌的實驗還是中產的腔調[N].中國青年報,2012-11-7(09).
[17]張學勇等.上市公司產品質量事件的動因與后果[J].證券市場導報,2015,(4):4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