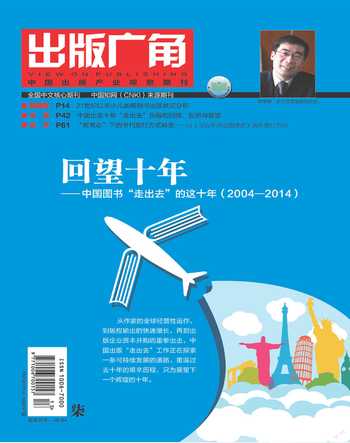論數字時代圖書產品新形態和編輯隊伍再造
沈小英
一、數字閱讀改變閱讀習慣
互聯網與IT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閱讀習慣。大眾閱讀方式開始從傳統紙質媒介向新興電子媒介轉移,電子書、手機書、在線閱讀等全新電子出版載體迅速崛起,出版業的格局急劇變化。
2010年,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發布《中國出版藍皮書:2009—2010中國出版業發展報告》,認為數字閱讀已成為伴隨互聯網長大的新一代讀者的閱讀習慣和生活方式,建設立體化數字出版大平臺將成為未來我國出版業發展的趨勢。此后,我國數字出版產業呈現爆發性增長。2009年的數字出版產業總收入近800億元,據《2013—2014中國數字出版產業年度報告》顯示,2013年我國數字出版全年收入規模達2540.35億元,比2012年增長31.25%,保持了快速增長勢頭。其中,在各類業務板塊中,電子書增長最快,從2006年到2013年,我國電子書收入年增長率為78.16%。
同傳統紙質書籍相比,電子圖書作為數字閱讀的典型方式,以特殊的格式制作而成,通過光盤等載體或有線、無線網絡傳播,在個人計算機、個人手持數字設備( PDA)、專門電子設備(電子書)上閱讀,有著鮮明的特點和獨到的優勢。電子圖書借助現代數字儲存技術和網絡技術,容量大、價格低、容易獲取,一張700MB的光盤即可容納1700多本20萬字的書,如果通過專門的閱讀網站、網上圖書館,更是可以獲取無限量的信息。一本同樣內容電子書的價格通常只有紙質書的十分之一、幾十分之一,甚至可以免費閱讀。一本數字化制作的圖書通常可以包含圖文聲像等各種資料,并含有大量的相關鏈接,讀者除了閱讀文本,還可以通過聲音、圖像、視頻獲取更多的信息,方便其進行檢索和擴展閱讀。依托互聯網和社交軟件,讀者還可以便捷地與他人互動、評價、分享。
圖書的電子出版逐漸改變了受眾的閱讀習慣。2014年,亞馬遜通過在線調查得出的《中國網民閱讀習慣報告》顯示,無論在哪個年齡段,嘗試閱讀電子書的比例都超過了70%;在20世紀70—90年代出生的人群中,30%只買實體書,40%以購買實體書為主。
二、紙質圖書閱讀方式仍受讀者偏愛
電子出版物會取代紙質圖書嗎?這一問題近年來持續籠罩出版界。2011年,愛丁堡國際書展有一個分會場,題目就是“書籍的終結”。在書展現場,蘇格蘭小說家埃萬·莫里森聲稱:“25年之內,數字革命就將帶來紙版書的末日。”
但是,出版物市場的數據卻并不如預測的那樣極端。據專業從事圖書市場調查的北京開卷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調查統計,2008—2013年,我國實體書店圖書零售市場的增長速度逐漸放緩,甚至出現負增長,但網上書店卻連續保持兩位數增長。兩者合并計算,整體圖書零售仍舊實現了年均接近10%的增長。同一時期,美國紙質圖書在受到電子書連年擠壓后,開始穩定在圖書總銷量的75%左右。
面對容易獲取、便于攜帶、價格低廉、方便閱讀的電子圖書,為什么仍然有讀者選擇紙質圖書?近年來,不斷有學者對電子閱讀和紙質閱讀各自的特點展開研究,總結了紙質圖書在閱讀、理解、感情、審美方面的若干特征。
其一,電子屏幕一次只顯示一頁信息,紙質圖書是前后翻頁,這對大腦理解作品——尤其是對于那些長而復雜的作品相當重要。讀者拿起一本曾經讀過的書,并不難找到特定的段落,尤其是學術著作,能隨時前后翻閱、對照并隨手批注、摘錄,這對閱讀者極為重要。
其二,有實驗表明,對于年輕閱讀者而言,通過紙質媒體閱讀說明文和記敘文,比在屏幕上閱讀更好理解。2013—2014年,美國美利堅大學教授內奧米·巴倫與其助手搜集了美國、德國、日本和斯洛伐克的300多名在校大學生的閱讀習慣信息,發現92%的受訪者認為閱讀紙質讀物時更容易集中精力,而在電子屏幕上閱讀時,他們有3倍的可能性同時做其他事情。如果紙質版和電子版的書價相同,75%—94%的學生(根據國家不同)更喜歡紙質書籍。大多數美國學生購買電子書僅僅是為了省錢,并不認為那是學習的最佳方式。
其三,紙質書籍因設計之美、裝幀之美、質感之美,以及反復閱讀而在其中凝聚感情寄托,滿足了閱讀者審美和感情的需求。
三、圖書產品新形態須實現數字閱讀與紙質閱讀融合
由于電子圖書和紙質圖書各自的特點和讀者對兩者不同的需求,使兩者在發展中逐漸借鑒、互補、融合。
在電子圖書的呈現形式上,通過硬件提升和軟件開發,一些電子書閱讀器采用電子墨水屏、彩色電子紙顯示技術,提高刷新和翻頁速度,努力向讀者提供接近紙質圖書的閱讀體驗,并致力于研發可折疊柔性電子紙、雙面顯示、多屏重疊閱讀等新技術,在電子閱讀中吸納紙質圖書方便前后翻閱、反復查找的功能。
在紙質書籍的出版方面,也有不少傳統出版社在內容電子化方面進行嘗試和開拓。目前,比較常見的做法是在紙質書中附帶光盤,或與專業的電子書運營商合作,通過互聯網推出電子書。少數以教科書、少兒讀物為主要出版物的出版社已經開始策劃、制作集紙質文本、電子文本及聲音、動畫等多媒體內容于一體的產品,并得到市場認可。但是,與電子和互聯網技術在電子閱讀領域的巨大潛力及對圖書出版業可能造成的巨大影響相比,紙質圖書與電子圖書在產品形態上的借鑒、互補、融合目前只是一個開端。
如今,無論出版社還是電子書運營商、閱讀網站,大多只是完成了圖書數字化的第一步,即將紙質圖書中的文字內容以電子文本的方式通過光盤或網絡提供給讀者。這對讀者來說,僅僅是在獲取信息的工具選擇上有所不同,而獲取的信息仍然與紙質圖書相同,這樣的電子出版物本質上與傳統紙質出版物并無差別,圖書產品的策劃、編輯、制作仍然是傳統紙質圖書的思維和流程。
有些出版機構則跳出傳統意義上“書”的形式,對文本按出版的特點,運用數據處理技術進行再生產,使讀者在閱讀方式上可進行鏈接式擴展,在內容獲取上可查找海量化信息。一些經過數字化加工的資料、文集、報刊等,可以通過作者、名詞、日期等多種方式檢索,并按讀者需要排列其中的內容,大大提高了出版物的“附加值”。例如,2013年起停止紙質出版并僅以電子版方式面世的《不列顛百科全書》具有更多的電子出版物特征。2010版《不列顛百科全書》定價1395美元,數字版訂閱費僅為每年70美元。電子版的百科全書內容實時更新,讀者在閱讀中可即時選擇、提取興趣的內容,并通過細分用戶群,針對不同年齡段學生、不同機構推出量身定做的在線數據庫。有人通過一部電子出版的百科全書查閱“小說”詞條的經歷進行描述,打開“小說”詞條,發現是一篇很長的文章,其中有很多粉紅關鍵詞,如“文藝復興”“薄伽丘”等,相當于傳統書籍中的注釋,但這樣的注釋并不是放在頁尾,而是點擊這些詞跳轉到另一篇相關文章。這樣的閱讀方式,完全打破了紙質圖書僅限于當前文本的局限,實現了閱讀者與閱讀對象的即時互動。
2012年12月20日《紐約時報》一篇關于雪崩的專題報道可作為另一類型數字化出版物的研究樣本。這個專題報道借助的媒介形態包括網絡、報紙、圖書,媒體類別包括文字、圖片、視頻。首先出現的是網絡上包括文字、圖片、視頻在內的6個故事及相關內容,其次是50個報紙整版圖文,最后以一本紙質書為壓軸。這樣一部由多形態呈現、多媒體組合完成的作品,打破了網絡、報紙、圖書的界限,網絡、報紙、圖書都成為整部作品的一種呈現方式。因制作者為一家傳統報紙,其一推出便成為紙質新聞媒體研究的對象。
四、產品新形態改變圖書編輯工作方式
這種基于海量數據庫、互聯網技術、便捷電子終端的數字化出版物,具有兩個有別于傳統紙質圖書的鮮明特征。
第一,在閱讀方面,傳統紙質圖書只能在作者和編輯所設定的范圍中,基本按照作品所提供的文本順序進行閱讀,其閱讀路徑呈線性。數字化出版物的讀者則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從作品的任何一個點跳躍到另一部作品進行擴展性閱讀,或者按照自己的需求,利用數據庫對信息進行查找、分類、歸納,其閱讀路徑呈樹狀或網狀。
第二,在作品呈現方面,傳統圖書只能提供平面的文字、圖表,并自其出版便已定型。數字化出版物則向讀者提供了“閱讀+視聽”的接受方式,往往是包括文字、圖表、聲音、影像、動畫等在內的多媒體組合,讀者可自行選擇“讀”“聽”“看”不同的方式接收作品的內容信息,作品的呈現形態須經過讀者的選擇才能定型。
數字出版的特點,使編輯在地位、工作流程、人員構成等方面都發生了變化,使其從傳統圖書的“加工者”向數字化產品的“制作者”轉變。
首先,從編輯在出版物生產中的地位考察,傳統圖書編輯在出版流程中居核心地位,負責圖書的策劃、選題、修改、規范,就作品而言,起決定作用的仍然是作者。當選題確定、作者稿件完成以后,編輯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加工性的,只能在作者提供文本的基礎上進行編輯加工,對文體所做的重大修改須得到作者的認可。讀者只能在作者文本的范圍內獲取信息,作品的基本形態主要由作者提供的文本決定。但在數字化出版中,作者所提供的文本往往只是最終作品的“腳本”,編輯要在“腳本”的基礎上,完成與數據庫的對接,要根據“腳本”設計相關的影像、動畫、聲音等多媒體內容,并組合到最終作品中。讀者從作品中獲取信息的范圍,遠遠大于作者所提供的文本,所看到作品形態也遠比作者的“腳本”豐富。
其次,從編輯在出版物生產中的工作流程考察,傳統圖書以作者的文本為中心,進行初審、二審、三審,并進行修改和校對、審校,前一項工作完成,方能進行下一項工作,整個流程呈順序性、直線型。數字化出版則以作者文本為出發點,在對作者文本按傳統圖書進行編輯加工的同時,須在文本基礎上進行相關技術合成和多媒體制作,其流程呈并進性、復合型。
再次,從編輯團隊的構成考察,傳統紙質圖書以責任編輯為核心,文字編輯、校對等承擔輔助性工作。而數字出版物的編輯必須為一支由多種專業人員組成的團隊,其中,既要有人負責圖像、聲音、影像等多媒體內容的制作,也要有人負責技術上的合成。傳統的責任編輯在數字化出版中,將成為最終作品的構思者、團隊的協調者。
最后,從編輯的專業素養考察,傳統紙質圖書編輯需要有與作者交流的親和力,對出版選題的判斷力,以及較好的文字功底,能對書稿進行刪改、規范。數字化出版中,編輯除以上素養外,還必須有組織、領導團隊的協調能力。在現有知識儲備上,要對相關的影像、聲音、動畫等多媒體制作有所了解,對與出版有關的計算機技術有所知曉,才能完成帶領團隊、設計產品、完成組合。
五、圖書產品新形態下的編輯隊伍轉型與再造
在紙質出版物時代,編輯無疑是構成出版機構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出版機構通過編輯才能形成自己的作者隊伍,通過編輯對書稿的加工,才能完成對圖書文字、版式、裝幀質量的掌控。在數字出版時代,編輯不但是作者的聯系人、選題的策劃者、文稿的編輯者,還是數字出版物的設計者、團隊的協調者、多媒體內容的合成者,更決定了出版機構核心競爭力的強弱。傳統出版機構開拓數字出版,編輯隊伍的轉型和再造是一項不可忽視的工作。
目前,我國數字出版產品生產基本處在內容提供商、技術提供商各自獨立的狀態。傳統的紙質圖書出版機構仍然按照紙質圖書的出版方式制造圖書產品,制作商將產品數字化或按照出版機構要求,制作一些多媒體內容。前者的編輯人員在本出版機構側重的專業學科領域有一定的專業素養并有較高的書稿處理能力,但對數字技術缺乏了解。技術提供商熟悉互聯網和數字技術,擅長開發各類電子書閱讀器和閱讀軟件,但對出版行業所知不多。這種狀況導致我國數字出版物內容資源不足、高質量產品不足、體現數字出版擴散性閱讀和多媒體特性的出版物不足。出版機構作為閱讀內容的提供者,應在數字出版中起主導作用,加快適應數字出版要求的編輯隊伍建設。
第一,以現任策劃編輯、責任編輯為主要對象,開展數字化出版基本知識培訓。策劃編輯、責任編輯是當前各圖書出版機構業務骨干,有豐富的紙質圖書策劃、編輯經驗,但大多接受的是文科教育,對基于計算機和網絡技術的數字出版技術、形態、功能不了解,針對這一群體開展培訓,可以比較迅速地將他們原有的資源與數字出版的要求結合起來。對責任骨干編輯培訓的主要內容有:一是數字出版概念、現狀、發展趨勢介紹,轉變圖書編輯以紙質出版物為圖書唯一形態的思維模式;二是介紹與數字出版有關的技術,如數據庫與圖書互動,各類電子書、閱讀軟件及其格式,各類可以與圖文形成組合的聲音、圖像、動畫等,使圖書編輯了解數字出版中有哪些技術可供使用;三是介紹目前數字出版各類案例,供圖書編輯參考借鑒。
第二,以數字出版為目標,引進專業技術人才。目前,各傳統紙質圖書出版機構的數字技術人員以設計和維護內部辦公與編輯軟件、網絡為主要工作,較少與圖書產品制作直接聯系。為適應數字出版的發展,需要引進一批掌握與數字出版物生產直接相關的專門技術人才,如數據庫設計與構建人員、多媒體制作人員等。
第三,從數字出版的長遠發展考慮,應從高校開始轉變僅從文科學生中培養編輯的教育模式,培養有創意策劃能力、文字編輯加工能力和數字化出版技術操作能力的文理復合型人才。
數百年來,以紙張和印刷術為基石的出版業從未有過根本性的變化。留聲機、電影、電視、錄音機,每一項發明問世,都有人預言圖書的歷史將要終結,但每一次都沒有成為現實。數字閱讀技術的出現,使人們獲取圖書的渠道、閱讀圖書的方式發生了不再依賴紙張和印刷的變化,閱讀的內容也由印刷時代的單一文本變為多文本、多媒體。但承載著知識和情感的閱讀,不會因技術的變化而消亡,相反,由于數字技術的介入,閱讀將變得更便捷、更豐富,服務于人們閱讀需求的出版業將隨之迎來一個全新時代。
只要出版業存在,作為溝通作者與讀者橋梁的編輯,就將繼續存在,只是時代對編輯提供了更大的施展舞臺,也對編輯的職業素養提出了新的要求。跟隨時代的發展,提升職業素養,編輯這一職業在數字出版時代將變得更加不可或缺。
(作者單位:法律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