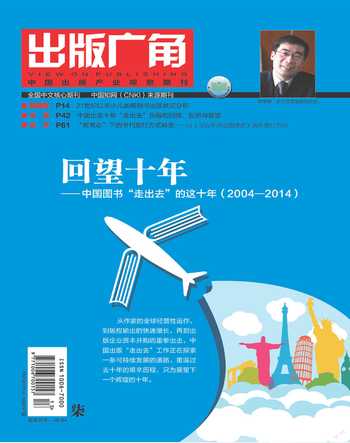那些綽號
仝冠軍
搜尋文人之間互起的別名、綽號,對讀者來說自是一種雅趣,但其中更能窺探到“賜名者”的創作功力、心理狀態,也更能體味到“受名者”的典型特征、個人性情,甚至能追溯至某些文壇公案,實能以小見大。有些綽號是人所共知、心領神會的,有些則隱藏在日記或書信之中,僅為個別人及小圈子所知。
魯迅給顧頡剛起的綽號(鳥頭先生、鼻、鼻公等)是人所共知的,其中的是是非非真個是剪不斷理還亂,一時恐難有定論。不過這綽號甚至用到了文學作品中,也算是文學史上少有的。在“故事新編”系列的《理水》篇中,魯迅塑造了“鳥頭先生”來影射顧頡剛——根據文字學將繁體字的“顧”字分解為“雇”(本義為“鳥”)與“頁”(本義為“頭”)。其中有這樣有趣的對話:“‘這這些些都是廢話,又一個學者吃吃地說,立刻把鼻尖漲得通紅,‘你們受了謠言的騙的,其實并沒有所謂禹,禹是一條蟲,蟲蟲會治水嗎?我看鯀也沒有的,‘鯀是一條魚,魚魚會治水水水的嗎?”把顧老先生口吃與酒糟鼻兩個特征都表現了出來,雖有些過分,但卻實在是幽默得很。在個人信件里,魯迅則以“鼻”“紅鼻”“鼻公”等代指顧頡剛。如1930年2月22日致章廷謙的信中,魯迅寫道:“至于鼻公,乃是必然的事,他不在廈門興風,便在北平作浪,天生一副小娘脾氣,磨了粉也不會改的。疑古亦此類,所以較可以情投意合。”
歷史學家鄧之誠愛在日記中給人起外號。如他于1955年1月20日寫道:“報載,李希凡評周聾《紅樓新證》,謂有瑜有瑕,改訂后,仍可行世。”周聾者,周汝昌也,周耳朵不靈,故被“賜”此號。1957年1月3日,鄧記錄道:“臭蟲請宿白代撰《從考古發現看漢代社會》一文……”臭蟲者,據考證指的是歷史學家翦伯贊。在其1957年9月18日的日記中,則有這樣的文字:“報載,齊木匠九日逝去,不葬八寶山,或嫌其遠,必以所刻玉印為殉,或恐人偽造真跡耶!若論其人,的確右派。”齊木匠,國畫大師齊白石是也。
魯迅的弟弟周作人也愛給人起綽號,不過卻是另一路風格。在周作人與俞平伯的往來通信中,各種綽號滿紙可見。如1931年9月10日,周作人致信俞平伯:“近因胡老博士之提議,經馬二主任之核準,國文系中新添新文學試作一項,令不佞計畫之……計擬定者為足下、詩哲、廢名、余上沅諸君……”其中的胡老博士,即胡適博士,周作人在其他信件中還稱呼胡適為博士、老博士。胡適年紀輕輕暴得大名,“博士”正是其最顯眼的標簽之一,加一“老”字,溫情頓起。此信中的“詩哲”,指的則是著名詩人徐志摩,因其曾陪同“詩圣”泰戈爾訪華,故得此名。不過這深具理性光芒的綽號與再別康橋的浪漫,卻有著不小的反差呢。1930年8月8日,周作人致信俞平伯說:“玄玄公何以無續訊,在船上恐又受茶房的優待,令人想起他的那篇文章也。”玄玄公,何其溫婉的稱呼啊,原來指的是寫了《背影》的作家朱自清。朱自清在1930年暑假期間乘船回南方,曾在船上作散文《南行通信(一)》,發表在周作人主編的《駱駝草》周刊上,署名玄玄,想來是因為他的字是“佩弦”吧。因此,周作人與學生俞平伯便用這一綽號戲稱朱先生,讀來讓人忍俊不禁、拍案稱絕。作家廢名,則被這師生二人稱為莫須有、莫須有先生等,一則因廢名創作了《莫須有先生傳》,二則廢名的字面意義與莫須有也相近吧。
而對疑古派學者錢玄同,周俞兩人所給的綽號更多,疑古先生、疑古君、疑古老爹、疑古翁、疑古公、疑古、老爹、某老爹等,指的都是錢玄同。如1927年7月1日,俞致信周說:“疑古先生昨來快談。”1928年7月31日,周致信俞說:“星期四苦雨齋夜談,我提議可以邀疑古公來,因為否則酒菜未免多余,而且缺少健談的人,亦稍稍冷靜也。”1930年9月18日,周致信俞:“六行書竟寫了五天,實在文思不屬,亦怪不得疑古老爹也,雖然十五日晚該老爹曾來敝齋談天。”不難看出,錢玄同由于其健談、風趣而深得這對師生的喜愛。周作人在其文章中專門寫道:“玄同善于談天,也喜歡談天……一直談上幾個鐘頭,不復知疲倦。其談話莊諧雜出,用自造新典故,說轉彎話,或開小玩笑,說者聽者皆不禁發笑,但生疏的人往往不能索解。”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周、俞二人不也正是這樣妙趣橫生的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