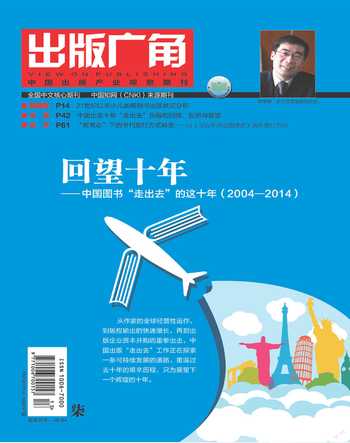慢慢成長,是種福氣
莊紅權
近期開始編輯天津大學張策先生的《機械工程簡史》一書,心里還是有些惴惴的,總感覺對不起張先生,之前做的《機械工程史》一書在工藝上選擇失當,愧對張先生努力收集并寫就的好書稿。
雖說《機械工程史》一書在工藝上的選擇也算無奈之舉,當時為了趕上張先生74歲生日,為了能讓張先生的學生們在這個特殊的日子里分享張先生的成果,我放棄了精裝,選擇了假精裝,但相比圖書內容,相比張先生的努力和付出,這個假精裝不倫不類,實在有失體面,以致我自己每次看到那本書都心有不安。真心希望首印的《機械工程史》一書能盡快賣完,重印時我一定重新裝幀,留足時間來印好這本書,以彌補對張先生的不安。也幸好張先生寬容大度,繼續將他的《機械工程簡史》交給我,而且還將和我合作《機械工程史》英文版的出版,讓我有機會去改正。
我認識張策先生是在2006年初的南昌,當時我作為金工領域的新編輯參加傅水根老師組織的金工課指組會議。會議期間,傅老師對張先生推崇備至。他多次跟我說張先生多么優秀,多么有風骨,多么有文采,多么喜歡幫助別人……因此,我對張先生印象深刻,但那次開會,其實和張先生接觸很少,他匆匆出席了半天會議就趕往其他地方了。之后我們也有很多次開會接觸,或者電話溝通,印象中的張先生謙和但不乏個性,儒雅但不失豪爽,高大但親和力強,風趣且底蘊十足,在我看來,他完全是機械基礎領域的偶像級人物。但我和他的溝通總是不夠深入,更沒有機會在出版上有所合作。
直至2014年8月份,當時我正在做清華大學申永勝老師的《機械原理教程》(第3版),經常和申老師討論圖書修改的事情。有一天,申老師對我和我的領導張秋玲老師說有件好事情,問我愿不愿意接,如果愿意接,他愿意幫忙搭橋。申老師的推薦,我們當然毫不猶豫地答應,申老師的認真和細致,我從大學上他的“機械原理”課就開始領教,之后一起開會、一起做書,感受至深,我相信他的推薦一定不會錯。但我原本以為他只是推薦一本普通的好書,沒想到,申老師推薦的居然是張策先生已籌備多年,正在統稿的《機械工程史》一書。
之后,經張先生同意,申老師將圖書簡介發給了我,簡介里張先生提到了他寫這本書的緣由,摘錄部分內容如下:
“我畢生從事機械工程的教學與研究,同時也對社會科學,特別是歷史和政治感興趣。
2006年,我從天津大學本部退休,到天津大學仁愛學院工作。我給學生開設的‘機械創新設計課程與所有其他學校都不同。我認為,歷史上所有機械發明都是創新設計,機械創新設計這門課最好是結合機械發明史來講述。所以,我課程的全名應該稱作‘機械發明簡史與機械創新設計。我講了三輪,后來把講稿給了青年教師去講。當時便萌生了一個想法——寫一本與眾不同的教材。
2013年初春,國家開放大學邀請我去給他們的教師培訓班做講座,我選擇了機械工程簡史這個題目,并以此為契機,開始寫一本專著。從那時起,專著的撰寫和講座的準備同時并舉。2013年6月,我在開放大學做的兩個多小時的報告受到歡迎,校方當即邀請我做一次5—6學時的講課錄像。于是,專著的撰寫又和錄像的準備同時并舉。
迄今,《機械工程史》一書的大部分章節寫得已經有了一些眉目。這本書是給高等學校和職業學校的教師和學生寫的,當然也可以供研究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參考。
從緒論中可以看出這本書編寫的宗旨和思路。寫此書時,我特別注意要把機械工程的發展放到社會發展和整個科技進步的大背景下加以論述。這從本書的目錄和緒論中可以看得出來。這些章均已完成第三稿。文稿中還有一些‘毛刺——個別史實還需要進一步落實;圖、表、參考文獻還沒有規范化;個別內容也許還要根據整體框架在章節間騰挪。
多年來,學界同仁普遍認為,應對學生加強科技史方面的教育。我在本書緒論中的論述也是建立這門選修課的理由。這件事做起來的難度主要是沒有教材。如果有學校開設‘機械工程簡史這門選修課,我的這本書應該是一本可用的教材。反之,我也期望本書的出版能推動這門選修課的建立。”
看完這個說明,我知道張先生對這本書是有很深的思考和很充分積累的。當然,我個人也非常認可張先生對創新、科技史以及相關教育的論述。張先生在緒論中提到:“機械工程的發展史絕不是一堆發明資料的合訂本。在機械工程歷史的宏偉畫卷背后,還有一個更加宏偉的社會發展史畫卷……筆者在敘述機械科技發展時,力求講清并展現機械工程歷史畫卷每幅圖畫背后的社會發展背景、經濟生產背景和整個科技領域發展的背景。”
看完目錄和樣章,我欣喜若狂,這是我近幾年遇到很難得的原創圖書,觀點鮮明、體系完整、資料翔實、論述清晰、行文流暢……唯一稍有缺憾的是有些圖不是特別清楚。當然,史書的圖片收集確實非常困難。張先生基本利用所有出差的機會,到各個圖書館、博物館等地方收集圖片,但有些圖片還是只能從網絡上找,清晰度相對會差一些。圖書編輯過程中,我和張先生就圖片修改交換了多次意見,他又花了很多功夫來尋找和處理圖片,我這邊也盡量多找圖修圖,盡量完善圖片質量,但終歸還是有一些圖片不太令人滿意,也算缺憾之一。
之后,我和領導商量,并征求申老師意見,盡可能提供最好的條件,希望能和張先生合作,一起來出版這本書,并后續一起開發《機械工程簡史》(學生用書)和《機械工程史》英文版(國內外出版發行)。張先生對我們的想法表示認可,但對報酬卻并不在意,只希望能一起把書做好,日后也希望有機會一起推廣,讓更多人看到這些書,并能從中獲益。
此事確定之后,張先生開始全力加速整理書稿,我們隨時通過電話和郵件交換書稿修改意見。張先生非常認真細致,令我記憶猶新的是,光參考文獻的格式和寫作規范,我們就通過了好幾輪郵件和電話討論。其間,我也專程去了一趟天津和張先生討論書稿,反饋中肯意見。記得當天,張先生穿了一件筆挺的大衣,戴了一頂禮帽,從家里騎車到天津大學機械大樓見我,他文質彬彬、氣質非凡。聊完書稿,他還請我和同事在學校吃了一頓狗不理包子,席間繼續聊書的后續計劃和推廣的事,聊得興起,還一起喝了瓶啤酒。那天和我一起去天津的是一位剛入職的女同事,她評價張先生說,這真是一位帥氣、謙和、博學、有風度的老先生。她問我工作中會經常遇到這樣的作者嗎?我說,你會遇到的,且作者各有各的優點,但這么優秀的也不算多,也算是編輯的福分。
那天我才知道,張先生為了趕書稿,生了一場大病,為此還專門做了一次心臟支架手術,而那天上午正好是他手術后復查的日子。之后,申老師多次跟我表示對張先生的歉疚,他說如果不是他拉張先生這么快敲定出版的事情,張先生可能不用做心臟手術。申老師一直覺得張先生這次心臟出事,是為這本書的忙碌而引起的。我覺得可能也確實有這方面的原因,張先生的認真,他對完美的追求,他的守信守時,無形中給了他很大的壓力,讓他放棄了很多休息時間,不斷修改,不斷完善。這也給我自己提了個醒,對于特別認真的作者,我還是需要提醒他們不要太拼命,畢竟身體最重要。
經過幾次通讀修改后,張先生于2014年12月初,嚴格按合同時間將書稿發給了我。書稿的質量非常棒,對我來說,編輯加工的過程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讓我有機會精讀一本好書,讀到精彩之處,我還會拍照記錄,并發在朋友圈與朋友分享。
但一本史書,終會有一些遺漏和問題,編輯加工和復審、終審過程中發現的一些小問題,張先生都非常重視,有疑問必細致求證后再答復我。書稿確定后,我找人設計了幾種版式,和張先生協商確認了現在的版式,當時我們考慮最多的是閱讀舒適度,所以排得相對較松,設計上也多了一些變化,以避免閱讀疲勞。封面也經過了多次設計,最終經張先生確認留下了現在的版本,相對樸素、嚴謹又有一些機械的元素。
無論是作者,還是編輯,我們都做了很多工作,希望能做出一本好書,但遺憾總是大于成就,這些遺憾讓我歉疚,也勉勵我更努力地去做好后面的書。作為一個學科編輯,能有機會在圖書編輯出版過程中向老先生學習,慢慢成長,是種福氣。以此為記,我知道成為張先生這樣的人對我已毫無希望,但還是希望自己能從張先生身上學到更多東西,慢慢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