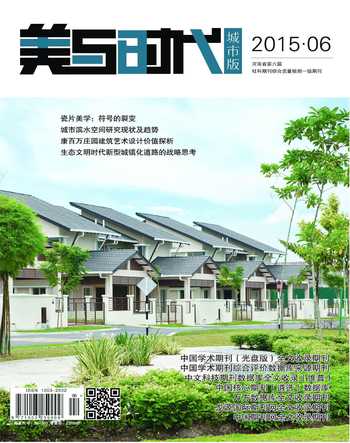南京六朝園林美學及其價值意義
摘 要:南京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城市,其六朝園林是中國園林史上重要的一筆,這些可貴的園林美學精神對城市建設有著積極的意義。南京的六朝園林大致可以按私家園林、皇家園林和寺廟園林來區分,不同類型的園林承載了不同的文化精神和美學內涵,研究六朝園林的美學精神,對提高南京城市形象、促進旅游業的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問題都有著重要意義。
關鍵詞:六朝園林;園林美學;城市建設
隨著城市發展帶來的諸多問題,我們已經認識到城市的發展不是簡單的經濟發展,城市的進步也不是簡單的技術進步,而是物質與精神的共同提高,才符合社會正常的發展規律,才能構建更適合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城市同樣有城市的精神命脈,即城市因不同的地理、歷史等因素而形成的特有的文化現象,我們把它稱作城市的文脈。“文脈”建設是一個城市文明程度、發展水平的精神意義上的體現。
南京是一個悠久的歷史文化名城。六朝古都,明初都城,民國總統府所在地,它在中國歷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六朝文化是南京地方文化的一大特色,南京的六朝園林在中國園林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主要遺跡有棲霞寺、玄武湖、雞鳴寺、北極閣等。目前,關于論述南京六朝園林的文章,大多是旅游開發等方面的價值研究,較少涉及到園林美學方面。
魏晉南北朝時期園林美學與當時思想發展息息相關,在中國傳統士人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造就了當時的園林美學發展承前啟后的特征。據歷史文獻資料和尚存的園林遺址,南京的六朝園林大致可以按私家園林、皇家園林和寺廟園林來區分,不同類型的園林承載了不同的文化精神和美學內涵。
一、貴族私家園林和皇家園林
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氏族興盛,促進了私家園林的興建,而士人階層對園林的審美取向直接影響了貴族經營私家園林營造的標準。南北朝特殊的政治格局,最終導致了社會上兩個極端的出現,一個是“士”階層的玩世不恭,一個是統治階級的貪婪奢侈。知識分子在肉體上追求放蕩不羈,精神上則追求麻痹解脫。他們將精神寄托于遠離世事塵囂的自然山川,大自然所滲透的悠遠的哲學意味和生命精神,正應了傳統美學思想中所追求的“天人合一”思想。對自然的眷顧受時空條件的限制,無論士大夫還是貴族王侯都熱衷于營造第二自然——園林,在園林中體味城市山林的隱逸趣味,于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私家造園開始興盛起來。這個時期的私家園林在文獻上有大量記載:“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云興霞蔚。”“(謝安)又于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侄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1]可見帶有文人士大夫階層審美趣味的私家園林此時應運而生,民間造園成風,名士愛園成癖。
皇親貴胄經營的私家園林在造園形式上迥異于階層所好的園林,但是在審美精神上卻受到了極大的影響。《洛陽伽藍記》記載北魏大官僚張倫的宅園:“齋宇光麗,服玩精奇,車馬出入,逾于邦君。園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復嶺,嵚崟相屬,深蹊洞壑,邐迤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懸葛垂蘿,能令風煙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野興之士,游以忘歸。”[2]
貴戚所經營的私家園林,在營造手段上不惜花重金,“齋宇光麗,服玩精奇”,使自然景象如真似幻,這是貴族對自然占有欲的放縱的表現,也更是為了滿足其奢侈的生活以及爭奇斗富的需要。我們可以從中看出其華麗的形式背后,如同士人一樣,因命運不測、政局跌宕將空虛的情感寄托于山山水水。
南方的貴戚經營的私家園林文獻中也有大量相似記載: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法亮、文度并勢傾天下……廣開宅宇,杉齋光麗,與延昌殿相埒。延昌殿,武帝中齋也。宅后為魚池釣臺,土山樓館,長廊將一里。竹林花藥之美,公家苑囿所不能及(《南史·卷七十七》)。[3]
廣陵城舊有高樓,湛之更加修整。南望鐘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一時之盛也(《宋書·卷七十一列傳》)。[4]
南齊的文惠太子開拓的私園玄圃是南京私家園林的代表之作,玄圃在造園形式上雖然與魏晉南北朝時期士人所好之園林有很大區別,但是在審美趣味上與士人階層卻有著一致性,都將自然作為審美主體。
玄圃在建成之時,為了遮蔽園內的奇珍異寶,建起了高高的屏障,足以讓人推想到當年園內的絢麗景象。玄圃現為南京玄武湖景區內的一部分,它已經不再專為個人服務,而是城市居民休閑游玩的好去處。
南京的皇家園林,在規模上都不太大,但是設計規劃得比較精致,內容也十分豪華。比較著名的是“華林園”和“樂游園”。華林園是大內御苑,包括雞籠山的大部分,始建于東吳,東晉時已經初具規模。《世說新語》記載簡文帝入華林園謂左右:“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密,便有濠濮間想也。”到劉宋時又大加擴建,殿堂林立,花木繁茂。樂游園在華林園的東面,北臨玄武湖,又叫北苑,始建于劉宋年間,自然條件十分優越,可以遠眺鐘山之景。此時的皇家園林尚未擺脫前朝園林的神秘色彩,依然具有求神拜仙的象征意味,但是同時也受到了世俗審美觀念的影響,比如劉宋時期華林園中建有模仿市井的店鋪街道。
二、寺觀園林
南京的寺觀園林展現的是漢化后的佛家美學思想,既突出了宗教情感,又兼顧了世俗審美需要。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至魏晉南北朝,深受社會條件的影響,同道教一起得到了極大發展。佛道兩家在發展的過程中既相互排斥又互相吸收借鑒,形成了一種錯綜復雜的格局,從認識論上講它們又是一致的,只不過因不同的教義而吸引著不同的信眾。佛道兩家思想的融合最終產生了玄學,寺觀園林在某種程度上即體現了玄學的美學精神。
我們可以從寺觀園林的造園形式和園林選址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寺觀園林與貴族經營的私家園林有密切的關系。寺本來是政治機構,最初被用來存放佛經,后變成佛教建筑專用名詞。寺觀建筑在中國呈現出完全不同于印度的,且更加符合中國傳統審美習慣的建筑形象。關于寺觀的來源,文獻上多有關于“舍宅為寺”的記載,也有僧道另行選址建造的。據史料記載,雞鳴寺前身即為官府宅第,后捐為寺廟。私家園林變成了佛教寺觀之后依然保存了原有的園林形式,同時寺觀園林也接受了私家園林所帶來的幽美閑逸、超然物外的美學精神。
寺觀園林的選址多為風景優美之地,這其中必然受到當時的美學思潮的影響。無論是城市內部的寺觀園林,還是郊外,鬧中取靜、風景幽美之地是寺觀建址的首選。僧道們對寺觀的選址不僅考慮到宗教活動的需要,其實他們更多地像知識階層的隱人雅士一樣,熱愛自然山水,僧人出世如同“高士”隱遁山林一樣,在審美意識上帶有幾分相似。《世說新語》記載:“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列于軒庭,清流激于堂宇。乃閑居研講,希心理味。”[1]
寺觀園林對選址的要求,在某種程度上與世俗的審美要求相契合,寺觀園林在成為自然山水點綴的同時,也成為了散發著時代美學精神的世俗審美對象。
三、南京六朝園林美學的現實意義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思想史上一個大放異彩的時期,各種文學藝術競相發展,美學思想方面也出現新的思潮新的概念。中國古典園林在這個時期得到重要的轉型。南京作為六朝古都,其園林文化在中國古典園林文化史上有重要的一筆,值得我們去研究。南京六朝園林美學意義主要有:
(一)南北朝時期南京的園林發展已經出現了私家園林,這不能不說是受了以自然美為核心的時代美學思想的影響,在造園方法和造園立意上都有了新的探索,給中國園林美學史添上了極具意義的一章。皇家園林不同于私家園林,表現出規模較大、造園手段依然保守的特征。適宜自然的隱逸美學思想在這個時期成為一種新的生活風尚,自然山川成為園林模仿的新題材,使中國傳統美學思想有了新氣息。這種氣息在后世更滲透到藝術生活的各個領域,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二)南京的寺觀園林,以私人府邸為基本樣式,發展出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園林建筑,使玄學的美學精神得到充分地發揮和體現。佛道結合形成新的美學精神,也即玄學的出現開了一代新風,影響了不僅一代的社會思潮。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晚唐詩人杜牧的一首《江南春》唱盡了六朝古都煙雨迷蒙的撩人春色,把我們帶入到南朝幽邃的城市意境中去,一縷縷一絲絲,情意綿長,回味無窮。這種對傳統園林描寫傳達出的審美精神,正是療治當前社會浮躁緊張情緒的一劑良藥。“南京在貫徹科學發展觀、實現城市現代化的過程中要發揚自己的歷史資源優勢,做大做強六朝文化”[6],六朝園林美學精神,是六朝文化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對其進行深入的挖掘發揮有著積極的意義。南京城市景觀設計師、決策人應從根本上理解六朝園林文化,并將六朝園林美學價值合理運用于城市建設作品中,將現有的六朝園林遺跡按科學的脈絡聯結起來,加強美學精神的表達。這對提高南京城市形象、促進旅游業的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問題都有著重要意義。
南京在中國幸福城市排行榜上連續多年入圍全國前十名,已經說明了一個問題,南京不僅是靠GDP贏得世人贊賞的城市,更是因其深厚的文化底蘊而吸引著世界的目光。
注釋:
[1]房玄齡等.晉書·謝安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4:2075.
[5][南朝宋]劉義慶著.沈海波譯.世說新語插圖本[M].北京:中華書局,2011.
[2][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校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唐]李延壽.南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5:1928-1929.
[4]陳文新主編.中國文學編年史 兩晉南北朝卷[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331.
[6]江可申,許麗君.論六朝文化資源的歷史價值與現實意義[J].南京航天航空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01):7-13.
作者簡介:
孫成東,南京交通職業技術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建筑環境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