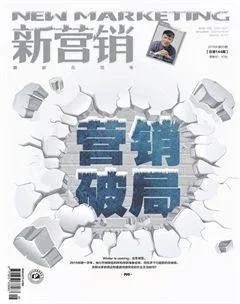只要有創意,垃圾也能變黃金
葉小果
怎么把一家沒人知道的茶館變得全城皆知?
我在1982年考入臺灣唯一的本科藝術學院戲劇系,學制五年,因為我們是第一屆,全學院只有81個學生,當時的校長鮑幼玉有一天問我有什么心愿?我誠實地說,我不想做導演,也不想做演員,他給了我一本書,中文名叫《藝術行政》,是從英國帶回來的。從那本書中我了解到了什么是管理,什么是營銷,當我把書還給校長時,說這就是我想學習的,我有興趣和信心, 校長很開心地說太好了。于是我就成為那個大學唯一的以藝術管理為專長的學生。一頭鉆進這個領域,校內教授這個方向的老師很有限,所以就跑到別的大學去旁聽,商業管理,企業管理,傳播、廣告的課程,因為營銷和這些很有關系。
在學習的過程中,也不是只有讀書,在1984年賴聲川成立表演工作坊時,我就以學生身份成為他的行政人員,后來因緣際會地在1987年大學畢業前親自做了落實藝術營銷的第一次嘗試,我讀過的一本小說《未央歌》中講述大學生們聚會的地方是茶館,于是我就開了一家茶館,把茶和餐復合式地結合了表演與視覺藝術,里頭有兩個舞臺,有展覽空間,免費開放給對藝術有興趣的表演者去表演,展覽,觀眾們可以一邊喝茶或用餐,一邊看表演,1987年1月11日茶館開業。
我后來總結,怎么把一家沒人知道的地方變成全城的人都知道?因為我默默無名,所以一定要去找有名的人。做商業廣告最簡單的就是找代言人,那么文化也有代言人,茶館開業20天后就是農歷新年的到來,那時很多店都關門了,大家哪里也去不了,而且新年的時候大家都對傳統的文化更有興趣,所以我就想何不找十五位離開舞臺很久的大師級人物,從大年初一到十五,把他們請回舞臺,好像回家團圓,做一次薪傳大師的聯合展演。
如果找人代言就得花大價錢,而這些爺爺奶奶級的人物都得過臺灣最高的藝術獎章——薪傳獎,有人是說相聲的,有人是表演評彈的,有人是說書的,有人是彈月琴的,每個人的專業都不一樣,我就找到十五位薪傳大師,他們看到一個20歲出頭的大學生感覺跟看到他們的孫子輩沒兩樣,當我講了自己的理想和理念之后,他們幾乎都不收費地來支持我,都愿意來做表演。
茶館只有150個座位,每天都是滿的,因為人們已經脫離那樣的感覺很久,薪傳大師要做15天聯演的消息一傳出去,各個報紙主動來報道。原來這個茶館包括我都是默默無聞的,如果請媒體來報道,肯定沒人來,可是從來沒有人把十五位薪傳大師聯結在一起做展演,十五天之后茶館出現在每家報紙的頭版,這里面就體現了營銷的“極端原則”,一般人們認為做生意的都是成年人,而我當時還是一個沒畢業的大學生,《遠見》雜志就以“大學生老板”為標題對我進行了報道。分析這個年輕人創業靠的不僅僅是資金和人脈,更是創意,從那時起創意營銷的名詞就跟我放在一起了。
在營銷上還有一個原則是“搭順風車”。比如正在流行什么,新聞有哪些熱點,那就搭順風車。我在茶館里做了兩個嘗試,4月1日是愚人節,我舉辦了臺灣的第一次說笑話比賽,不是說別人的笑話,而是說自己的笑話,大家都來聽,覺得很有趣。
第二個活動是,從三月到五月連續三個月的13號都是星期五。在西方的概念里,這是不吉利的。我就想到鬼故事。臺灣的那個年代沒有機會在公眾場合聽鬼故事,我就想把那個感覺拉回來,茶館總共有三層樓,從入口開始一直到店里頭,我就找美術系的同學,打造成「聊齋」。因為在臺灣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報紙和電視、廣播都來報道,等到正式開始說鬼故事的那一天,我找來了寫鬼故事很有名的作家來做評審。其中有一位叫司馬中原在臺灣非常知名,他也來了,結果一炮而紅。這個事情引發了后面的很多效應。因為有了說鬼故事的比賽,有聊齋餐廳,電視公司就來找我合作,讓現場觀眾在攝影棚里面體驗像聊齋一樣的鬼屋,聽聊齋那樣的鬼故事,而說故事的人就是司馬中原。他后來出版錄音帶就大賣,所以從一個創意點不斷向外延伸,變成很多相關的服務跟產品。有一個媒體來采訪我,寫了一篇很大的報道叫做《鬼不迷人人自迷》。那段時間是我覺得很有成就感。因為我是一個大學生,沒有什么負擔。父母、朋友跟老師們支持我,相對而言,我自己也不畫地自限。有一則營銷法則就是“典范轉移 - 不要畫地自限”。
在1987年1月茶館開業以后,四五月份從美國加州來的一個教授經過朋友介紹,到了茶館,看了演出,用餐喝茶以后,他就打聽老板是誰?當我走到他的面前,他詢問我畢業后想做什么?他說愿意給我全額獎學金。所以在1987年8月26日我就去美國加州大學讀研。然后茶館就交給了我的母親和股東去營運。一直到1989年,有一位很有名的詩人“管管”非常喜歡我的茶館,就找到我的母親把茶館轉讓給他的朋友了。
如何把剩余的票盡快賣光?
我在美國總共經過了3個學位的訓練。讀博士時主攻了文化營銷,這樣就確定了我的專業方向。1988年,美國加州的一個州立劇團要到亞洲來巡演,導師就推薦了我擔任助理團長和營銷總監,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跨國營銷的工作,從美國到日本、臺灣、香港,做了三個國家和地區的營銷工作。那年,我還未滿25歲。
演出的劇名叫《征服我兄弟》,講述白人和印第安人的種族矛盾。該劇在日本演出的時候,大家純粹是把它當做美國的白人文化和印第安文化的沖突問題,因為日本是單一民族,沒有太多的感覺。可是這個劇到了臺灣引發了很多的注意。因為臺灣本身有原住民,很像印第安文化,存在著高度的同理心,在那樣的狀況下我們把演出本身推動得非常有效益。
劇團在臺北演出時的挑戰是,如何在最后時間把沒有賣完的票盡快賣掉?在美國的百老匯,比如說今晚就要演出了,如果還有剩余的票就會半價或以很低的折扣賣掉,我做的方法不是這樣。出演的印第安人里頭有個人的爺爺是真正的酋長,我就請這群穿著酋長服裝的印第安朋友,全副武裝地在臺北最熱鬧的大街上散步,帶著鼓、鈴鐺等樂器,在很知名的商業街 - 忠孝東路上游行。在臺灣沒有人這么近距離地看過印第安人,所以就引發了轟動,有電視公司主動來邀約上節目,做訪問,更多的人就知道有一群印第安人來臺灣演出。
演出的當天是星期六,我和演員們走到中正紀念堂的廣場中央,演員們在那里敲鼓,人們聽到聲音就圍觀過來,酋長的孫子就演唱,女演員唱和聲。我告訴圍觀的人們這是在祈福,請大家手牽手一起跳舞。并且我說下午兩點半和晚上七點半在戲劇院里各有一場表演。大家一直跟著演員們跳,最終就跳到了售票口附近。我就感謝大家參加跳舞祈福儀式,表示我們還有一些余票,這次演出會更精彩。結果大家就開始排隊買票。
還有一個這樣的例子。1999年臺灣發生了921大地震,美國的一個表演團體的導演跟我聯絡,想到臺灣做一次巡回公演,把所有的收入捐給受災的孩子們。我們就開始準備, 演出先是在臺灣的西部地區和東北部地區進行,在臺北的演出前夕,還有不少票沒有賣掉。本來臺北人的平均收入比別的地方更高,為什么反而票賣得不好呢?我的同事們說各種方法都試過了。我就打電話給電臺的一個朋友,拜托說從明天清晨上班時間起做第一波的廣播,在午餐時間做第二波廣播,在傍晚下班時做第三波廣播,主持人只需要講一個話題,就是「臺北真的沒有愛心」嗎?聽說美國有個團體來為921大地震募款,在臺中、桃園非常順利,而在臺北卻出現問題,歡迎觀眾打電話和主持人探討解決方法。那是一個交通電臺,開車的人都會收聽。出租車司機也主動幫我們宣傳。后來不僅票賣光了,而且很多出租車司機還義務把觀眾送到劇場。結果在臺北的四場演出票全部賣光,而且還加演。所以我有一個啟示,絕對不要放棄任何一個機會去做營銷,也絕對不停止做營銷。每次哪怕只有三十秒的曝光,也一定可以找到支持你的人。
如何在60個小時內設計18個咖啡品牌?
一些大公司有錢做廣告,而一些小的機構沒有那么多錢去做廣告。我在臺灣很喜歡做一些公益事情,帶領學生們做的項目叫做”零預算營銷”,就是沒有錢也可以做營銷。臺灣在921地震后發生了一場88風災,讓臺灣中部以南的山路幾乎都斷掉了,有個地方叫特富野部落,是88風災的重災區,山民們種植了政府鼓勵的咖啡豆,結果咖啡豆堆積如山,沒有條件可以烘焙,貨也出不去。
我從一位學生口中知道消息以后,就上山跟部落里的人談話,下山后和臺灣大學的學生在課堂上模擬營銷,在12月初帶領學生們上山。部落里有18家農戶,我把36個學生分成2人一組,任務是在60個小時內設計18個品牌。因為時間很趕,一到了部落就去考察,做記錄,拍照,做訪談,從每個家庭找出有故事的照片,不斷地和每個家庭聊天,然后進行18個品牌的頭腦風暴會議。當天晚上沒有人睡覺,大家在大通鋪上拿出電腦,或者手繪,第二天在部落集合的地方做簡報,整理18個品牌故事,從下午到晚上進行討論,第三天早上把18個品牌的logo(CIS)和宣傳標語全部做好。
轉眼到了1月份,我們在臺灣大學舉辦了一場品牌發布的記者會,把18個品牌用標準的商業要素,包括標準字、標準色全部做好,名片也全部印好, 商品的包裝和包裝袋都打樣好,就是一整套的CIS標識全部設計好,部落的鄒族原住民穿著民族服裝來到現場,當天的每家電視臺和晚報以及第二天的報紙都報道了這個活動。講述臺大的36個學生無怨無悔為了原住民部落翻山越嶺,有人擔心山路危險不敢告訴家人,現場記者都很感動,做了大篇幅報道。從那天以后到現在,消費者是買不到那里的咖啡的。因為臺灣的每個企業都有福利委員會,他們看到報道中臺灣有個2600公尺海拔的地方種植著品質極好的咖啡,就全部預定了,每年生產好就直接送到每個企業的福利委員會,到今天為止,我都買不到那里的咖啡。這就是營銷的逆轉法則,怎么把奄奄一息的東西進行復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