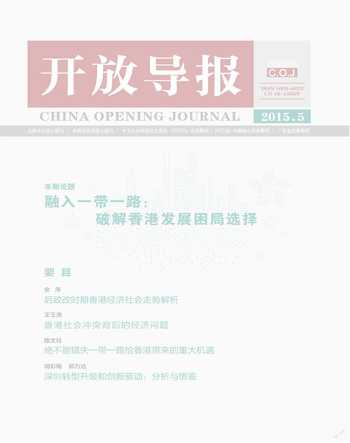后政改時期香港經濟社會走勢解析
[摘要] 綜合來看,香港進入經濟周期下行、爭斗與矛盾頻發的社會“新常態”,突出表現為經濟增長放緩、社會民生福利改善提升有限。如果這些困擾社會的普遍而基本的問題不能妥善加以解決,香港的長治久安就難以實現。應采取有力措施,切實解決涉及香港普羅大眾福祉的經濟民生問題,使社會重拾希望和信心,為“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翻開新的篇章。
[關鍵詞] 香港 “后政改” 經濟增長 社會民生 問題與挑戰
[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6623(2015)05-0007-03
[作者簡介] 金萍(1964 — ),北京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經濟部副部長,研究方向:港澳問題、區域合作。
自2013年起,歷時近兩年,經歷“占中”風波沖擊的香港政改方案,于2015年6月被反對派捆綁否決,香港社會進入了紛爭更為復雜的所謂后政改時期。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要放下政改爭拗、聚焦經濟民生,這一呼吁盡管得到社會大多數人的認可,但并不能遏制社會紛爭的不斷發生和社會更加政治化的趨向。香港近期爆發的“鉛水事件”和“港大副校長遴選事件”表明,香港錯綜復雜的社會深層次矛盾已經對解決經濟民生問題形成掣肘,而反對派和激進勢力的蓄意挑釁依然來勢洶洶,香港社會各種矛盾不僅沒有因為“占中”和政改結束而告暫緩或平息,反而通過各種形式不斷爆發。而從2013年開始,香港經濟下行的勢頭突顯,“占中”之后旅游和零售市場明顯走低,使得香港經濟增長步入2%(甚至更低)時代,可以說,以“占中”為標志,香港進入了經濟周期下行、爭斗與矛盾頻發的社會“新常態”。
回歸18年以來,香港經濟發展經歷了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一是1997至2003年,香港遭遇亞洲金融風暴重創,又恰逢全球科技股災、禽流感和SARS等來襲,股市、樓市斷崖式暴跌,市場極度蕭條,經濟大幅度滑坡。二是自2004年起,主要是實施CEPA和開放自由行,在內地需求的刺激下,香港GDP總量(以市值計價)才得以恢復到1997年水平,經濟發展經歷了十年比較穩定的發展期,盡管期間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的影響,但仍實現了十年平均4%的實質增長。但與上世紀60至90年代接近雙位數的增長相比,明顯動力不足。
作為小型經濟開放體,香港在回歸之后經歷了多輪外部沖擊,在經濟大落大起的同時,社會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特別是CEPA實施后,香港與內地融合的步伐明顯加快。在內地需求的推動下,香港經濟要素不斷向服務業聚集,服務業占比目前已超過93%,并形成高端金融和低端商貿兩大主要核心產業以及與之相配套的航運物流、旅游和工商專業服務。高端金融服務業是香港經濟的主要增長點,而低端商貿服務業則承擔了吸收普羅大眾就業的功能。香港經濟高度依賴于單一的服務產業及其產業二元化形態,使得香港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空間狹窄,社會兩極分化日益加劇。2013年香港人均GDP達3.8萬美元,但貧困人口卻達131.2萬歷史新高,占總人口的19.6%,成為世界發達地區中少有的貧富最懸殊地區。而且,香港經濟的二元化已從收入二元化走向了財富二元化。
面對內地的巨大需求,香港完全處于自由放任狀態。然而,興旺的內地需求并未給香港普羅大眾帶來更加美好的生活。作為小型服務經濟體,外部需求的增加,本應該是重大利好,但數據表明,從2003年到2013年,香港實際GDP增長了55.6%,而從業者的薪金并沒有明顯提高。香港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僅從1萬港元增加到1.3萬港元,折合年增長率不足3%;“按行業類別劃分的就業人士評價薪金指數”顯示,以1999年第一季度為100,2003年和2013年所有行業類別的實質指數分別為106.8和114.3,表明香港普通工薪階層并未從對內地開放中得到實惠。由于沒有及時有效地增加服務設施供給,這些需求反而帶來租金的大幅上漲、社會環境和公共服務質量的日趨惡化。以就醫方面為例,香港的醫療條件曾經非常令人稱道,但目前的情況則是醫療供應嚴重不足,醫療設施超負荷運轉,公立醫院人滿為患。2003年到2013年,香港醫療機構病床數從每千人5.3張下降到5.1張。與此同時,香港人口年齡中位數快速上升,每年增加約0.4歲,2013年已達到42歲。年齡中位數的上升,意味著城市活力的下降,也意味著今后對于社會福利相關的軟硬基礎設施的需求大幅增加,而內地需求的無限制加入無疑使原本就顯不足的供給更加緊張,社會沖突不可避免。
香港經濟結構變化引發的社會矛盾既是外在因素推動的結果,也離不開內在因素的作用。香港作為一個小型開放服務經濟體,在完全自由的市場模式下已經形成了高度的市場壟斷,特別是土地和房地產高度集中所造成的超高成本,幾乎剝奪了所有產業和民生發展的空間;而特區政府堅信自由主義的理念,在調控市場、改善民生方面無所作為,使得社會民生矛盾逐步累積日益加劇,突出表現在住房、就學、養老等諸多方面。
住房方面,香港人多地少,居住問題一直是民生頭等大事。港英時期實行的“居者有其屋”計劃,使得60%的居民住上了政府提供的公屋(廉租房)和居屋(經濟適用房),大大緩解了居住矛盾。回歸前,港英有意實行高地價、高房價和高福利政策,抬高了香港的營商成本。回歸后第一任特首董建華為香港長遠發展考慮推出“八萬五計劃”并加大了土地供應。但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香港出現了大量的負資產居戶,2003年后特區政府基本停止了土地供應,也不再建居屋。此后號稱亞洲大都會的香港每年供應的私人住宅不到1萬套,僅相當于內地大城市一個中型樓盤的供應量。到2013年,香港居然無地可供。香港很多土地是不能開發建設的郊野公園,而農地變成商業用地程序又極為復雜,因此香港房價飚漲,大多數居民置業、青年人成家立業的目標都成了泡影。土地是一切供應的核心,土地供應減少不僅影響了居民的住房問題,購物商場、寫字樓、醫院、學校、交通設施和新產業發展等都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基礎設施和商業樓宇供應不足造成的資產價格大幅度膨脹,大大加劇了本來就相當嚴重的收入兩極分化趨勢,并從收入的兩極分化走向財富的兩極分化。
就學方面,大學升學率低是主要問題。2013年香港的大學學士學位升學率不到30%,包括海外留學和自費課程,香港適齡青年上大學本科學位者在35%左右①。這一數據不僅與國際發達經濟體相差太遠,也與北京、上海等內地大城市有較大差距,因此就不難理解香港大學校園內對來自內地、占10%的學生的敵視或不友好。年輕人升學艱難,自然沒有更多好的就業機會,而薪金也不能隨經濟發展而提高,再加上飆升的房價,使得很多青年一進入社會即淪為貧困。據2009年統計數據分析,青年貧困人口為18萬,貧困率高達20%,比十年前增加28%。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年輕人看不到生活改善的前景,社會上有個風吹草動,他們打先鋒、沖出來鬧事的幾率必然會很大。
社保方面,由于沒有全民退休保障,香港長者貧困率居高不下。根據2012年的統計數據,香港有近1/3的長者生活于貧困線下,其數據可謂觸目驚心。根據政府2012年發表的人口推算數字,香港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將在2041年達至30%。如果不計算其它致貧因素人口,單是長者的增加,已使貧窮人口凈增加45萬。在香港這個高度發達的社會中,“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代版每天都可能在八旬老人身上上演,這種景象實在令人難以想象。
自2003年以來,中央政府對香港經濟給予了強有力支持,頻頻送出“大禮包”,但由于香港社會沒有構建合理的分配機制,受惠的主要是商界和持有房產的既得利益階層,結果反而加劇了香港的貧富差距和社會資源緊張的矛盾,形成了收入和財富的雙重二元化結構;而特區政府管治的放任,特別是對社會問題的回避,也使得民怨不斷加深。近年來特區政府面對日益嚴重的社會矛盾仍不斷出臺不惜傷害長遠發展、換取短暫和緩的“短視”政策,更加劇了香港未來的風險。
歷史的經驗表明,經濟民生是現代社會繁榮穩定的基石。回顧香港回歸18年的歷程,不難發現期間發生的兩次重大的社會事件,即2003年的“七一事態”和2014年的“占領中環”,都有著深刻的經濟社會背景和復雜的政治環境。其中內外因素導致的經濟民生困頓是社會爆發危機的重要因素。如果這些困擾香港社會的普遍而基本的問題不能妥善加以解決,香港社會的長治久安就難以實現,一點微小的事情都會釀成頻發的社會運動。這就是香港越來越政治化甚至激進化的社會基礎。香港的“深層次矛盾”說到底就是社會的經濟資源高度壟斷,人員的流動和上升空間狹小甚至停滯,青年人上不了大學,適應不了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中產階級生活質量不斷下降;老年人晚境堪憂,整個社會發展無望,彌漫著很重的怨氣和戾氣。應該說,這十多年來問題不斷積累,矛盾不斷深化,并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實踐表明,香港社會已經進入內部爭斗的政治化漩渦而難以自拔。如果再不下決心從源頭上加以解決,遲早會不斷爆發更大的社會政治危機。中央和特區政府應該下定決心,果斷決策,在外圍環境和香港經濟出現急劇惡化和危機之前,采取有力的措施,切實解決涉及香港普羅大眾福祉的經濟民生問題,使社會重拾希望和信心,為“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翻開新的篇章。
Abstract: Generally speaking, Hong Kong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period in which the economic growth slows down, and peoples livelihood and social welfare improvement are limited. If these problems cannot be properly resolved,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las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Hong Kong. Therefore, Hong Kong shoul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resolve economic and livelihood issues, and then society will regain the hope and confidence. In this way,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actice will successfully open a new chapter.
Keywords:Hong Kong, Post-Political Reform, economic growth, peoples livelihood, issues and challenges
(收稿日期: 2015-09-21 責任編輯: 垠 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