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想象的逆鏡像
李歐
烏托邦想象與敘述在西方文化中可稱得上是源遠流長、豐富多彩。當代西方烏托邦理論研究者,常將西方烏托邦敘述追溯到《圣經》、柏拉圖的《理想國》以及古希臘赫西俄德的《工作與時日》、古羅馬普魯塔克的《來科古斯傳》等等。當然,眾所周知,“Utopia”觀念的正式定型來自16世紀莫爾的著作《烏托邦》以及康帕內的《太陽國》、培根的《新大西島》。而這些“近代”的烏托邦敘述,與西方古代相比,神話思維與神話想象大大減弱,理論設計的性質普遍增強,而且可實踐性也大大增強,似乎是人類社會即將實現的藍圖。19世紀的西方,文化的主調是樂觀主義,相信人類正在向“天堂”前進,科學會幫助人類戰勝困難,“伊甸園”可以甚至即將達到。在這種文化氛圍下,烏托邦文藝風云際會,幾乎泛濫成災。有人統計,在19世紀最后十年,就大約有一百多部烏托邦小說出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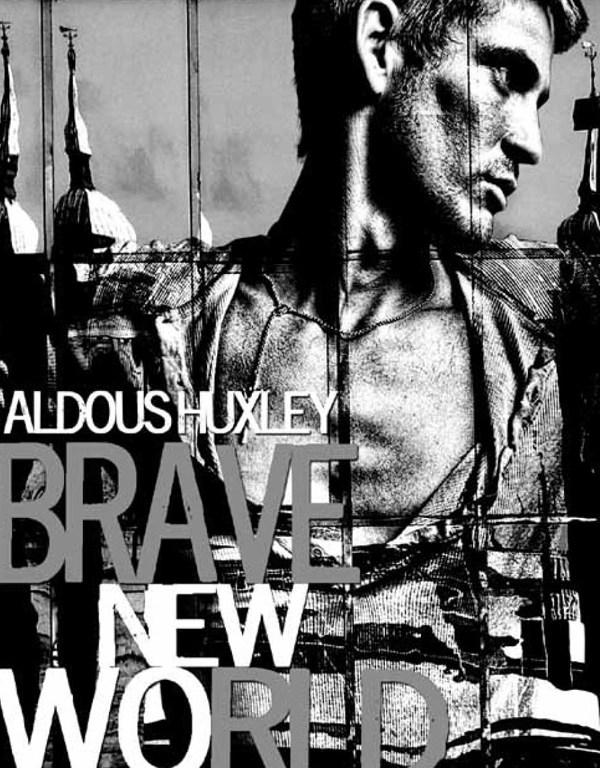
到了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大屠殺,種族滅絕,生態危機,恐怖主義……人類似乎不是在向天堂前進,而是更趨近于地獄。殘酷的現實,導致悲觀主義大流行,文藝基調大逆轉,于是“反烏托邦”文藝開始盛行。明顯的表現之一是,各種“烏托邦(Utopia)”的反面概念術語,不斷被思想界創造出來。像“顛倒的烏托邦”(reverse utopia)、“非烏托邦”(non-utopia)、“丑惡的烏托邦”(nasty utopia)、“諷刺烏托邦”(satiric utopia)、“反烏托邦”(anti-utopia)、“惡托邦”(dystopia)、“批判的烏托邦”(Critical utopia)等等,一般簡而言之統稱為“反烏托邦”(anti-utopia),這是20世紀西方文藝的主潮之一,即或是非典范的“反烏托邦文藝”,也或多或少的帶有一些“反烏托邦”的意味,如系列電影《黑客帝國》等。
其實,反烏托邦文藝還可追溯到19世紀及以前的一些文藝作品,如威爾斯的科幻小說,“未來世界”就已經開始悲慘,只不過沒有形成氣候,不過是樂觀主義畫面上,一兩抹憂郁的色塊而已。“反烏托邦”文藝在20世紀上半紀主要表現在小說,下半紀主要表現在影視,進入21世紀,勢力稍減,但在網絡文藝、卡通、漫畫等文藝領域,卻繁榮起來,看來21世紀的西方也不會是樂觀主義的世紀。
在小說領域,首先是所謂的三大反烏托邦小說:《我們》《美麗的新世界》和《一九八四》。從文學性、審美性來看,《我們》與《美麗的新世界》談不上多么高明,敘事策略平常;而奧威爾的《一九八四》與他先前寫的《動物莊園》,都可以稱得上20世紀的文學經典。可惜他英年早逝,未得諾獎。不過,能稱之為“三大”,其意義在于這三部小說共同奠定了、甚至確立了反烏托邦文藝的主要觀念,甚至是主要情節、主要性質。后面緊隨的反烏托邦文藝無論有多么多樣化的發展,仍只是這三部小說所建立的領域內的變化,所謂“丸不出盤”而已。包括影響極大,甚至可以稱得上是20世紀西方文學的經典,如威廉斯·戈爾丁的《蠅王》,伯吉斯的《發條橙》,艾拉·萊文的《這完美的一天》等等;因此,當代研究反烏托邦文藝,仍是以這“三大”為核心而展開。另外,重要的“反烏托邦”小說還有美國的《記憶傳授人》,加拿大的《羚羊與秧雞》等等。
20世紀下半紀,反烏托邦文藝最大發展是在電影領域。電影作為20世紀文藝的“燈塔”藝術,雖然“反烏托邦”并沒有構成其主流,但一些重要的反烏托邦電影作品產生了重要影響。首先是《一九八四》,1954年被改編成電影,1984年再次被拍成電影,評論者認為可以視為電影加入“反烏托邦”譜系的一個標志。還有曾被評為“歷史上十大優秀科幻影片”首位的《銀翼殺手》以及影響較小的《羅根逃亡》等,這之后,伴隨著“反烏托邦”小說的逐漸衰落,“反烏托邦”電影卻日漸興盛,如《巴西》等等。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后,更是不斷問世:《撕裂的末日》《人類之子》《V字仇殺隊》……還有近年來在中國上映的《雪國列車》,雖然它是韓國電影,但卻是高度“西化”,而且是韓國電影試圖融入“國際”的一種努力。
當代西方“反烏托邦”文藝還不時出現在漫畫、卡通、lT游戲中,如標準的“反烏托邦”電影《V字仇殺隊》,實際上先是小說,后被改編成漫畫,最后才改編成電影。
從“烏托邦”到“反烏托邦”,反映了西方文化思潮的變化,究其原因,首先是對人類文明與人類生活必然會不斷“進步”的觀念的懷疑,對人類終將戰勝自然,終將戰勝自身的愚蠢,而終將走向“伊甸園”這一信念的懷疑。無論是政治大革命,還是科技大發展,確實使人類在不斷的“進步”,尤其是科學技術上帶來的生產效率,使人類的物質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可是人類“進步”是否就一定意味著人類“幸福”?反思審視人類20世紀的生存狀況,就如當代加拿大人類學家隆納·萊特(Ronald Wright)在《進步簡史》中深刻憂慮地指出,人類已經陷入“進步主義陷阱”中,而且無力自拔。因此,當代美國著名的文藝理論家弗·詹姆遜曾評論道:“對烏托邦的沖動的邪惡進行了批判和分析,已經變成了一個迅速發展的行業。”很多當代西方一流思想家與學者都直言不諱地對烏托邦觀念進行抨擊。如波普爾、哈耶克、伯林等,他們甚至認為對烏托邦思想的誤用,是造成20世紀人類社會諸多災難的重要原因。在這種思潮影響下,反烏托邦文藝風生水起,不足怪也。
當代西方的反烏托邦文藝作品眾多,但是其主題、內容,甚至主要情節卻大致相同,主要有以下內容情節。首先是“未來社會”不是近于天堂,人人快樂、自由、平等和幸福,而是幾乎一致地認為將要出現“極權社會”,社會處于高度集中的權力控制之下。《我們》中的“大一統國”封閉在綠色大墻內,每個人的每分鐘都被嚴密控制:
每天早晨,我們幾百萬人像六輪機器一樣準確:在同一小時、同一分鐘,像一個人似的一齊起床。在同一小時,幾百萬人一齊開始工作,又一齊結束工作。我們融合成一個有百萬只手的統一的身軀,在守時戒律表規定的同一秒鐘,把飯勺送進嘴里,在同一秒鐘出去散步,然后去講演廳、去泰勒訓練大廳,最后回去睡覺……
只有在“性活動日”時,人們才有權利放下窗簾,遮擋在玻璃房上,使人們有了那么一丁點兒的隱私,然而,這一行為卻是需要憑“票”進行的。
先由性管理局的化驗室對號碼們作全面檢查,準確確定血液中性激素的含量,據此制訂出相應的性活動日期表。然后人們就可以提出申報,自己在哪些日子里愿意和某某或某某號碼發生性關系,并有權得到一個粉紅票子小本子。至此就萬事大吉了。
這一切的背后是高度發達的科技力量。科技發展,其目的是為了人類的解放與自由。而在極權政治下,科技成了強大的邪惡力量,支撐著恐怖。電影《雪國列車》,得以維持運行,依賴高度發達的科技,而《一九八四》中無處不在的監視,也是依賴高技術的支撐。在《美麗的新世界》中,一個人從生到死都受著科學技術的控制,生育、性別、身份、職業,甚至性快感、語言都由高技術來全面控制。在妊娠期中每個胚胎就被編程設定了各種條件,即在胚胎時期就“命中注定”擁有不同的命運、職業、愛好、從事的工作甚至思想。可以說,科學技術對人類的控制已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這些反烏托邦文藝作品,實質上是對當代人類生存狀態的質疑:幸福感、快樂和穩定一定要以壓制自由、個性、創造激情為代價?科技無節制地發展,是否是讓人類登上了欲望號列車,向深淵極速前進?為科技發展所依賴的工具理性是否會必然導致人會異化為機器?當生命被儀器所包圍,人格是否也會被淹沒而窒息?……在小說《記憶傳授人》中,為了更好地“控制”,連每個人的記憶都應消失。這與馬克思所描述的“共產主義社會”有天淵之別。馬克思認為“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類的特性”,共產主義社會應是“自由人的聯合體”;而這些反烏托邦文藝所描述的“未來社會”,則完全否定和壓抑人的自由、自由思想和個體性。如《我們》中稱:“自由和犯罪緊密不可分地相聯系著……就像飛船的飛行和它的速度。飛船速度等于零,那它就不能飛。人的自由等于零,那么他就不會去犯罪。這是很明白的。要使人不去犯罪,唯一的辦法,就是把人從自由中解放出來。”即或是人們生活無憂,快樂立即可得,如《美麗的新世界》中通過服用“唆麻”,難道這是人類所奮斗追求的世界?這無疑是反烏托邦。
其實,反烏托邦文藝,在一定意義上是烏托邦文藝的一種發展,一種逆轉性的發展。除了外部環境,時代境遇的刺激外,烏托邦文藝與反烏托邦文藝在內在邏輯上有相通之處。莫爾構建的理想社會,人人追求為大快樂放棄小快樂!為他人利益放棄自己的利益;但是再向前走一步,“我”就成了“我們”,以社會名義犧牲個體;權力集中就成了恐怖宰制,個體的人則淪為喂養國家這個怪物的食料。《太陽城》中規劃的全體居民的“作息時間表”,就是《我們》中全體社會絕對步調一致的生活秩序的先聲。可以說,反烏托邦文藝是烏托邦文藝的一種逆鏡像。
反烏托邦文藝,并不僅僅是某種絕望與恐懼的情緒表達。可以認為反烏托邦文藝的生產者是人類文明的“守望者”,表現了直面慘淡人生的批判意識,是一種嚴肅的現實主義精神,同時也暗含著對美好未來的強烈的訴求,即在恐懼甚至絕望中仍有堅守。烏托邦思想的真正價值在于它的否定性,對現實中丑惡、異化、災難的否定,以“將來”的光明來燭照現實,從而促使人們去改變現實。但是已有的“烏托邦”工程的失敗,烏托邦觀念的一些具體實現反而導致人類更大的災難,因而對烏托邦思想的厭倦甚至反感就必然產生,反烏托邦文藝必然會泛濫。但是反烏托邦文藝并非全是絕望情感的表達,我們可以看到反烏托邦文藝的種種凄慘畫面中,作者有意識甚至可能是無意識地總有一絲亮色留給世人。在《雪國列車》的結尾,地球溫度開始回升,僅剩下的兩個人:尤娜和小男孩,還有生存下去的可能性。
當代西方著名思想家保羅·蒂利希曾對“烏托邦”做了深刻的思考,他指出:“如果烏托邦并不同于無價值的幻想,它必定在人自身的結構中具有一個基礎,因為歸根結底只有在人的結構中具有基礎的事物才會有意義。”他斬釘截鐵地強調:“要成為人,就意味著要有烏托邦。”——反烏托邦文藝是烏托邦文藝的“逆鏡像”,是對虛假、變質的烏托邦思想觀念的否定,實質上仍是一種烏托邦精神,一種烏托邦沖動。“戰勝(虛假、變質)烏托邦的,正是烏托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