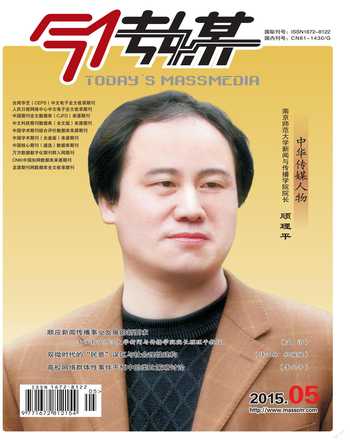國家治理現代化視域下的網絡輿情治理研究芻議
陳端
摘? 要:本文以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理念和中國高層領導大力強化網絡輿情治理作為研究緣起,圍繞信息時代的“治道變革”,深度剖析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總體目標與網絡輿情治理之間的內在關聯;在對當前中國網絡輿論場域及其新變特征重點把握的基礎上,從多個維度梳理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總體目標對輿情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并且基于前述分析對當前中國網絡輿情治理研究重點、研究思路、價值立場、研究視野、理論資源和研究方法等關鍵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關鍵詞:國家治理現代化;網絡輿情治理;治道變革
中圖分類號:G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5)05-0019-03
一、引 言
2013年11月份召開的中國共產黨黨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政改中間模式的“治理現代化”理念的提出(田飛龍,2014),是糅合了對社會發展總體趨勢研判和中國政治智慧的一種話語創新,標志著中國社會的制度變遷擺脫了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新時代以來“自下而上、局部創新”的自發變遷路徑,在不觸動基本政體格局、不引發意識形態層面爭論的前提下,轉向以現代化為發展取向、以法治為基礎的“統籌規劃、頂層設計”新模式。在這種模式之下,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手段現代化(俞可平,2014)、治理體系制度化、科學化、規范化、程序化(江玉新,2013),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公民、權力與權利的關系將被重構,從一元單向管理到多元交互共治,“黨、政、企、社、民、媒”共同構成了新形勢下的多元國家治理主體群落(陶希東,2013)。
在此時代背景下,作為新時期社會治理與國家治理的重要主體和參與者,媒體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擔當也需要隨之調整。中國的傳媒體制改革本身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有機組成部分,尤其就當下中國現實狀況而言,社會整體變革與傳媒自身變革錯雜交織,社會輿論場域空前復雜,轉型社會中的諸多矛盾和博弈都在輿論場中集中呈現,無論從打造公共話語空間、協調多元治理主體、推進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凝聚發展共識抑或促進公共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等角度而言,行之有效的輿情治理都將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深入推進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2014年2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親自出任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組長,凸顯了最高領導層對網絡安全和輿情治理的高度重視。因此,將輿情治理現代化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有機組成部分,立足于中國現實國情土壤和現代傳播格局的深刻變動,總結把握現代輿情生發衍變規律,深入剖析輿論生態與政治生態的多元互動關系,研判新形勢新格局下的新情況新特點,立足國家發展戰略高度構建起科學化、規范化、法治化的新型輿情治理體系,以推動法治中國的“治道變革”,這對于中國社會全面轉型和社會進步具有積極意義,本文在此嘗試進行一種研究框架和研究思路層面的探索,以期拋磚引玉,引發更多深度思考。
二、國內外關于“治道變革”的相關研究簡介
從國際上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下催生了以加強政府回應性和滿足公民意愿為主要目標的“治道變革”,這場潮流發軔于西方發達國家,后發展為一場全球性的運動,被視為“公共行政的范式轉換”(歐文休斯,2007),由信息技術驅動的國家治理變革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西方發達國家在治理現代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官僚制的改革和流程再造,后來又陸續出現了“分權治理”、“合作治理”、“網絡治理”、“公民治理”、“數字化民主”、“虛擬政治”等拓展研究;哈斯曼德在《善治:以民眾為中心的治理》中探討了如何把治理內化為秩序,從而使治理成為善治,輿論引導、輿情治理與“善治”之間的內在關聯被思考和關注。在應用輿情推動治理方面,美國建立了一個強大的輿情分析收集系統,每年花費在民意調查上的資金約數十億美元,輿情采集與新聞發言人制度一起成為政府與公眾溝通和形象塑造的重要橋梁。
中國學者“治道變革”的相關研究有法治框架、善治框架、轉型框架和現代化框架幾種研究框架,涌現出俞可平、楊光斌、羅榮渠、毛壽龍、鄭永年等一批代表性學者,但因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念系最近一年才提出來,國內學者關于國家治理現代化和輿情治理的關聯研究開始有一些探討,但成熟性的成果尚比較欠缺。
三、當前中國網絡輿論場域的總體描述
(一)當前中國網民數量、結構總體描述
2014年是中國實現全功能接入國際互聯網20周年,中國網民數量早在2008年6月已經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2015年2月5日,CNNIC(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發布第3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對中國網民規模與結構特征、網民互聯網應用狀況、手機網民規模等數據信息做了全面披露。
根據這份報告,截止2014年12月,中國網民有6.32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46.9%。在這6.49億網民中,手機網民規模達到5.57億,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人群比例高達85.8%,手機使用率已經超越傳統PC使用率,成為第一大上網終端設備。與之相應,社會輿論場域向移動端的遷移更加明顯。
(二)當前中國輿論場域所處的整體社會背景
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總目標的改革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全面深化改革既涉及理念和方向之爭,也涉及利益和權力的激烈博弈,屬于社會發展的非常態運行階段。就國內形勢而言,改革與轉型交織,利益博弈與觀念交鋒并存,按照官方表述,“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內外環境、矛盾、風險、困難多重疊加;就國際環境而言,我國大國崛起、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與全球治理結構的深刻調整同步,國內政策溢出效應日益明顯,也不可避免會受到外來力量和外來因素干擾。
就改革本身而言,立足長遠健康發展的改革會引發局部短期陣痛,社會公眾追求公平正義的心理期待與可能承擔的改革成本錯綜交織,有可能引發局部社會心理震蕩;深水區的改革本就暗礁密布,是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的過程,現有的政策工具騰挪空間日益狹小,制度創新、政策創新勢在必行,一旦創新或實施過程中出現操作失誤或用人失當都可能激化既有矛盾;從長遠看,以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總目標的改革是中國百年現代化歷程的又一新起點,國家治理的制高點是倫理塑造(江玉新,2013),將人的社會化與國家整體的現代化進程結合,塑造擁抱變革、勇于接受挑戰的現代國民性格,以文明復興支撐真正意義上的大國崛起,都需要兼顧秩序穩定與發展活力的輿情治理體系做保障。
(三)當前中國輿論場域的新變特征及其給輿情治理帶來的挑戰
1.微博輿論場式微,微信輿論場崛起
現代傳播構筑起全新的社會互動體系,社會風險系數和輿論變數不斷增大(丁柏銓,2012);2012年以來,微博作為社會公共話語空間和民間輿論場域核心的地位逐漸式微,據CNNIC第33次中國互聯網發展情況統計報告,2013年微博用戶規模下降2783萬人,使用率降低9.2個百分點,22.8%的網民使用微博的時間減少;與此同時,以微信為代表的社交網絡崛起,成為新的民間輿論場域核心。CNNIC數據表明,減少使用微博的人中,37.4%的人轉移到了微信。與微博相比,微信傳播內容與人際關系鏈條相依相生,非常態社會動員及社會組織風險大大提升,“朋友圈”、微信群和微信公眾號成為新的信息傳播關鍵節點,原有的新聞場、輿論場、心理場等場域格局發生深刻變遷,公共議題生發傳導機制、社會意見領袖生成淘汰機制及輿情傳導路徑都呈現出新的特點;在以微信群為代表的社群傳播模式下,輿情偶發性強,不可控性增加,可能風起于青萍之末,由單個事件意外引爆社會積蓄的情緒,在短時間內通過跨群傳播模式迅速擴散,輿情危機逾越潛伏期直接爆發;與此同時,后現代娛樂文化盛行,權威消解,神圣遭遇解構,受眾基于自身心理基模對內容進行戲謔性的解碼及再編碼,給輿論引導和輿情治理工作帶來深度挑戰,傳統的媒體管控模式在新的內容生產機制面前效力式微。面對空前復雜的輿論格局,一味的壓制管控只會激發非常態的表達渠道和表達方式,需要轉變觀念,總結規律,以新的姿態重新審視和對待。
2.低學歷、低收入網民比重上升,網絡民粹主義抬頭
隨著網絡使用的快速普及和網民基數的擴大,低學歷、低收入網民在整體網民結構中比重上升。根據CNNIC最新統計結果,當前網民構成中,本科及以上學歷者僅占10.7%,農村網民規模已經達到1.77億,占整體網民的28.6%。以下崗工人為代表,很多低學歷、低收入網民本身處在社會運行的邊緣,社會參與和社會表達渠道少,在整個社會改革和發展過程中利益受損,“相對被剝奪感”較強,渴望公平和正義,網絡成為其表達意見、謀求社會話語權和能見度為數很少的重要渠道,但因為對問題的分析相對簡單淺表,在意見表達上容易偏激極化,情緒化表達比較激烈,如果引導不當,很容易出現“網絡鍵盤俠”和“網絡廣場政治”,使網絡輿論場存在著引發“網絡民粹主義”的潛在風險。
3.左右分歧加大,話語體系的分裂帶來輿論場域的分裂風險
德國著名傳播學者伊麗莎白·諾依曼提出了“輿論是社會的皮膚”的論斷,強調了社會輿論對社會發展和社會結構變化的強烈指示性作用和價值。網絡輿論場域的博弈就其本質而言,是社會深層矛盾運行和利益博弈的折射和體現。改革進行至今天,基于價值和理念的方向之爭逐漸凸顯,緬懷計劃經濟和毛澤東時代的左翼群體與支持市場經濟高呼自由民主的右翼群體各有其輿論領袖和話語體系,在網絡上意見分歧加大;與此同時,以莊重肅穆為特點的官方話語和以調侃戲謔為特點的民間話語、以社會穩定為內核的維穩話語與以個體權利為內核的維權話語之間也呈現出一定的分裂,話語體系的分裂使得輿論場存在參與方各說各話、有交鋒無交流的風險,難以通過對公共話題的深入討論凝聚發展共識。
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的網絡媒體一開始是以“補償性媒體”的角色登上歷史舞臺的,與掌握社會話語權和主流媒體傳播渠道的社會精英相比,網絡成為邊緣群體更為倚重的表達渠道,通過網絡話語宣泄取得“代償性”心理滿足,某種程度上也起到了社會發展“安全閥”的作用。但與此同時,邊緣群體對網絡傳播和表達渠道的高度倚重也非常態的社會動員風險,影響到社會整體的安全穩定運行狀況,尤其是在改革進入深水期、攻堅期,社會矛盾進入多發期、交錯期的當下,肇始于網絡的群體性事件頻發,已經構成社會發展和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潛在威脅。因此,對于社會輿論場域發展態勢的全面把握和社會輿情的綜合治理已經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
四、國家治理現代化總體目標對當前中國輿情治理提出的新要求
如前所述,當前中國輿論場域出現的新情況、新特征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總體目標呼喚輿情治理思路的創新,要從理念上對輿情治理的內涵重新認知,思路上做出重大轉換,超越“維穩”、“維權”的二元平衡思維和危機應對性輿情管控模式,以彌合社會分歧,強化社會發展共識為主要訴求,順應潮流,充分挖掘新技術為輿情治理創新帶來的可能空間,讓輿情治理成為提升社會治理水平和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驅動力;于2014年10月20日~23日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擘劃出依法治國的路線圖,國家對輿情的治理也應逐步導向法治化軌道,以法治的可預期性與可操作性設置社會傳播底線,穩定民心,紓緩民情,推動民間輿論場和官方輿論場的良性互動,推動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帶來多方共贏善治的正和博弈。?要深入探索新形勢下輿情治理的手段創新、模式創新、機制創新,站在國家發展戰略高度構建起國家立法、公民守法、社會協同、共識引導、技術保障、多元互動、分類治理、彼此協調、自律與監督相結合的常態化、科學化、規范化、法治化的現代化輿情治理體系。對大眾傳播媒體,要以良好的治理策略和激勵機制鼓勵其進行傳播創新,恪守媒體職業道德,凝聚傳播共識,牢記話語底線,承擔應有的歷史責任;對于廣大自媒體和社交媒體用戶,要通過敏銳的輿情采集、研判和反應機制的構建,讓他們切身感到自身的聲音能夠被傾聽、被尊重、被采納,讓民情民意的社會表達有合理合法有效的渠道,并且因為這種傾聽、尊重和表達渠道的有效性避免情緒的積壓與態度觀點的極化,以傳播的溫情和溫度帶來理性溫和的溝通,在尋求各方利益最大公約數的基礎上推動發展共識的形成。
五、當前中國網絡輿情治理研究思路及方向探討
就相關研究而言,要立足中國國情,綜合歷史文化、現實國情、時代精神和未來趨勢,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中國道路、中國模式框架下,尋找“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轉型過程中媒體在多元交互共治方面的功能空間與責任擔當,以此作為輿情治理創新的研究邏輯起點;現實的發展要求我們超越以往輿情研究主要依托的新聞傳播學研究視野,引入公共管理學、社會心理學、系統論等學科理論,將輿情研究置于全球化、信息化時代“治道變革”的大視野中進行探討,順應歷史潮流,以發展眼光審視當下問題,并且緊扣全面深化改革大局下的現實國情;要深入把握影響當今輿情治理的支撐力量和約束條件,厘清輿情治理的要素變量與制度變量,可以采用系統論的分析方法,把輿情治理現代化視為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大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以“善治”為目標,通過系統目標分析、系統要素分析、系統環境分析、系統資源分析和系統管理分析進行系統化的輿情治理體系建構。
數字化、全媒體、大數據等信息傳播技術的發展促動了新聞生產機制、流程和新聞形態的嬗變,同時也提供了創新治理手段、拓展治理寬度、提升治理精度的契機,優化輿情治理模式、深入挖掘傳播技術為促動社會發展帶來的各種可能對國家治理能力提升大有裨益。
此類個案不勝枚舉,例如,大數據技術讓輿情監測與研判超越了簡單的內容分析層面,可以從社會話語表達、社會關系呈現、社會心理描繪、社會訴求預測等角度對社會輿情進行多維透視,以對社會輿情的技術性挖掘見微知著,透過網絡輿情窗口形成對社會發展狀況的全局性、整體性描摹,讓決策者能更好認知社會發展階段性需求,探測民意、體察民情、順應民心進行公共決策制定,同時也為紓緩社會矛盾、尋求各方發展的最大共識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撐。此外,通過網絡輿情數據進行立體化、全局化、動態化的關聯分析,可以將輿情監測的目標時間點提前到敏感消息進入網絡傳播的初期,通過對網絡用戶原有人口社會學數據和行為軌跡數據的關聯挖掘,輔以模型建立、模擬仿真實際網絡輿情演變過程,實現對突發輿情的方向性預測,據此及早采取相應措施,防止網絡突發性事件演變成為線下的社會性事件。
網絡輿情治理的研究離不開治理效果的評估。任何評估指標體系的有效構建必須以核心價值目標的設定為前提,國家治理現代化視域下的輿情治理效果評估,首先涉及到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價值目標的確定,其次是評估主體和評估理論工具的選擇,再次是評估指標體系的構建,評估數據的采集和匯總分析。當前的改革進程中,觀念爭鋒和利益博弈無處不在,由誰來評估?如何評估?如何搭建評估結果與輿情治理體系之間的正向反饋和修正調整機制,使我們的輿情治理突破過去一元剛性媒體管理思維藩籬,形成與現代治理理念和治理環境相適應的柔性治理體系?這些都是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不斷傾聽業界人士和民眾呼聲進行深度研究和系統總結的研究重點。
參考文獻:
- 丁柏銓.論網絡輿情[J].新聞記者,2010(3).
- 歐文休斯.公共管理學導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 喻國明.大數據分析下的中國社會輿情:總體態勢與結構性特征——基于百度熱搜詞(2009—2012)的輿情模型構建[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3(5).
- 俞可平.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若干問題[N].福建日報,2014-06-08.
[責任編輯:東方緒]
——評《中國現代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