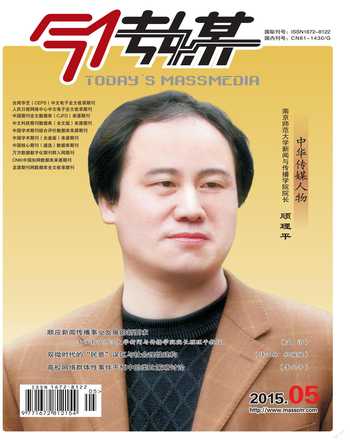從禮物交換看馬塞爾?莫斯的交流傳播觀
張露
摘? 要:本文通過闡述法國人類學家馬塞爾·莫斯的禮物交換理論,介紹莫斯三重角色——讓·鮑德里亞的理論向導、齊美爾的思想知音和涂爾干的學術繼承人的同時,著重從禮物交換的象征性、交換行為的社會性和交換主體的總體性三個角度探析了莫斯的交流傳播觀,從而得出現代社會交流危機的病癥所在——內容象征意義的缺失、連續互動鏈條的斷裂以及主體完整人性的分離。
關鍵詞:禮物;象征交換;莫斯;交流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5)05-0141-03
當談及傳播研究的歐洲根源時,法國社會學家塔爾德和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被學界奉為代表旗幟,而其他人文或社科領域的著名學者在此二人的炫目光輝下則略顯暗淡。無可否認,前者的模仿理論和后者的網絡理論是美國諸多傳播學流派誕生和發展的基石。然而正如約翰·彼得斯在分析“communication”一詞的多源涵義時所言,“‘communication theory不是指人們現在習慣的探究理論,它和倫理學、政治哲學、社會理論具有同質性,其關注點都是社會組織中的‘我與‘他、‘我與‘我、‘近與‘遠的關系”[1]。據此,能夠稱為傳播研究思想源流的學者、著作以及理論,在人文社科領域就有了無限延伸,故法國著名人類學家馬塞爾·莫斯或可成為這延伸范圍內的一員。作為社會學年鑒學派的第二代旗手,莫斯的聲譽被親舅舅埃米爾·涂爾干如雷貫耳的名氣有所掩蓋。然而其最具代表性的個人著作——《禮物:古式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理由》(以下簡稱《禮物》),卻被后世學者尊為研究人、物、社會本質關系的精悍之作。這本僅有200多頁的小書“對于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影響絕不遜于乃師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2],反映了一個脫離田野調查的人類學家,基于浩繁的民族志材料,以他者的身份,從禮物交換的角度,對古式社會人之所以為人、社會之所以為社會展開的詳實探析。莫斯的禮物觀或可稱禮物范式,不僅具有啟示象征交換理論誕生的符號學意義,更有佐證交流,使社會成為可能的現象學價值。因此,關于莫斯的交流傳播觀,筆者通過其禮物交換思想即可一探究竟。
一、鮑德里亞的向導——作為象征交換的禮物
象征交換理論成形于法國后現代理論家讓·鮑德里亞的《象征交換與死亡》一書,“一般說來,象征性交換包含著獲取和回報、給予和接受……禮物與對應禮物的循環等各種一般的和可逆的過程”[3]。在祭祀活動和宗教儀式豐富多樣的遠古社會,象征交換主要指的是人與人、人與自然、甚至人與神之間的交流互動。作為鮑德里亞所有核心理論,如符號消費、擬像和仿真的“阿基米德原點”[4],象征交換的思想來源之一就是莫斯的禮物交換理論。在鮑德里亞看來,正是禮物交換中不斷循環往復地饋贈與回贈、給予與接受,建構起了古式社會的社會關系,而這種社會關系就是其所謂的象征交往關系。顯然,現代社會充滿經濟意味的禮物交換和古式社會具有象征色彩的禮物交換已不可同日而語。莫斯甚至在《禮物》一書中,發出了回歸古式社會禮物交換的呼喚,而這種呼喚實際上蘊含了莫斯的傳播思想,即對人與人本真交往的期盼。
禮物交換的象征性首先體現在內容上。通過對波利尼西亞、美拉尼西亞等原始部落族群的研究,莫斯提出古式社會的禮物交換,“并不僅僅限于物資和財富、動產和不動產等等在經濟上有用的東西,它們首先交流的是禮節、宴會、儀式、軍事、婦女、兒童、舞蹈、節日和集市”[5]。相較于現代禮物交換濃厚的功利色彩,古式社會的禮物交換更強調個體以及群體對儀式的參與和對意義的共享。比如特羅布里恩人在婚禮中對“mwali”(手鐲)和對“soulava”(項鏈)的文化認同,前者象征女性,后者象征男性,二者的交換則象征著男女雙方對彼此的親近和對關系的確認。這就是禮物交換象征性的表層體現,而更深層次的體現則在交換雙方和饋贈禮物的“共融”上。與現代社會更加注重禮物的物質屬性不同,古式社會中禮物的實際價值往往回歸于無,從而凸顯出了禮物的象征意義。象征所在“歸根結底便是人物的混融,人們將靈魂融于事物,亦將事物融于靈魂,人們的生活彼此相融,在此期間本來已經被混同的人和物又走出各自的圈子再相互混融,這就是契約與交換”[5]。因此,古式社會中的禮物交換與其說是物的交換,不如說是人的交流。“饋贈某物給某人,即是呈現某種自我”[5],古式禮物交換對物質的消解和對人性的釋放,破除了物與物關系對人與人關系的遮蔽,從而真正實現了人與人的本真交往。
除了內容之外,禮物交換的象征性還體現在其形式上。通過研究西北美洲的夸富宴,莫斯總結了古式社會禮物交換的一般過程——給予、接受和回報。這種贈禮和回禮的交互式行動似乎驗證了彼得斯對communication詞源探索的結論之一——exchange。“‘communication的第三個意義分歧是交換(exchange),就是說,是兩次的遷移,在這個寓意上,它包含交換、情感共享的意思,是一種禮尚往來。[1]”因為回報機制的作用,古式社會的禮物交換變成了永恒輪回的“兩次遷移”。比如象征人神交往的農業祭祀,人在祭祀活動中將充滿感恩和祈禱的“犧牲”獻祭給神,他們相信,“犧牲”之靈會在神的指引下再次回到凡俗社會,進駐到成為來年“犧牲”載體的農業生產中。這就是禮物交換形式上的象征所在——無限循環的社會過程。借鑒中國道家文化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論述,古式社會的禮物交換可謂是一個沒有起點和終點的圈。這個包含了給予、接受和回報模式的圈就是象征的框架,它使得集體意識和共同文化通過交換產生,也融于交換之中。區別于當代斷裂、浮于表面的符號消費,連續、深入人心的象征交往才是人性交流的基石。由此可見,禮物交換之所以稱為象征交換的思想源泉,除了其交換內容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本真交往外,其交換形式更表明了本真交往與古式社會的互為因果關系。而關于古式社會何以可能的問題,莫斯則用其象征性的禮物交換給出了類似齊美爾的答案。
二、齊美爾的知音——社會是如何可能的
關于社會是如何可能的,法國社會學巨擘涂爾干與德國社會學大師齊美爾就社會現象是既定事實還是產生于交流一直存在分歧。前者始終將社會現象作為外部事物考察,后者卻堅持把人類社會作為內在關系研究。盡管身為涂爾干的學術繼承人,以禮物交換思想聞名的莫斯在解釋何為社會時卻與齊美爾有著驚人的相似,即社會是需要建構和維系的關系。根據最早介紹莫斯的專著《莫斯》一書,作者讓·卡澤納弗提到,“莫斯曾指出:整個社會不過就是關系”[2]。齊美爾則認為,“社會現象產生于交流,關系和個體之間的互惠,也就是產生于主體間的運動或‘關系網絡”[6]。因此,晚輩莫斯和前輩齊美爾因陣營原因雖從未有過直接的思想交流,二者對社會如何可能的回答卻表現出了知音般的理論取向。在莫斯研究的古式社會中,循環往復的禮物交換使得個體間的交流、互惠以至關系網絡的建構、維系成為可能。但正如齊美爾將社會如何可能延伸到個人能動性上,深究到意識想象層面,莫斯也跳出了淺顯的關系理論,追根溯源禮物交換的本質以探析社會何以可能。
需要明確的是,莫斯是從禮物交換何以循環的角度提出了類似“社會如何可能”的問題,即“在后進社會與古式社會中……禮物中究竟有什么力量使得受贈者必須回禮”[5]。換言之,是什么讓禮物交換流程中的給予、接受和回報成為一個無限循環的圈,從而使得古式社會的關系網絡在交換和交流中得以生成。莫斯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為“禮物之靈”(Esprit),它在薩摩亞人文化中被稱為“曼納”(Mana),在毛利人文化中則被稱為“豪”(Hau)。因為禮物之靈的存在,“即使禮物被送出,這種東西依然屬于送禮者,由于有它,受禮者就要承擔責任”[5]。此處的責任就是回贈禮物的責任,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歸還禮物之靈的責任。在莫斯看來,它是禮物中包含的來自送禮者的某種精神力量和人格品性。因此,“接受了某人的某物,就是接受了他的某些精神本質,接受了他的一部分靈魂,保留這些事物會有致命的危險,這不單單是因為這是一種不正當的占有,還因為該物在道德上、物質上和精神上都來自另一個人”[5]。據此,禮物交換中的禮物之靈,既確保了生生不息的社會關系,也實現了個體間的人性想象和精神交往。社會的結合事實上是在各種“事物”里實現的——在這里,事物就是個人的心靈[7]。莫斯和齊美爾通過不同方式的闡述,共同強調了社會整合過程中,主體對自我和他者認識及把握的重要性。
如果說禮物中具有的精神是使社會成為可能的內部驅動力,那么交換中流動的意識則可稱為使社會成為可能的外部催化劑。此處的意識亦即齊美爾所謂的,將原本相互分開的智力要素綜合為一個社會統一體的過程。在莫斯看來,禮物交換與個體或集體意識是相輔相成的,交換產生意識,意識推動交換,二者的共同作用實現了交換的行為主體對藏于禮物中的禮物之靈的普遍承認,同時實現了行為主體對藏于交換中的互惠本質的默契認可。雖然禮物交換一直都受互惠(Reciprocate)驅動,但在“最具伊壁鳩魯學說傾向的古代道德中,利益指的是人們所尋求的善與快樂,而不是物質的有用性”[8]。因此可以說,古式社會中的交流雙方都是懷抱彼此都能獲得快樂和善的意識而進行禮物交換的。這種同時站在自我和他者角度上的交流使得每個個體都確信禮物交換中,“流通的根本不是有功用的事物,而是與這些事物緊密融合的個體、群體、榮譽、巫術、宗教、道德等”[9]。換言之,禮物的真正價值在于附著在它之上的聲望、榮譽等象征力量,而這些均已融入到人們的意識之中。比如上文提及的夸富宴,莫斯解釋道:“夸富宴作為一種財物的散發, 就是‘確認(Reconnaissance)的一種基本行徑”,夸富宴作為一種儀式完成了所有參與者對宴會背后榮譽、尊重、道德和快樂的想象與分享。而這些意識生產行為實際上都離不開齊美爾所言的個人能動性,對于能動的人,莫斯也有著其突破導師理論框架的獨特見解。
三、涂爾干的學生——總體的人與社會
正如前文所言,除了師生關系外,莫斯和涂爾干還有著更為親密的血緣關系。這段血緣關系讓最新介紹莫斯的人物傳記《莫斯傳》的作者馬塞爾·福尼耶,直接將全書的第一部分命名為“涂爾干的外甥”,借此驗證猶太法典中的一句箴言——“大部分孩子都像他們的舅舅”。相較于舅甥關系,師生關系或許更能說明莫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學術建樹。作為社會學三大巨頭之一——涂爾干的學生,莫斯繼承了老師社會唯實論的傳統,堅持用社會事實解釋社會事實,并“將一生中的大部分精力都奉獻給了迪爾凱姆的學術搭建和修補工作”[10]。然而作為一個人類學家,莫斯通過《禮物》一書解釋社會事實(莫斯稱為“總體的社會事實”)的同時,更關注著活躍于社會中的人(莫斯稱為“總體的人”),從而“用彌散于生活當中的禮物交換彌合了社會和個體之間連續性的斷裂”[11],使得以涂爾干為代表的社會學更加人類學化。
在莫斯看來,古式社會中進行禮物交換和精神交流的人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原子式個體,而是本身能夠反映總體社會事實的“總體的人”(指存在于古式社會中的道德人)。“總體的人”產生于“混同的人和物又走出各自圈子再相互混融”的過程,也就是說,產生于禮尚往來中的人性交流。“總體的人”和現代社會個體的不同之處在于,“總體的人”是受善之指引而形成的完整的人,現代個體則是受利之誘導而形成的分離的人。“總體的人”之所以完整,是因為其不僅可以通過禮物交換接受他人的靈魂,而且可以通過禮物交換保留個人的精神。換言之,“總體的人”是兼具普遍性和個性的人,他們在禮節、道德、呼喊、語詞、動作與儀式中表現普遍性,同時也借著禮節、道德、呼喊、語詞、動作和儀式這種象征性表達確立自我。在古式社會,“總體的人”最典型的代表當屬庫拉(Kula,一種大型夸富宴)中的首領,“他們均以一種高貴的方式行事,表面上十分地慷慨和謙遜”[5]。在集體參與庫拉活動時,首領個人身上所反映的整個社會的影子——慷慨和謙遜擴散至每個個人。因此個人個個都成為“總體”,“總體的人”也就成了“總體的社會”。至此,我們明白莫斯是通過“總體的人”的概念彌合了社會和個體之間連續性的斷裂。
古式社會中,人因參與禮物交換(交流)具有了總體性,社會因夸富宴呈現也具有了總體性。因此在某種意義上,總體性成了社會性的另一種表述,而人也成了社會的另一種概念。莫斯借助對禮物中人、物、靈魂的共融考察,闡明了其“神圣并不外在于世俗,正如社會或集體并不外在于我們每一個個人[8]”的思想。這種對個人和社會關系的看法,實際上與查爾斯·霍頓·庫利的“一體兩面觀”十分接近,即“‘社會和‘個人并不代表兩個事物,而只表示同一事物的個體方面和集體方面”[9]。莫斯對涂爾干的“學術搭建和修補工作”首先便體現于此,即突破導師人與社會的二元對立論,走向人與社會的一體兩面觀。此外,《禮物》中很多類似夸富宴形式的禮物交換表明了交換和交流不僅發生在個體之間,同樣也發生在集體、氏族和部落之間。因此禮物交換作為總體的社會事實,不僅表現在宏觀的社會層面上,也表現于微觀的日常生活中。莫斯借助夸富宴找到了不局限于個別社會現象而存在的“總體性社會現象”,這是對其導師用個別社會現象——“集體歡騰”解釋社會事實的突破。而無論是“總體的人”的學術建樹,還是“總體的社會”的理論突破,莫斯都在用禮物交換表達著自己對古式社會傳播交流形式的羨慕與稱贊。
四、結 語
從鮑德里亞的向導到齊美爾的知音再到涂爾干的學生,禮物觀讓莫斯收獲了很多人生角色。然而洗盡鉛華,他最想呈現給世人的或許一直都是學術研究中的“他者”身份。以歐洲大陸現代社會中的一員“他者”,審視美、亞大陸古式社會的人與交換,從而揭示“他者”所在社會交流危機的真正病因——內容象征意義的缺失、連續互動鏈條的斷裂以及主體完整人性的分離。社會化媒體時代,當我們沉浸在微博呈現的社會事實中,當我們遨游于微信構筑的人際關系中,當我們徜徉于微視頻營造的快感體驗中,我們或許很難體會彼得斯所言的“交流的無奈”。但當以“扶不扶”為典型的人情冷漠案例聚集輿論時,我們卻無法忽視這案例背后深藏的現代交流和信任危機。正如彼得斯所言,交流是公共輿論的管理,也是語意之霧的消除,是自我固有的障礙,也是他者特性的揭示。面對新媒體時代的“交流的無奈”,作為和莫斯一樣的“他者”,我們若是如他般抱守回歸古式社會的烏托邦幻想實屬不切實際,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從其傳播思想中窺視交流危機的解決方案——在現代社會重塑“總體的人”,從而實現人物混融式的象征交往。
參考文獻:
- (美)彼得斯著.何道寬譯.交流的無奈:傳播思想史[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
- 汲喆.禮物交換作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J].社會學研究,2009(5).
- 劉擁華.布迪厄的終生問題[M].上海:三聯書店,2009.
- 瀟瀟.從象征交換到沉默的大眾——鮑德里亞媒介理論研究[D].廣西師范大學,2007.
- (法)馬塞爾·莫斯著.汲喆譯.禮物:古式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理由[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法)阿芒·法特拉,米歇爾·法特拉著.孫五三譯.傳播學簡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 (德)齊美爾著.林榮遠編譯.社會是如何可能的:齊美爾社會學文選[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 龍俊飛.犧牲作為禮物——讀莫斯的《禮物》[J].西北民族研究,2012(5).
- (美)庫利著.包凡一,王源譯.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 支運波.人類學:巴塔耶通往莫斯的橋梁[J].青海民族研究,2010(10).
- 趙素燕.從涂爾干到馬塞爾·莫斯——社會何以可能——以《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和《禮物》為例[J].長春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1).
[責任編輯:艾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