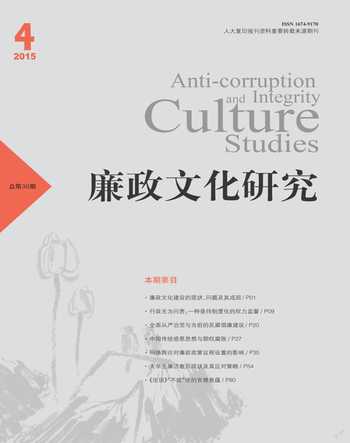抗戰期間我黨反腐敗形勢嚴峻復雜性的政治生態學分析
朱慶躍
摘 要: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不僅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方面發揮著中流砥柱的作用,同時也在實踐中保持著先進性,以使民眾從黨的清正廉潔中看到國家和民族的未來。但是這種清正廉潔現象的保持是非常不易的,因為這一期間我黨反腐敗所面臨的形勢本身是極其嚴峻和復雜的。以當時眾多根據地中的淮北抗日根據地作為案例,運用政治生態學的理論與方法來進行考察,就會發現無論是新舊社會特點并存的權力運行外環境,還是黨的權力運行體系在適應新環境的調適方面,都潛伏著一些誘發權力異化的劣變生態因子。
關鍵詞: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淮北抗日根據地;反腐形勢;政治生態學
中圖分類號:D26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170(2015)04-0060-07
在抗戰時期這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特殊階段,從總體上看黨不僅在民族民主革命的進程中作了重要貢獻,更重要地保持了先進性,實現了自身的發展壯大,使民眾從黨的身上看到了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如在清正廉潔方面,相較國統區“利用抗戰發國難財,官吏即商人,貪污成風,廉恥掃地”,根據地則呈現出“艱苦奮斗,以身作則,工作之外,還要生產,獎勵廉潔,禁絕貪污”[1]1048這一鮮明特色。但如果回歸到當時具體的政治生態環境中,就會發現這種先進性特別是清正廉潔的保持是非常不易的,因為抗戰期間我黨反腐所面臨的形勢本身是極其嚴峻和復雜的,無論是新舊社會特點并存的權力運行外環境,還是黨的權力運行體系在適應新環境的調適方面,都潛伏著一些誘發權力異化的劣變生態因子。本文以淮北抗日根據地為例,運用政治生態學的理論與方法(即將黨的權力運行所處環境狀況分為外環境系統和內環境系統兩種,在此基礎上分析內外環境系統中具體的誘發權力異化的劣變生態因子)考察和分析這一期間反腐敗所面臨的嚴峻復雜性形勢,既可充分認識到這一期間反腐斗爭的艱辛;也有助于增強對當時反腐歷史實踐特征理解的深度,特別是把握相關反腐舉措的演進原由,以此為新形勢下如何有效有序地開展反腐提供一些啟示。
一、新舊社會特點并存的權力運行外環境潛伏著一些劣變生態因子
所謂黨的權力運行外環境,就是指引發、促使黨的權力運行體系構建變遷的外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條件狀況。抗戰時期,各個根據地和解放區所建立時的社會狀況具有復雜性,如有的是在原革命根據地基礎上演化而成,有的是通過對淪陷區的奪取和解放轉化而來,有的處于城市的統治被日本侵略者或日偽或國民黨所控制而鄉村處于黨的領導之下的情形等,這就造成了根據地既有社會主義和新民主主義因素,也有封建性和半封建性以及殖民地性和半殖民地性等舊因素。以淮北抗日根據地的蘇皖區為例,1940年9月劉瑞龍在蘇皖區黨委書記聯席會的報告中,就指出蘇皖區有三種不同的工作環境:抗日進步力量所支配的區、敵偽統治或敵偽力量占優勢的區域以及反共派、頑固派、投降派所支配或他們力量占優勢的區域。相應地,這種新舊社會特點并存的權力運行外環境中,必然潛伏著一些誘發權力異化的劣變生態因子。
(一)經濟層面:私有制經濟的存在為腐敗滋生提供了誘因
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進行抗日,抗戰時期黨對廣大根據地內的私有制經濟采取了保護政策,如除了認可地主階級土地私有制外,還允許和鼓勵資本主義工商業存在、發展。“這個共和國并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并不禁止‘不能操縱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后的緣故。”[2]678為束縛它們的破壞性作用,黨實行了“節制”的政策,使其不能操縱國計民生;但這些私有制經濟的自利性及其所帶來的私有制觀念,直接或間接地侵襲著黨的系統,誘發著腐敗的滋生。正如毛澤東1941年在為《農村調查》所寫的《跋》中指出:“在這個時期內一部分共產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化,在黨員中發生的資本主義的思想,是可能的,我們必須和這種黨內的腐化思想作斗爭”[1]793。
作為黨在敵后所創建的根據地之一——淮北抗日根據地,其內部私有制經濟包括資本主義經濟的存在,同樣也為黨的權力異化現象和行為的滋生直接或間接地提供了重要經濟誘因。如在自利性影響下,一些私有制經濟所有者對黨的干部進行拉籠和腐蝕,使黨的權力在運行中發生“離軌”。1941年豫皖蘇區黨委直屬區區委書記王光宇在《直屬區的鞏固工作》報告中,就列舉了直屬區某鄉的一個保主任兼保委員被地主收買和利誘的現象。當地主抽幾畝地給他種,并答應給他借錢后,一反常態不僅不說地主的壞話,反而說地主的好話。同樣私有制經濟的存在,也為一些干部滋生自私自利腐化墮落的個人主義提供了經濟根源。如這種個人主義一度像傳染病、歪風一樣在淮北抗日根據地黨內軍隊內流行,以新四軍第4師為例曾在數月內犯貪污、浪費、生活腐化錯誤的排以上干部共計六十九名。為此,當時的4師政治部主任、兼淮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吳芝圃在猛烈批判個人享樂主義所造成的危害性時,就明確指出它是“私有財產制度下的產物”,是“建筑在商品經濟所有者(剝削階級)對于商品和金錢的拜物教的錯覺之上的一種思想”[3]122。另外,在私有觀念的影響下,出現了一些在職干部用所謂的“私人積蓄”作本錢做生意,休息養病的干部拿休息費或借一部分資本做投機事業;不少干部要求退伍以獲取撫恤金去經商發財,甚至影響到部分戰士也以做生意為副業。1942年淮北蘇皖邊區公布的《懲治貪污暫行條例》中,對貪污腐敗類型所作的明細化也間接佐證了這些不良現象的存在。如所列舉的八種貪污行為中除了五種屬于直接貪污公款財物外,諸如“買賣公共物品從中舞弊漁利者”、“意圖營利,販禁運或漏稅物品者”、“因職務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4]57-58等三種則屬于將手中權力和公款財物變為“資本”這一類型。在民族統一戰線的背景下,不可能消除私有制經濟特別是資本主義經濟。為此,要克服它們帶來的消極影響,正確途徑只能是構建有效的反腐政治體系。正如毛澤東在這一時期就明確向全黨告誡:“不要把反對黨內資本主義思想的斗爭,錯誤地移到社會經濟方面,去反對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分。我們必須要明確地分清這種界限”[1]793。
(二)政治層面:民主政治實現的不充分為腐敗滋生創造了條件
抗戰時期,黨領導的根據地在政治層面開始了新民主主義憲政模式的實踐探索,以便為保障民眾的政治權利以及如何更好地監督黨的權力尋找一條正確的道路。正如美國學者馬克·賽爾登所指出的:“從政治過渡的角度看,‘新民主主義代表著意義非凡的一步,即邁向產生一個負責的、不貪污的和基礎廣泛的政府,這在中國其他地方或當時整個第三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5]136而如何正確構建和較為成功實踐這種既不同于蘇聯社會主義政治模式,也有別于資本主義民主政治模式的政治制度,需要共產黨人立足于具體國情進行艱辛探索。在這個探索過程中,因一些根據地在這之前長期處于專制統治的環境,以及黨自身民主理論準備不足和對土地革命時期所獲政權建設經驗教條化的運用等諸多因素影響,難免會出現一些差錯,甚至某些環節的不成熟性還會起到“適得其反”效果,特別是對于黨的反腐敗來說。
以這一期間的淮北抗日根據地為例,在新民主主義憲政模式實踐中也一度出現了民主政治實施不充分的弊端,從而為腐敗的滋生提供了政治層面的可能性。“我們民主建設有了許多成績,……但以新民主主義的尺度衡量他,還有許多缺點。”[6]273對于這種民主政治實施不充分的表現,在1943年2月淮北蘇皖邊區第二次民政會議上劉瑞龍就給予了具體的闡釋,如認為它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即政府與各階層關系的脫節、政府內部黨員與非黨員關系的脫節、政府機構運用及上下級關系的脫節。而至于危害性方面,劉瑞龍特別強調它容易造成政府的孤立和權力異化現象的滋生,因為“沒有老百姓對政府的嚴格監督”[6]275。民主政治實施得不充分,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歷史的因素,又有現實的因素。歷史的因素,在當時淮北根據地新民主主義憲政模式實踐中影響最深的就是尚未徹底根除的封建社會保甲制和官僚制的殘余。“淮北各級政權機構的民主改造已進行了四年,但大部分的基層政權尚未加以徹底改造,舊的建立在家長專制基礎上的保甲制的統治機構尚未被徹底打破。”[7]146“現在官僚主義在抗日民主政權中間還沒有成為支配性的地位,但是已有很嚴重的現象。”[7]64保甲制的思想在一些干部頭腦中的存在,容易造成“以保甲制的工作作風來運用代表制,致不能充分發揮代表制的作用”[7]43-44;而封建主義官僚制的影響,在政權本身建設上“使民主改造變成了有名無實,只做到開會選舉,不問他的成份是否符合于 ‘三三制,選出后如何做工作,不去問它”[7]62-63,這樣最終惡化了民主政權的性質,使其變質為官僚政權而不是群眾的政權。而現實的因素,集中表現于新政權建設中的一些錯誤傾向和部分環節操作的不成熟性。如在民主選舉層面,出現了兩種錯誤性態度:一種錯誤就是忽視“選舉”,將它視為可有可無之事。這導致了根據地各級參議會遲遲不能依法正常開會和改選。為此,當時淮北區黨委副書記劉子久就指出我們工作中所產生的一系列毛病就是來自于這一根本性缺點,即“在我們的干部、甚至負責干部中,對于召集參議會不夠重視”[6]303。另一種錯誤在于雖認識到“選舉”在民主實踐中的作用,但存在著過于”重形式輕內容”的弊端。就如1943年8月《淮北蘇皖邊區行政公署訓令——關于繼續開展民主運動,改造基層行政的指示》中所列舉的諸如實施中與民眾生活和中心工作的脫離,或者如表現在領導上用工作干部代替選舉委員會、宣傳動員上的不切實不深入、只知完成選舉手續而不注意改選效果,重人員改選而輕組織改造和作風整頓等缺點。因此,在這種情境下民眾參與變成了一種服從、強制性參與,而不是真正的信念、分配型參與;同樣所建立的政權機構相應地更多呈現出虛假的“人民性”而缺乏有效的監督,腐敗現象和行為的滋生也就在所難免。
(三)文化層面:舊思想舊文化的劣根性對部分黨員的理想信念造成了沖擊
從思想文化層面來看,腐敗現象和行為既是腐敗意識的外化,同時又加劇了這種腐敗意識的惡化。抗戰時期,根據地滋生的腐敗現象和行為,如從黨的權力運行外環境中尋找原因,除了經濟、政治、微觀的社會等層面所存在的劣變生態因子之外,社會文化中的一些劣變生態因子也是滋生腐敗現象的深層次因素。盡管這一期間黨也著力實行根據地由舊社會向新社會的轉變,但是轉變本身是一個長期復雜性過程。在這一轉變過程中舊社會的因素如舊思想舊文化的劣根性,也一定程度對部分黨員理想信念的樹立造成了沖擊,從而為黨的權力異化現象和行為的滋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誘因。
以當時的淮北抗日根據地為例,在未開展普遍的整風運動之前和其他根據地一樣黨員干部中也存在種種違反黨性的不良傾向。單純從思想文化層面尋找發生源,這些不良傾向固然與當時根據地周圍的反動階級如國民黨反動派和汪偽政權的腐朽文化滲透有很大關系,但是不可否認也與一些黨員干部頭腦中根深蒂固的舊思想舊文化的劣根性沒有徹底拔除密不可分。這些不良傾向最典型的體現為一些黨員干部中盛行的自私自利腐化墮落的個人主義(當時的4師政治部主任、兼淮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吳芝圃將其具體分為厭倦主義、享樂主義、英雄主義、自由主義等八種傾向)和官僚主義(當時淮北區黨委副書記劉瑞龍揭示淮北區政府中盛行擺官架子、不接近群眾,制定計劃的主觀隨意性,上下級關系上的欺下瞞上、官官相護等四種類型),以及部分軍隊中滋生的軍閥主義(當時淮北區黨委書記鄧子恢將其概括為不尊重政權、對部隊的私有觀念和私人干部政策等五種表現)。上述無論哪一種傾向無不帶有舊思想、舊文化弊端的烙印。如個人主義無論是何種表現它們的共同點就是“在經濟上的私有觀念,在道德上的壓榨人奴役人的傳統思想”[3]133;官僚主義的根源就是“過去封建階級奴役人民、壓迫人民、鄙視人民、看不起人民,等級制度、反對民主思想的反映”[7]64;軍閥主義暴露出我們部隊中一部分干部“他的過去長期在舊社會、舊軍隊生活中形成的舊思想——貴族地主階級的思想與軍閥思想并未徹底改變”[3]56。而這些劣根性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當時淮北抗日根據地黨員干部的階級基礎比較差這一狀況所決定的。如1943年2月淮北蘇皖邊區第二次民政會議上,劉瑞龍就指出當時黨員干部中出現不民主思想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出身差。“分析我們干部的出身,一種是舊政府的工作人員,一種是學生,一種是工農出身的干部。舊政府人員帶來了官僚習氣;學生小資產階級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作威作福;工農干部的報復心理、向上爬的落后觀念。因此,很容易接受官僚主義思想或方法。”[6]276同樣1943年6月淮北區黨委所下發的《關于反對目前黨內嚴重存在著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傾向的決定》中,也指出當時蘇皖邊區的干部主要有兩個來源,即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與半知識分子出身,以及地主階級出身。而這種階級基礎差的狀況,從客觀上誘發了干部中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不良傾向的產生。
(四)社會組織層面:群團組織獨立性和人民性的不足削弱了社會制約權力的效果
從黨的權力委托源看,它不僅來自于黨內的黨員群眾和各級黨組織,同樣黨外的廣大民眾及其組織也是重要來源。這就決定了除要理清和處理好黨內各種關系之外,黨還要處理好黨與群眾及其組織之間的關系。而后一種關系具有雙向性,即黨對于群眾及其組織來說處于何種地位、作用;群眾及其組織對于黨來說置于何種地位、作用。從反腐視閾看,這兩個層面能否正確回答和和解決好至關重要。因為第一個層面涉及到黨是群眾及其組織的包辦者還是利益的體現、維護者的問題,關乎黨的權力內容的“失真”與否;第二個層面涉及到群眾及其組織是黨的完全依附者還是獨立者的問題,關系著黨的權力行使中“失控”、“失監”與否。
面對民族危亡,不同于國民黨的“片面抗政”方針,抗戰期間黨始終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其中一個典型做法就是在廣大根據地領導和幫助群眾建立屬于自己的組織,諸如農民抗日救國會、工人抗日救國會、婦女抗日救國會和青年抗日救國會等各種類型的群眾團體。正如鄧小平指出,它是“我們指導根據地群眾運動應掌握的規律”[8]67。但是由于這一時期階級斗爭服從和配合著民族斗爭以及根據地環境的復雜性等因素的影響,黨和根據地政權在領導這些群團組織中一度出現了一些錯誤的思想傾向。而從反腐視閾看,這些錯誤思想和傾向不同程度地損害了黨領導下的群團組織的獨立性和人民性,相應地也削弱了社會制約黨的權力運行的效果。以當時的淮北抗日根據地為考察中心,就可以獲得明顯的佐證。如在處理群眾組織與政權和黨的關系上,曾出現了忽視兩者在性質、功能上的原則性區別,相互替代的錯誤傾向,即把前者變成后者的附屬物,否認前者的獨立性,最典型的就是根據地一度盛行所謂的“先鋒主義”;或用前者替代后者,包辦后者工作,最經常的就是在根據地出現了農救會替代政府機關進行罰款、抓人、游街等行為。另一種錯誤傾向就是在領導和幫助群眾組織發展方面,黨與政府要不采取旁觀或漠不關心的官僚主義態度,要不就是干涉過度而忽視群眾組織自身發展的規律,致使群眾組織自身建設上出現了一系列問題。當時淮北民主抗敵聯合會主任李晨就揭示根據地的一些地區黨和政府在幫助群眾組織發展方面,出現了諸如有湊數目字、嚴重的家長制作風、包辦代替等反民主的傾向[9]169。同樣1944年淮北區黨委書記鄧子恢在《轉變我們的群眾工作方式與作風》的講話中,就根據地內一些群團組織發展中出現的黨化、政府化、軍隊化、非勞動化、非群眾化與非地方化等錯誤現象,也給予了嚴厲的批判。上述種種錯誤傾向對黨的權力規范有序運行的影響,借用1943年5月《淮北蘇皖邊區黨委關于加強各種群眾團體工作的決定》中的一段話就可以獲得清晰的認識:“我們的各種工作之所以不活躍,推不動,工作人員貪污腐化的嚴重,各種工作干部的缺乏等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近來各地群眾團體的日加削弱,群眾工作的無形停頓甚至取消而造成。”[9]225
二、在適應新環境的調適中黨的權力運行體系內部隱藏的“雜質”
所謂權力運行的內環境,就是指黨的權力運行體系內各子系統,如政黨文化的政治社會化、政治制度、政治關系等層面協調運行的狀況。抗戰這一時期,由于黨的合法性被承認以及民族戰爭所賦予的特殊性任務,使黨必須對土地革命時期形成的權力運行體系進行調適。在調適過程中,因對環境狀況特征認識的不徹底和實踐本身的不充分,不可避免隱藏一些“雜質”,從而對權力規范運行起到了破壞和妨礙作用,直接或間接地誘發著腐敗的滋生。
(一)對內政治社會化一度的輕視和缺失導致了一些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存在
在探討這一時期黨的權力運行過程中為何存在非無產階級思想和意識,人們經常將其歸結為黨處于一個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占主導地位的外環境中,而環境中存在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又通過統一戰線的載體和通道,不斷地對黨的肌體進行影響和滲透。這點確實存在著,也不容否定。但如從黨本身來看,還直接與這一時期黨在思想建設環節上即內政治社會化方面一度的薄弱或缺失有關。從反腐視閾看,在錯誤思想意識的指導下黨的權力運行中不可避免滋生出一些腐敗現象和行為。以當時的淮北抗日根據地為例,這種內政治社會化的輕視和缺失曾一段時間內表現在黨、政權和軍隊等各個方面。如黨內,1943年6月淮北黨委在《關于反對目前黨內嚴重存在著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傾向的決定》中,就強調黨員中間特別是干部中間存在著諸如貪污腐化、功臣思想、權位觀念等非無產階級意識,在主觀方面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干部教育特別是思想教育的缺乏”[3]113。政權內,1943年2月淮北蘇皖邊區第二次民政會議上劉瑞龍就認為政府中干部不民主現象滋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干部中民主教育不夠,一知半解,缺乏有系統的認識”[6]276。同樣軍隊內,1941年8月在《關于四師進入淮北后之各方面工作布置報告》中,彭雪楓就指出由于在整訓工作中不去進行雜務人員的教育,從而造成了部隊中一些貪污現象的滋生;在部隊中對干部不注意紀律教育,結果一些部隊渙散。
除這一期間抗日形勢的緊迫性等客觀原因之外,單純從內政治社會化的施動者、受動者以及社會化過程等內在要素看,造成內政治社會化一度輕視和缺失的原因也是錯綜復雜的。同樣以當時的淮北抗日根據地為考察對象,一是與施動者的缺乏有關。在淮北抗日根據地內,雖然經過上級政治機關的培養和訓練,輸送了大批抗大的干部,但是由于戰爭中的傷亡,再加上政工干部的本身培養也不是一日之功,這就導致根據地許多地區在思想政治工作中遇到的主要的困難“首先是政治干部的缺乏,特別是有經驗的干部”[10]20。二是與受動者的吸納方面“重數量輕質量”傾向有關。如1941年5月至1943年底,淮北抗日根據地黨組織處于大發展時期,黨員有24000多人,但是由于“重數量輕質量”這一錯誤傾向的影響,導致了一些不純分子混入黨內。1945年7月邊區組織工作會議上,淮北區黨委組織部部長謝邦治在所作報告中列舉的一組數字足以反映問題的嚴重性。如泗南、泗五靈鳳、盱鳳嘉、淮泗四個縣鄉級干部281人中,雇、貧農120人,占43%弱;中農129人,占45%強;富農地主商人32人,占12%。平均動搖的占60.7%,貪污腐化的最高分比達到98%,參加封建團體與政治派別者平均70%上下[3]308。三是與政治社會化過程中出現的一些錯誤傾向有關。以淮北抗日根據地所開展的整風運動來看,在前期就存在著過于形式化而沒有深入地開展下去。1943年《關于中央整風新指示及華中局補充指示的傳達》中,彭雪楓就指出在淮北地方黨和主力部隊的整風中存在著專整下級不整上級,或專整上級不整下級;專整別人不整自己,或專整自己不整別人;專整老的不整新的,或專整新的不整老的等不正確認識。1943年淮北區黨委下發的《關于加強整風學習的決定》中,強調整風運動雖然在根據地開展了一兩年,但淮北黨的整風學習中仍然存在著把“整風第一”的號召視為一句口號;整風中只知反省現象,不從思想上尋找根源;整風領導主觀隨意性大;組織領導和思想領導均表現無力等嚴重缺點和偏向。可見,這些錯誤傾向的存在削弱了內政治社會化的效果,相應地黨的權力運行中特別是權力形式主體頭腦中所存在的一些非無產階級思想不可能獲得徹底的根除。
(二)黨政關系上一度出現的“左”右傾錯誤造成了拒腐防變能力的下降
黨政關系表面涉及到黨的組織權力體系、政權的權力體系兩者之間的關系,其背后蘊含著如何對民眾的權利進行維護和保障。相較于黨的組織權力體系,政權的權力體系是民眾權利的直接授予和委托方,這就決定了如果黨的組織權力體系對政權的權力體系的過于干涉,將會造成對民眾權利的侵襲,助長政權中黨員干部腐敗現象的滋生;而同樣如果黨的組織權力體系不對政權的權力體系進行必要的指導和監督,則又會出現政權的權力體系對民眾權利的虛假代表和直接傷害。可見,從反腐視閾看要保障黨的權力有效有序運行,在政治關系層面必須構建和諧而有張力的黨政關系。
抗戰時期由于環境的復雜性,以及非國內因素(主要為蘇聯和共產國際的一些錯誤指導)和黨以前所經歷的慘痛性教訓等影響,使得黨在解決黨政關系問題上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一度出現了“左”右傾錯誤。以當時的淮北抗日根據地為例,這些錯誤傾向重點體現在“三三制”的統一戰線政權中是否需要黨的領導、如何實現黨的領導這一方面。如“左”的傾向,主要由于害怕實行“三三制”后政權的性質變異,以及受“以黨治國”錯誤觀念的影響,在“三三制”政權的人員構成上采取黨員包辦的做法;在黨的領導權認識上將其解釋為“黨權高于一切”,用黨權替代行政權;在行政決策上求簡單避復雜,不重視民主程序[8]10-11。1943年2月淮北蘇皖邊區第二次民政會議上,劉瑞龍所列舉的根據地的一些地方政府內部黨員與非黨員的關系方面存在著諸如黨員遇事不與黨外人士商量,平時不征求非黨員干部對黨員的意見,只相信黨員而不相信黨外人士的話,不尊重行政系統,黨員不遵守法律搞特殊、行政會議召集很少等缺點,就是這種“左”傾錯誤的具體化反映。這種傾向的實行,表面似乎使黨牢牢領導和掌握了“三三制”這一統一戰線政權,結果卻造成了黨的兩種權力體系(組織權力體系和政權權力體系)運行的混雜,以致彼此不能按照各自的規律有效有序運行;同時,這種傾向也使黨的權力脫離了群眾的監督,產生了黨員墮落腐化的危險。正如鄧小平在1941年《黨與抗日民主政權》一文中,所指出的“‘以黨治國的國民黨遺毒,是麻痹黨、腐化黨、破壞黨、使黨脫離群眾的最有效的辦法”[8]12。右的傾向,或因沒有充分認識到黨的領導在政權問題上的重要性,或畏懼政權工作的繁雜性,而放棄和輕視了“三三制”政權的領導權。如1940年7月在《關于整黨建黨的幾個基本問題》的報告中,吳芝圃就指出豫皖蘇邊區的一些地方黨存在著對各級政權領導不堅強、不正確,其中最明顯的表現之一就是犧牲黨的策略和群眾利益,對于地方士紳以行政上的位置爭取他們對黨表面的暫時的好感,結果使鄉保甲基層政權落在不積極抗日并且危害大多數群眾利益的地主、豪紳、地痞流氓的手里。可見,此種傾向使黨的行政權力容易被地主和資產階級所掌控,從而造成權力的異化,成為壓制和剝削人民的工具。
(三)經濟管理制度建設的一度薄弱留下了滋生腐敗的制度漏洞
經濟領域是腐敗最易滋生的地方。抗戰時期根據地內滋生的腐敗現象和行為,也有許多直接就發生在黨領導下的政府經濟管理部門和合作社企業中。而造成這些經濟管理領域滋生腐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還在于制度層面特別是相關經濟管理制度的薄弱。如在財政收支制度上的不統一,造成了許多根據地的機關部隊團體自收自用現象的發生,甚至出現了強占強征或強募財物;一些機關部隊團體長期不建立預決算制度,誘發了嚴重的貪污浪費、入不敷出現象;會計、審計制度的不健全,導致偽造或虛報收支項目等以權謀私現象的發生;金庫管理制度的不完善,致使監守自盜、擅移公款現象的頻發等。上述經濟管理制度上的漏洞,在當時的淮北抗日根據地一段時間內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如1942年劉瑞龍在淮北地區第二屆參議會的報告中,就列舉了因沒有建立統一財政預決算制度,致使一些地方財政支出不節省,浪費現象嚴重,淮泗政府辦公費一個月用了900元,泗五靈鳳一個月用了2300元[6]226。1943年,張震就揭露在淮北根據地的部分干部中滋長著一些不良傾向,其中嚴重的表現在對經費對公物的貪污浪費上,如虛報賬目,與商人通謀,假造發單,盜買糧食或以高價收買物品,私要商人饋贈東西,以公款與商人合股私做生意等[3]138-139。可見,這些貪污浪費現象更多地是鉆了經濟制度的空子。
抗戰期間,包括淮北抗日根據地在內的許多根據地在具體制度建設方面特別是相關經濟管理制度的薄弱狀態,既與當時斗爭任務的緊迫性致使其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有很大關系,但是不可否認以下兩個方面也是重要的因素:一是與黨的領導體制上所實行的“分權式”體制有很大關系。這種體制導致了各根據地機關部隊團體擁有過大的經濟管理權力,也造成了經濟管理制度的極不統一和混亂,使貪污浪費者有機可乘。正如1942年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毛澤東就明確指出“經濟和財政工作機構中的不統一、鬧獨立性、各自為政等惡劣現象,必須克服,而建立統一的、指揮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貫徹到底的工作系統”[1]895-896。二是受“輕經濟重革命”錯誤思想和認識的影響。當時一部分同志把從事經濟工作與從事革命工作完全割裂開,認為前者不是革命工作,經濟工作沒有革命意義。對黨安排其從事經濟工作,要不就是以各種理由盡量推辭或不服從,要不就是敷衍了事。如當時淮北軍區三分區供給部長任秀生通過對淮北軍區獨一團的調查,發現48名供給干部中11人不安心,2個要改行,4個無興趣,而分析不安心的原因不外乎地位觀念作怪;對供給工作重要性認識不足,認為做供給工作吃不開等等[11]223。可見,在這種錯誤思想和行為的影響下,加強經濟管理制度建設基本上不可能。另外,這也造成了黨內經濟管理人員的短缺,而相應地給一些將經濟管理工作視為發財捷徑的不法分子提供了便利。也正是針對此種情況,1941年陳云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黨員參加經濟和技術工作的決定》這份重要文件。在此文件中,就要求全黨同志務必了解“各種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從而糾正那些對革命工作存在狹隘了解或認為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沒有嚴重政治意義”等錯誤觀點;同時指出所有黨員都必須“無條件的服從黨對于他的工作分配”,以根本杜絕“不愿參加經濟和技術工作及分配工作時討價還價的現象”[12]95。
參考文獻:
[1]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豫皖蘇魯邊區辦公室,安徽檔案館.淮北抗日根據地史料選輯:第四輯[Z].合肥:安徽省檔案館出版,1985.
[4] 劉宋斌.中國共產黨廉政反腐紀事(1921-2009)[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9.
[5] (美)馬克·賽爾登.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M].魏曉明,馮崇義,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6] 豫皖蘇魯邊區黨史辦公室,安徽檔案館.淮北抗日根據地史料選輯:第二輯第一冊[Z].合肥:安徽省檔案館出版,1985.
[7] 豫皖蘇魯邊區黨史辦公室,安徽檔案館.淮北抗日根據地史料選輯:第二輯第二冊[Z].合肥:安徽省檔案館出版,1985.
[8] 鄧小平文選: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 豫皖蘇魯邊區黨史辦公室,安徽檔案館.淮北抗日根據地史料選輯:第三輯第一冊[Z].合肥:安徽省檔案館出版,1984.
[10] 豫皖蘇魯邊區黨史辦公室,安徽檔案館.淮北抗日根據地史料選輯:第一輯第一冊[Z].合肥:安徽省檔案館出版,1985.
[11] 豫皖蘇魯邊區辦公室,安徽檔案館.淮北抗日根據地史料選輯:第五輯[Z].合肥:安徽省檔案館出版,1985.
[12]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三冊[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責任編校 王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