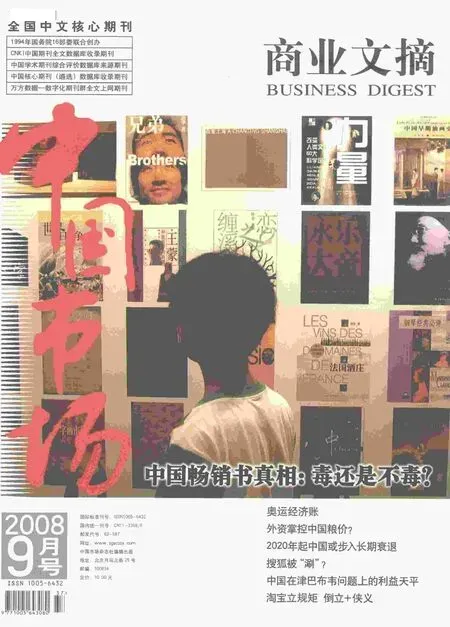視覺文化時代:學院立場與公共責任
李芳
[摘要]文章從信息社會發展的趨勢出發,主要結合當代高校美術館所處時代的數字化特質,引據博物館學、傳播學、教育學的經典文獻,結合當下論述高校美術館在學院立場與公共責任的維度上,如何實踐數字化教育的可行性研究。
[關鍵詞]視覺文化時代;美術館;數字化;教育功能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70161
視覺文化時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數字技術、新媒體、互聯網等領域的發展突飛猛進;信息傳播、大眾文化、民主意識等方面的巨變,匯集為洪流般泛濫的視覺信息。作為兼有文化場域和公共空間特質的美術館,特別是教育功能上同時擔負專業建設與公共教育的高校美術館,如何在蕪雜的信息中,燃起精神明燈,吹響人文號角;在數字化教育功能上彰顯學院立場與公共責任,重新思考其存在的意義及形式,逐漸成為亟待加強研究并給予解決的重要課題之一。
1美術館發展進程中的“物”與“人”
作為博物館中的一支,我們首先從從屬關系的層面上來看博物館。“博物館的物是物化的觀念,物的博物館化過程就是賦予物以意義的過程。博物館的本質是社會需要的、由博物館機構反映出來的人與物的結合。”[1]在這個賦予意義的過程中,作為“精神殿堂”的博物館,孰“物”孰“人”的指向,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概念,而是重心或有不同。
回看最早的博物館——繆斯神廟:在亞歷山大大帝對于物的搜集為前提條件下,建立起的亞歷山大博學園,可謂是物的聚集地。它的產生以實物為基礎,諸多活動又圍繞著“物”進行,從物的收集、保存、展示到研究,其主要任務均偏重于“物”。由此推之,博物館顧名思義實物性是主要特征,其中的“物”典型且重要。
從1961年到1974年,從“一個以研究、教育與欣賞為目的,來保存以及展示在文化及科學方面具有重要價值的對象的機構”到“不追求營利,為社會和社會發展服務,而且是向公眾開放的永久性機構。它為研究、教育和欣賞的目的,對人類和人類環境的物質見證進行了搜集、保護、研究、傳播與展覽”。國際博物館協會相隔13年的兩條關于博物館的定義,在“物”與“人”的訴求上有了重要轉向,后者更加強調博物館的公共性、服務性、非營利性和以人為本的精神。
對此,臺灣博物館學者劉婉珍提出了“博物館就是劇場”的概念,“整個博物館就是一座穿梭時空的記憶劇場……協助觀眾找到適當的感情去創造劇場的精彩演出,正是博物館的責任所在。”[2]無論臺上臺下,劇場的主體是人,“人”的地位開始提升至中心位置。作為博物館的一支,美術館亦應以人為本,將對“人”的研究提到與“物”平等的水平上,并致力于研究“人”與“物”的關系。
尤其是在信息技術的狂飆驅動下,美術館被置于場館現實空間與數字虛擬空間的交叉路口。數字技術的“預言家”尼古拉斯·尼葛洛龐蒂曾經在其經典著作《數字化生存》中,用“沙皇退位,個人抬頭”洞幽察微地指出了數字化所推崇的注重個體、突出個人的特質。可見,美術館在數字虛擬空間中,若要將收藏、研究、展示、教育、交流五種基本功能貫穿始末,須將終極價值鎖定為“人”。這是一種適時適勢的調整。
2時代轉向與語境轉換所引發的美術館連帶效應
視覺文化時代的特征是現代科技的高速發展和大眾文化的主流地位。此時的信息傳播以信息技術為依托,以文字、聲音、圖像、影像等多種媒體為載體,具有實時性、交互性、體驗性的特點。加之“大數據”熱潮方興未艾,“數字化”、“大眾化”從而成為其基礎。
這其中所謂的“數字化”,是隨著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的不斷發展,頻繁出現的新概念。數字化是信息社會的技術基礎,是利用計算機、通信、網絡、人工智能等技術把聲、光、電、磁等信號轉換成數字信號,或把語音、文字、圖像等信息轉變為數字編碼,用于傳輸與處理的過程。“數字化關系著人類的生存”[3],同樣是尼葛洛龐蒂在《數字化生存》中的經典語錄。它清晰描繪了數字科技為人們帶來的種種沖擊和其中值得反思的問題。作為上層建筑的美術館,同樣經歷著數字化進程的構建與發展,并已然是其發展的必然方向。
綜合看來,美術館的數字化進程其實是一個由數字化信息、數字化信息的管理、運輸和提供利用組成的整體,幾方面相互依存共同完成數字化信息建設的高密度存儲、快速傳輸和無地域、無時限資源共享的功能;并通過專業知識系統、組織結構系統、標志功能系統、瀏覽功能系統、導航功能系統和視覺展示系統的內容搭建,最終實現以受眾為中心、以數字化信息資源服務為訴求的服務模式。
具體而言,美術館的數字化建設主要包含兩個層次:一是將現代信息技術引入到美術館的收藏、研究、展示、教育、交流等功能型工作及日常管理中,如美術館信息網絡的構建、針對美術館不同工作領域開發的各類應用程序、導覽系統以及陳列展示中所使用的各類信息化展示設施等;二是建成以傳統展覽為基礎的“數字美術館”,以美術館展品、藏品所負載和蘊含的歷史、文化、科技等信息為收藏、展示的主體,并借助網絡等信息傳播渠道對受眾進行傳播、發布和推廣。
3數字化教育功能的文化堅守
“信息越豐富,就會導致注意力越匱乏……信息并不匱乏,匱乏的是我們處理信息的能力。”[4]的確,面對如此浩瀚的數字化信息海洋,尤其是視覺文化時代的日漸膚淺與失度的奇觀化傾向,作為“終身教育課堂、激發思維與創造才能的場所”[5],高校美術館在貫徹教育使命之時,亟須在學院立場和公共責任的維度上有效地引導受眾,以高揚人文精神,增強文化自覺意識。
31數字化教育何為
作為學府型美術館所承擔的教育功能,是當代美術教育的一種呈現形式,它既應扮演提升本校學生的健全人格、陶冶人文情懷與修養的角色,也應扮演提升校園之外的國民素質的角色。
如果歷史為縱軸,技術水平為橫軸,那么,教育形式的變遷則主要依托于社會技術背景的變革。從最早的教育形式,師生之間以口耳相傳的“傳幫帶”完成知識的傳遞;到依托于印刷術的發明以及人類工業社會的進程,新載體書籍的誕生與普及,促使教育變革而建立學校……得益于信息技術的推動與發展,數字化成為傳播知識的新形式并面臨著必須不斷更新的趨勢——利用信息時代的諸多先進科學技術,在自由瀏覽、實時交互、臨場體驗等方面對自身教育功能的數字化延伸,進行有益的探索與嘗試,這是其適應美術信息傳播新語境的潛在要求。
32學院維度上的數字化教育
“數字時代的到來給我國高等教育帶來新的挑戰和機遇。培養受教育者的終身學習能力是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務,信息素質教育則是培養受教育者終身學習能力的重要途徑。”[6]“信息素質教育”主要是以培養學生信息意識、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為宗旨的教育。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數字時代從信息受眾的需求出發,在提升受教育者文化辨識能力的同時,提供其多樣的思維路徑,顯得尤為重要。
數字化語境中,高校受眾對于信息的需求處于增長態勢,受教育者對于信息需求主要表現出及時性、專業化和個性化。背靠學校現有資源的高校美術館,更要作為一個開放的空間,放棄單向的傳導方式,讓受眾表達訴求,去了解他們的訴求。一方面,采用以計算機技術、通信技術和網絡技術為核心的信息技術對美術信息資源進行存儲、檢索與傳遞,以實現資源共享,這樣,每一位受眾都有可能得到全面系統的、與自己需求相關的信息,且不受限于時間、地點的制約;另一方面,在開展數字化教育的過程中,不能只是教育者向受教育者的單向傳遞,而是雙向交流,互動影響,使受教育者在交流合作中提高能力,以應對知識含量的激增,學科的交叉滲透。
33延伸開來的高校美術館“信息素質教育”
在植根于本校之外,長久受惠于當地文化傳統與現實惠給的高校美術館,在一定程度上著眼社會,反哺社會,是其應有職責之一。高校美術館在數字化教育建設上,更需要實施以培養信息意識、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為宗旨的“信息素質教育”,可以分別稱之為信息理論教育、信息能力教育和信息道德教育。
首先,信息理論教育可以使之確立較強的信息價值觀念和從信息角度觀察問題、解決問題的思維習慣,使其掌握一定的信息科學思維方法和信息研究方法,從而具備強烈的信息意識;其次,作為信息素質教育的主要方面,信息能力教育的重點在于培養受眾尋求信息和解決信息問題的能力,提高公眾的信息能力將有利于促進開放式信息思維的形成;最后,信息道德教育主要培養受眾的信息道德意識與道德責任感,培養其判斷、選擇信息的能力和道德自律精神。這樣,高校美術館在加強社會橫向聯合的同時,就多方面拓展了功能型教育,成為社會集體經驗的締造者以及學校教育的第二課堂。
4結論與展望
在奔涌向前的數字化洪流中,高校美術館不僅亟須深入推進數字化教育,借助于科技手段在技術、設施層面上進行更新與改造,而且作為時代進步和社會發展的特征,構建起屬于自己地域或族群的歷史記憶、文化經驗與意識形態。作為一個聯結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載體,高校美術館在兼顧學術堅守與追求、公眾關懷與教育方面將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這同樣適用于在數字化教育功能領域中不斷探索而行的高校美術館。
參考文獻:
[1]中國博物館通訊[J].1994(11):15.
[2]劉婉珍博物館就是劇場[M].臺灣:藝術家出版社,2007:26
[3]田小平,等數字博物館研究與實踐:2009[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156.
[4]涂子沛大數據[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86
[5]胡俊博物館縱橫[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9:1
[6]馬春燕數字信息資源開發與建設[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