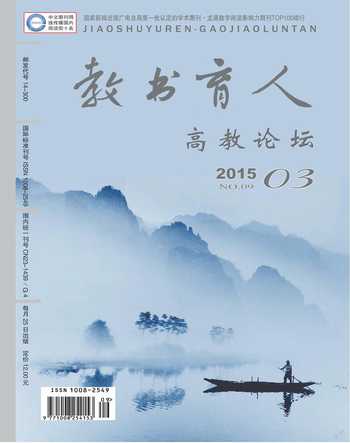人與文化關系中的教育內涵
趙清陽 趙聰 趙彥宏
一 內涵探析
(一)人的內涵
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人是通過實踐自覺解放自我的主體。人的內在生命物質本體與特定的大腦意識本體構成整體的自然人。自然人通過勞動關系構成一個完整的社會關系,形成系統的外在矛盾關系,“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不論是自然人還是社會人,都是通過人的內外矛盾關系形成自我解放的主體矛盾關系。
教育學對人的理解有以下幾點:第一,人是一種存在的可能性;第二,人具有自覺能動性和自主創造性;第三,人具有發展的本質;第四,人具有歷史性和現實性。綜合以上觀點,筆者認為人作為人的存在具有以下特征:(1)存在的絕對性。人的存在具有絕對的價值,是一切價值的基礎和依據。(2)存在的意識性。人的意識性正是人區別與動物存在的本質之一。“意識性”的存在是指其方式和意義是受意識指引的,而非感覺,是人由可能性變為現實的先決條件。失去意識性,人就失去了歷史,失去了未來,失去了生命連續性。(3)存在的獨特性。世界上沒有兩個完全相同的人,這種獨特性不僅表現在身體上,而且表現在思想精神和行為習慣上。(4)存在的文化性。人具有雙重生命,即生物生命和文化生命,沒有文化生命的人與動物無異。人之所以為人,是生物生命與文化生命的協調統一。(5)存在的語言符號性。人的存在也是一種語言符號的存在,因為無論是意識,還是文化都表現為一種語言符號的形式。(6)存在的時間性。人的存在是一種時間性的存在,而不是一種空間性的存在。這種時間性說明了人既是歷史中的人又是現實中的人。
若給“人”下一個定義,筆者認為所謂人就是在自我意識的支配下,通過實踐活動,自覺地發展自我并創造相應的文化和語言符號,使其由自然人成為社會人的獨特生命存在。
(二)文化的內涵
在西語中,“文化”一詞最早源于拉丁語cultura,其詞根colere有耕作、種植、飼養之意,是指人類通過勞動來獲得成果。到16世紀才逐漸演變為被栽培、培育、有教養以及文化等意義。首次給文化下完整定義的是愛德華·泰勒,他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定義:“文化是一個復雜的總體,包括知識、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人類在社會里所得到的一切能力與習慣”。在古漢語中,“文化”最早見于西漢劉向的《說苑》中,其含義是文治和教化。因此,無論在西語還是在漢語里,文化都表示人類有意識地進行社會實踐的成果和人類社會實踐所體現的人類思想的含義,而且這種人類思想體現在人類生活的整個環節和各個領域,它也必然對后來人和其他人產生指導和教化作用。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認為,“廣義上的文化是指人類在實踐中所創造的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的文化專指人們的精神創造及其結果”。正如上述泰德的文化定義,是特定社會中特有行為和思維方式、價值觀的體系,或者說是人類社會所創造的特有意義體系。物質財富只能作為文化的載體,而不是一種獨立的文化要素。
筆者認為,無論是西語還是漢語,無論是廣義還是狹義,文化都是人類在實踐中創造出來的反映人的思想觀念的精神層面的成果,而物質文化只不過是這種精神成果作用于相應的物質上,體現在物質上,反映在物質上而已。并不是所有思想觀念都可以稱其為文化,它有空間、時間兩個條件:(1)它是在一定范圍內被大多數人認可和接受的。(2)它是不受歲月束縛而被傳承下來的。其實,這種人的精神層面的成果作用于何處,便形成了什么文化,作用在建筑上形成了建筑文化,作用在制度上便形成了制度文化,體現在文字上便形成了知識文化,反映在影音上便形成了影視文化,作用在人們的行為上便形成了習慣或風俗。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精神層次的思想觀念價值體系是無形的,不可見的,它的傳遞必須依附一定的載體,不可能脫離載體獨立傳遞。
二 人與文化的對立統一關系
(一)正負態度的角度:積極與消極的矛盾
在人與文化的相互作用過程中,二者都具有兩面性,既有積極的作用又有消極的影響。文化對人的積極作用主要包括:文化是人成為社會意義上的人及其發展的標志,是人的文化生命的對象化和反映;文化是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效工具,也是人與人之間相互溝通和交流的橋梁;文化也是人們生存和發展的保證和必要條件。文化對人的消極影響主要包括:文化的惰性和保守性,會成為人們發展和前進的障礙,成為人們進行創造性活動的阻力和包袱;文化的局限性和缺點會導致和加深人的弱點和缺陷;文化差異還會成為人與人相互溝通和理解的障礙,甚至引發各種沖突。
人對文化的積極作用主要包括:人作為文化的造物主,其實質規定著文化的實質;文化的發展動力源于人的發展;文化得以保存和延續的前提條件是人的發展和延續。人對文化的消極影響主要包括:人自身的偏見、誤解和局限性是文化的弱點和局限性產生的根源,并制約著文化系統的進化和不斷更新,既影響文化間的傳播和交流,又影響文化作用的發揮,甚至會造成文化的破壞。“創造文化的是人,毀滅文化的也是人;創造優秀文化的是人,創造文化糟粕的也是人”。人與文化之間這種積極與消極的矛盾在歷史的長河中此消彼長,推動著二者不斷完善和更新,是人與文化發展的不竭動力。
(二)能動性的角度:主動與被動的矛盾
就個人而言,生活的文化環境是先天既定的,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所處文化環境的影響,帶有此種文化的民族印記和時代印記。無論這種影響是積極也好是消極也罷,無論對自己所處的文化環境采取何種態度,人都不可能徹底擺脫本土文化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是潛移默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人作為文化塑造和影響的“產品”,在與文化的關系中有被動的一面。
與此同時,人對于文化的接受也有自覺的、能動的一面。也就是說,人不但可以在文化環境的作用下保持自己的獨特個性,而且還可以通過自身努力,逐漸改變自身所生活的文化環境。即在文化對人施加作用的同時,人也對文化施加影響。如果人是完全被動地接受文化環境所施加的影響的話,那么同一環境里的人與人就不可能存在個性和差異了。人類和人類文化不斷發展和進步的關鍵就在于,人們在接受文化作用的同時,在某種程度上自覺能動地改造文化環境,使自己成為現實文化的完善者、創新者和超越者。從這個角度看,人在人與文化的關系中又有主動的一面。人與文化之間這種主動與被動的矛盾在時空上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是促使二者不斷發展的源泉。
(三)質的角度:同一性與差異性的矛盾
人在實踐的過程中由自然人變為社會人,并在這一發展變化過程中創造了文化、豐富了文化、傳承了文化、創新了文化。與此同時,文化在被傳承、創新的過程中也不斷完善人,推動了人的發展,使人成為有文化特質和文化品質的人。也就是說,文化是人的創造物,同時,人也是文化的創造物。因而人與文化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同一性和互為表征的關系。“人與文化之間的這種同一性,使人們可以通過某種文化來了解創造和擁有這種文化的人,也可以通過特定的人群來了解他們所擁有的文化”[1]。所以,人與文化互為表征。脫離了文化的人是不存在的,沒有文化,人就沒有了文化生命,與動物無異。而文化來自于、存活于生生不息的人的世界中,是人的生命力和主體性的聲張和展示,人是文化的締造者、擁有者和守護者,沒有人就不存在文化。這一點體現了人與文化的相互依存、相互貫通、相互滲透的同一性。
然而,人與文化同時也存在著差異和區別。比如,文化中所含的人是對人的典型化和理想化,而人身上的文化又含有對文化的個性化、現實化、形象化。文化一旦被創造出來,便成為一種獨立于人的“異己”力量,具有了非人的特性,隨著時空的推移和其他社會因素的變化,這種文化會漸漸與時代潮流不符,成為人從事新的文化創造和自身發展的制約因素。如封建時期的儒家倫理文化對于現代人創造性的禁錮作用,這種制約作用體現了矛盾雙方即人與舊文化之間相互排斥、相互分離的斗爭性。
人與文化是一種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是一種由矛盾走向統一的螺旋式的上升關系,它的矛盾運動是人的發展和文化進步的源泉和動力。
三 對教育內涵的再認識
當前學術界普遍認為教育是一種有目的的培養人的活動。這種說法似乎將教育定義為一種單向活動,體現不出教育系統之中所蘊含的人和文化的動態生成性。我們應該從一個全新的視角理解教育的本質,將教育理解為是實現文化與人的雙向互動并在互動中相互建構的過程,即教育用不斷更新豐富、不斷動態變化的文化來完善人,又通過不斷完善、隨時代變化的人來豐富文化。這一動態循環系統便是教育系統。
從教育與文化的關系分析,教育是文化的社會傳承和創生機制。文化通過教育得以傳承,前輩們創造的文化成果代代相傳、綿延不斷;教育也創造著文化,不斷地豐富著人類文化寶庫的內容。這兩種過程是同時交互進行而非分開的。因而,人類文化呈現出加速發展的態勢。文化如果沒有教育的傳承和創生,它就無法形成一個開放的、發展的、動態的系統,文化的生命就將枯竭。
從教育與文化的關系來說,教育是使人由自然人變為文化人的過程。教育以人為中介實現文化的傳承和創生。人存在的特定社會文化環境,為人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性。但要使這種潛在的可能性轉化為現實,人必須通過教育,使外在的文化經過人的接受、理解內化為自身的一部分。教育的作用在于使個體成為發展了的人,文化化了的人。教育過程即是教育者借助教育內容(篩選后的部分文化)與受教育者之間的雙邊互動過程,其最終表現為文化為受教育者所接受掌握,知識增加了,心理結構得到發展,心理能力有所提高。因此,教育與人的關系,實質上就是文化通過教育促進個體發展的關系,教育過程就是使個體文化化的過程。
從文化與人的關系看,教育起著中介轉化的功能。一方面,通過教育過程,使人獲得一種把握世界方式的能力,使人得以發展。與此同時,通過教育對文化的選擇、批判和甄別,防止糟粕文化對人發展的阻礙,這種使人和文化相互適應的過程促進了二者矛盾的統一。另一方面,經過教育培養的人創造了更為高深、復雜的文化,從而形成新一輪的人與文化的矛盾。教育就是在不斷解決二者矛盾的同時又不斷引發新的矛盾。在人與文化的矛盾不斷解決和晉升的過程中,教育實現了人與文化的動態的雙向互動和建構。
參考文獻
[1]石中英.教育哲學導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2]張應強.文化視野中的高等教育[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