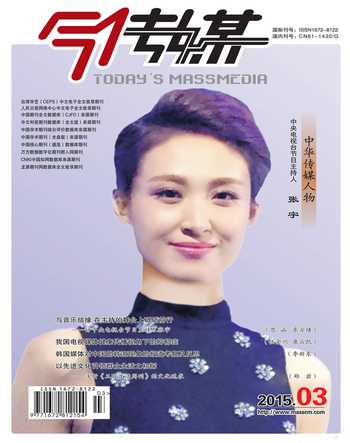《西藏商報》與藏族群眾認同建構研究
趙婷婷 馮萌
摘 要:大眾媒體所營造的媒體文化和國家文化、區域文化、民族文化之間存在著一種交流與對話關系。本文以《西藏商報》為研究對象,考察城市媒體文化對西藏社會的影響。研究認為,西藏城市媒體有效地結合地域文化與受眾的特色對藏族群眾進行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傳播和國家認同觀念的建構。
關鍵詞:《西藏商報》;城市媒體文化;國家認同
中圖分類號:G2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5)03-0131-03
大眾傳媒以其獨特的語言風格和文化魅力成為社會信息的傳播載體、社會文化的傳承載體,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發揮了無窮的力量。大眾媒體所營造的媒體文化也在和國家文化、區域文化、民族文化之間進行交流與對話。
因此,從媒體文化角度考察媒體與社會的關系,就能夠探索出一定的規律,能夠為新聞傳播實踐提出指導性的思路。本論文,筆者主要考察城市媒體文化對西藏社會的影響,以及在新時期如何通過媒體建構認同。
一、城市化與都市報《西藏商報》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西藏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在西藏的中心城市地位越來越突出。拉薩是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西藏其他地區的人越來越多地被拉薩的現代化所吸引,紛紛來到拉薩尋找自己的幸福生活。拉薩也是全國有名的旅游城市,布達拉宮、大昭寺、羅布林卡等景點吸引了無數的中外游客來到拉薩。拉薩的藏式建筑、街道、酒吧、拉薩河都是人們觀賞、體驗西藏文化的好地方。拉薩被一種充滿時尚和文化氣息的現代化氛圍所包圍,成為一個具有獨特魅力的城市。作為文化發展之代表的媒體文化,在快速發展的拉薩也需要一種新的力量,以滿足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此時,《西藏商報》一份代表城市人心聲,幫助城市人了解社會的報紙應運而生。《西藏商報》是區黨委機關報《西藏日報》創辦的第一張子報,其宗旨是:追隨時代步伐,傳遞社會信息,把握經濟命脈,服務百姓大眾。目前《西藏商報》以拉薩為中心,輻射全區七地市,覆蓋全國,成為繼《西藏日報》后又一發行量最大的報紙[1]。周德倉教授對《西藏商報》創辦的社會價值和歷史意義給出了高度的評價。他認為,1999年,一張全新的報紙——《西藏商報》面世。它的出現極具象征意義。這不僅是西藏第一張市民報紙,而且也是西藏第一家以企業模式經營的媒介。它使西藏報業增加了新的成員,豐富和改變了西藏傳媒體系。在機關報和行業報一統天下的西藏,它的“閃亮登場”,不僅帶給受眾以驚喜,還帶給西藏傳媒界以新的傳播理念[2]。《西藏商報》不僅在報道內容和傳播方式上與西藏傳統的報紙有所不同,在城市生活的解讀,市民價值觀的形成方面也具有獨特之處。《西藏商報》以拉薩城市報道為主,為市民帶來了第一時間的都市新聞信息,百姓視角的信息解讀,帶來全國的重要新聞和國內其他城市的報道。《西藏商報》是市民了解西藏,了解全國的重要窗口之一。
二、政治功能與商業功能的交融
西藏特殊的政治環境決定了報紙必須具有強大的政治功能,必須成為黨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傳達黨的方針政策、加大主流輿論引導力。這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原則,也是60年來的經驗總結。但是,大眾傳媒的功能是多項的。群眾需要媒體提供文化、娛樂、信息等多方面的功能,以滿足自身的文化和生活需求。同時黨報黨刊的經濟來源單一,以及國家其他地區的傳媒產業化改革也給西藏新聞業帶來了壓力。所以,都市報在西藏的面世解決了西藏媒體功能單一和經營創收困難的問題,實現了媒體政治功能和商業功能之間的有效融合。
政治功能與商業功能的交融體現在報紙的性質上。黨報和都市報都是社會主義新時期的報紙,都是黨的報紙。《西藏商報》在報紙版面編排、報紙欄目設計、新聞報道角度、信息解讀方式上和《西藏日報》是完全不同的兩種風格,但是在新聞文本呈現的話語、新聞報道建構的社會認同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可見這種類型的報道,是針對不同的受眾群體,有所側重的新聞報道模式,最終能夠達到殊途同歸的效果。從都市報創辦的初衷,也可以看出這樣的傳播效果的事先預設。都市報是黨報改革徘徊中異軍突起的生力軍。黨報的權威地位和壟斷資源使它成為中國報業的領頭羊。但又正是這種權威地位和壟斷資源使它同時過多地受制于體制、機制和觀念的束縛。黨報改革多年來步履沉重,難有突破。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推動下,一些黨報意識到:自己不能走市場,為何不生個“兒子”走市場[3]?可見,都市報是對黨報的補充,是黨報在無法實現內容和傳播模式的革新條件下的產物。都市報和黨報更是一種互動的關系,大眾傳媒是黨和國家的宣傳工具。在這樣的思想支配下,都市報所呈現的是一片辦報新天地[3]。《西藏商報》堅持正確的辦報方針,發揮了報紙聯系黨和群眾的作用,為實現西藏的跨越式發展付出自己獨特的力量。
三、大眾文化與中華文化認同邊界的模糊
都市報是一種市民文化的報紙,它具有濃郁的地方文化特色,也是大眾文化交流與傳播的重要場域。都市報與城市文化聯系密切。城市現代化的發展,促進了城市文化的發展。而都市報是城市文化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也是反映城市文化的一塊晴雨表[4]。《西藏商報》還以輕松、靈活的方式呈現這些內容。《西藏商報》的新聞內容主要包括兩個來源:本社記者采編,其他媒體、新聞機構供稿。本社稿件以城市生活為主的報道,內容主要包括本地新聞、大眾文化、城市生活、消費購物等版塊。這些內容的設置體現了一種市民生活為中心的傳播理念。外來稿件,則代表《西藏商報》向全國內地看齊,關注各地重要事件,報道中國社會的新動向;本地稿件,是西藏城市文化的集中表現,相關的報道主要集中在西藏的建筑文化、西藏飲食文化、西藏酒吧文化、西藏旅游文化、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展示等方面。它向大眾呈現了一個豐富、多元化、底蘊深厚、現代時尚的拉薩,呈現了熱情、虔誠、現代、有活力的西藏群眾形象。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文化中,西藏群眾的性格特征逐漸建立起來,并為外界所了解。《西藏商報》呈現了西藏的“大眾文化”,呈現了文化、城市與人的統一。
外來稿件,雖然和《西藏商報》的采編能力之間是一對矛盾,但是,它呈現給受眾的是全國當前的文化趨勢和潮流。它對于豐富西藏群眾的文化生活,引導正確的文化追求,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具有積極的作用。外來稿件報道全國新聞,特別是和大眾生活相關,并為大眾文化生活注入活力的新聞。其他媒體供稿的新聞以一種大眾文化建構國家認同。2012年10月,莫言獲得世界諾貝爾文學獎,這一重大文壇消息和國際消息使我們充分認識到中國文學可以走向世界,增強了國人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西藏商報》對這一消息也進行了連續報道,報紙大量采用其他媒體的稿件,報道了莫言獲獎的情況,向西藏群眾介紹了莫言的作品。這一報道的主要傳播學價值不僅是讓西藏群眾了解莫言,更是讓西藏群眾看到了中國文學、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而另外一組關于中央電視臺新聞“幸福”的報道,也引起了群眾的熱議,大家在思考“我幸福嗎”。《西藏商報》的大眾文化傳播超出了傳統主流媒體新聞傳播的范疇,顯示了群眾對中國文化的關注和思考,也證明了大眾文化在中華文化的建構中的強大的力量。
四、個人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的互動
《西藏商報》作為西藏日報集團的子報,是日報的有益補充,也是對日報功能的延伸。日報以成熟的儀式傳播、媒介事件報道成功地塑造了國家形象,建構了國家認同。而商報將敘述轉向大眾層面,沒有宏大的愛國主義敘事,但是卻以日常的、關系民生的新聞報道實現其特定的傳播價值。《西藏商報》關注拉薩的市民生活、關注相關政策、法規給民眾帶來的好處。《西藏商報》把目光轉向群眾當中,群眾生活、就業創業、求學等是媒體關注的主要問題,記者時常到群眾中去,報道群眾生活的問題。面對城市化帶來的各種問題,《西藏商報》都進行了深度的挖掘,制作出了好的新聞。這樣的報道也塑造了媒體切近市民生活的作風,塑造了媒體的良好形象。在這些社會問題的報道中,《西藏商報》逐漸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模式:尋找社會問題、分析原因、找到對策,推廣經驗。
關注民生的報道風格是否將媒體的功能導向了服務社會的層面,而偏離了國家價值理念傳播的功能?其實,也不一定是。《西藏商報》將報道的主體由國家活動轉向民眾活動,是對國家在社會發展中總體作用的更有效的呈現。因為國家的活動,最終是為了民眾的利益,國家活動的效果最終要在民眾的活動中體現。《西藏商報》將報道主體轉向民眾,有利于解決民眾的疑惑,也有利于通過報道民眾生活的變化反映國家政策和領導的水平。《西藏商報》對于民眾的報道致力于制造一種認同,尋找民眾認同的對象。通過展現西藏群眾工作、生活問題,以及問題解決的方式,塑造優秀的西藏群眾個體的形象。這種模式向報紙的閱讀者樹立了一個榜樣,是一種他人導向。他人導向是美國學者大衛·李斯曼在《孤獨的人群》中提出的概念。學者周憲認為,大眾文化環境下《百家講壇》的成功是一種“他人導向”下的民間小敘事對傳統宏大敘事模式的一種改造。“他人導向”理論認為,……而是始終關注于“他人”,這一“他人”或許是周圍的同學、同事,也可能是大眾傳媒。“他人”有兩種特點:其一,“他人”應該是個人可以認可的楷模,也就是說,他是那一個圈子中“最優秀的人”或最顯眼的人,大眾“求助于他人來指導自己追求和解釋人生的經驗”;其二,“他人”也并非固定不變的某個人,而是會隨時更替的偶像[5]。《西藏商報》試圖在平民中塑造一個個認同的對象,使受眾向其學習,進而改變自己的觀念,形成新的認識。
《西藏商報》淡化國家、民族符號的傳遞,而是將意義建構在普通的社會場景中。通過展現良好的西藏社會認同,教育民眾形成積極的現代認同。做一個新時期的好公民,就是促進社會發展、維護國家穩定,也就是愛國的表現。社會事件報道、文化報道、民眾生活報道對于大眾形成良好的社會公約,弘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都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當代愛國主義的表現是什么?筆者認為,不做違反民族團結,祖國統一的活動,不發表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的言論,就是愛國的表現;遵紀守法、熱愛生活、積極向上、追求進取就是愛國的最好表現。所以,《西藏商報》建立了一個國家認同的大眾文化的場域,并且將國家認同的概念和觀念進行了分解和重構。傾向于民間立場的新聞報道和文化傳播活動,充分實現了個人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的互動。
五、研究結論
西藏媒體新聞傳播具有獨特的語言魅力和特定的社會功能。區內各媒體發揮了積極的輿論引導和價值觀念建構的作用。西藏媒體除了對廣大鄉鎮地區、農牧民群眾的影響以外,對大城市群眾的影響力也是關鍵的環節。拉薩城市化程度比較高,城市文化獨具特色,城市媒體身份建構與國家認同的互動形成一組相互的關系。城市媒體,尤其是都市報在國家認同的建構中發揮著基本的作用。西藏媒體的新聞傳播語言與媒體特色為西藏群眾帶來了豐富的新聞和信息,也為國家宣傳相關政策和法律提供了大眾化的通道。國家希望在西藏群眾中傳播的價值觀念,媒體很好地結合地域文化與受眾的特色進行了傳播。媒體與國家形成了一股合力,共同作用于西藏群眾,影響群眾國家認同觀念的形成。
參考文獻:
[1]百度百科.“《西藏商報》”詞條 [EB/OL].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894/6407314.htm.
[2]周德倉.西藏新聞傳播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
[3]童兵.試論中國都市報的第二次創業[J].新聞記者,2005(4).
[4]吳艷.城市文化與都市報研究[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11(10).
[5]周憲,劉康.中國當代傳媒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責任編輯:艾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