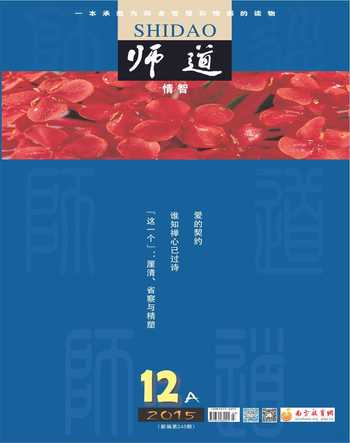春風化雨處,靜待花開時
葉君明
臺灣作家陳默安說:“堅強點,那些曾讓你哭過的事,總有一天會笑著說出來。”時間太瘦,指縫太寬,不經意間,自己已從事教師工作四年,回首這一千多個日日夜夜,有平靜,也有起伏;有迷茫時的困惑,也有收獲時的感動;有遇挫折時的淚水,也有成長后的喜悅。
執教高一的時候,在眾多科任老師的支持和幫助下,對于班主任工作,我雖然時常忙到焦頭爛額,但更多的是學生帶給我的喜悅和感動,無論是學習成績還是文體娛樂,我們班都是同類班級中的佼佼者。
但是高二分班后班級的狀況卻是急轉直下。因為優生的再分化,新班級中的學生無論是行為習慣還是學習成績較于之前的班級都差了很多。但面對著學情的變化,那時的我卻沒有隨之調整策略,仍是熱切地鼓勵學生和我一起努力向前沖,期待能和以前所帶的班級一樣,取得一個又一個的階段性進步。我的熱情很快遭遇到了學生們潑來的冷水。
開學不久的一次班會課上,我在課件上展示了“堅強、勇敢、努力、善良”這些我深信不疑的價值時,我希望我的學生們也能明白堅持不懈必能有所收獲的道理,但是孩子們的眼神卻讓我看到了無動于衷,讀出了“無聊”兩個字!當我激情洋溢地激勵同學們要全力以赴,形成一種“進攻性學習”的習慣時,他們卻百無聊賴地期待著快點下課。
幾個男孩子每天習慣性地遲到,上課時不是偷偷玩手機就是睡覺;考試時選擇題全部選B,材料題一律空白,或寫著一些與考試科目無關的內容,或在試卷上畫漫畫;有的男孩子囂張地在女老師的課堂上開黃色笑話,班上附和哄笑一片;有個男生宿舍衛生臟亂差,屢遭宿管投訴甚至嚴重到被停宿;女孩子們宿舍內部小矛盾不斷……現在的班風、學風與我之前所帶的班級之間的落差之大讓我難以接受,我急切地希望他們能夠“改邪歸正”。針對幾個特別囂張的男生,我采取了高壓打擊政策,但我們之間的矛盾卻越加白熱化。他們在周記中赤裸裸地說我表面裝得很民主,但實際上像斯大林一樣強硬專制,甚至在私底下拿我的名字開玩笑,稱我為“暴君明”。有些男生知道我平時不怎么玩微信,就在微信上發上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臺的圖片,并配文:消滅暴君,走向共和。
當時我被這個班的孩子折磨到身心俱疲,多少次我為自己教育不好一個孩子而深深內疚,那種深切的力不從心的感覺會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浮上心頭,甚至在夢中都會夢到班級的糟糕狀況,這無聲的傷痛讓我手足無措。我不明白他們為什么要那么惡劣地惹惱老師?我不明白他們為什么無心向學,卻把大把的時間浪費在嬉戲打鬧上?我不明白為什么學校明令禁止做什么,他們偏偏就做什么?我不明白他們明明可以做得更好,卻為什么非要自甘墮落?
在那一段迷茫的低谷期,感謝身邊的同事不斷鼓勵與支持我,也感謝自己有著閱讀的習慣,有著反思的勇氣,讓我能從書本中汲取源源不斷的營養。當讀到蘇霍姆林斯基先生的《給教師的建議》時,我明白了:正是因為學生的頑劣,所以才需要教師的教育;當讀到雷夫先生的《第56號教室的奇跡》時,我懂得了:要深入了解、寬容學生,做學生的榜樣,充分發揮自己的教育智慧與創意,點燃教育的熱情;當讀了佩納克先生的《上學的煩惱》時,我認識到:任何一個“壞學生”都有值得肯定之處,都有不為老師所知的脆弱的一面……
在堅持中,在反思中,我逐漸認識到:以前在自己的學習拼搏過程中,我是主體,我以自己的堅韌與努力往往可以達到預期的追求,因為成長只是我自己一個人的事情。但現在不同了,主體已不再是我,成長的主體是學生,而我面對的又是一群有著不同見解和不同成長方式的學生,我要做的應該是思考以何種最佳方式來引導他們,怎樣才能把我的一些積極信念轉化為他們的信念,繼而讓孩子們的主體積極性得到最大的發揮。
思考越多,了解越多,我明白了孩子們之所以調皮搗亂、無心向學,是因為他們沒有明確的目標;他們的玩世不恭,倔強反叛,都只是一個缺少愛、渴望得到愛的孩子在面對外界批評指責時的自我保護色而已。
所以,我開始轉變了我的教育方式。我仍然愛護我的學生,但在出現問題時,我改變了以往強硬的做法,努力做一個講道理、有智慧的班主任。我利用班會課讓大家談遲到的危害;為他們介紹憧憬中美好的大學,讓他們為自己樹立奮斗的目標;并邀請科任老師們開展了“紙張疊高”“國王與天使”等團體活動;每天都“抓”幾個學生進行學習和心理輔導;抽空拍下男生宿舍“慘不忍睹”的畫面,在女生的笑聲中男生羞紅了臉;買一些好書給上課總是睡覺的男生看;在那位成績不錯但愛講臟話的男生的本子上借清朝一代大儒王永彬先生的名言“生資之高在忠信,非關機巧;學業之美在德行,不僅文章”作為勉勵,并讓他做“文明語言督察”,使其先自律再律人……在朝夕相處中,在一件件小事中,師生之間慢慢地培養起了感情。越來越多的學生感覺到,“老師是非常喜歡我們的,是和我們在一起的,是和我們一起奮斗與進步的”。
半個學期過去后,我們之間的關系變得和諧起來。肩并肩地奮斗讓我們之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學生與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開始親切地叫我“Jimmy”(與我名字諧音)。在他們迷茫彷徨之時,我站在一個也曾為高考彷徨的過來人的角度給予他們鼓勵,他們戲稱我為“明哥”,有學生編成口號“信明哥,上本科”。每次大考之前,孩子們開始焦慮,我一對一找了班上每一位學生進行學習與心理輔導,幫助他們克服考前焦慮,給予鼓勵和關愛。有的學生甚至尊稱我為“爸爸”(也有可能是本人長得比較著急)。學生以父之名,為我命名,這是我作為他們的班主任最大的驕傲。
師生關系的融洽讓班級的學習成績也在逐漸地提升。第一階段考試的時候,我們班幾乎科科墊底,但在期末考試出來后,竟然有四科是同類班級中的第一,兩科是第二,再也沒有一科墊底了。他們這種媲美于“化腐朽為神奇”的能力讓我驚喜感動。更具有喜感的是,當我很開心地在班上跟學生們分享這個喜訊之時,學生們也不敢相信自己有這么大的潛力,第一反應而是很認真地確認:“是正數第一?還是倒數第一?”我進而又利用這個契機狠狠地鼓勵他們,發揮皮格馬利翁效應,期望他們取得更大的進步。
常說學生要感恩老師,我認為,老師其實也要感恩學生。我覺得我遇上這群孩子真的是我人生的幸運。他們各種各樣的出乎意料的行為,讓我焦頭爛額的突發狀況,使我變得更加穩重與堅強;他們華麗的蛻變,“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的覺悟,使我明白了班主任工作的意義所在。在學期總結之時,我對班上的學生說:“相對于你們對老師的感謝,老師更要感謝你們。因為老師只是讓你們收獲了我自己一個人的思想而已,而你們,卻讓老師我收獲了五十一種思想。”
在挫折與困境中,我學會了堅韌,學會了反省,我真正懂得了教育是一門愛和慢的藝術。“沒有愛就沒有教育”,我們作為教師,對學生的教育始終都要以愛為基礎,用愛心陪伴著對學生教育的全過程,在“曉之以理,導之以行”的同時,還要“動之以情”,讓他們真正感受到班主任的一片愛心,春風化雨。但在教育的過程中,我們又不能以愛的名義去綁架學生成長的方式,因為學生的成長經歷各異,家庭背景亦不相同,教育方式當然也應該不同,所以我們要因材施教,給予學生足夠的成長時間與空間,靜待花開。
回想起這些學生一副副生動活潑的笑顏,我感謝他們曾經的調皮,感激在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難與挫折。事實證明,當時讓我哭過的事情,現在我已經可以笑著說出來了。
(作者單位:廣東佛山市順德區杏壇中學)
責任編輯 黃佳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