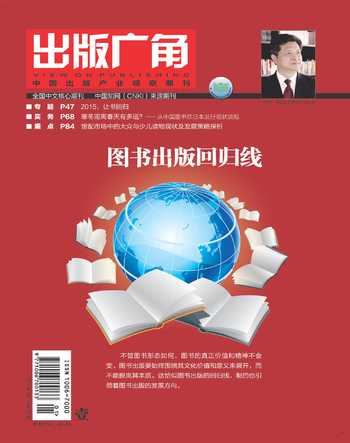出值得出的書才有意義
2015-05-30 08:16:00劉明清
出版廣角 2015年1期
劉明清

從一般意義上講,我們總認為圖書(出版)的根本目的是知識積累和文明傳承。這當然沒有錯。可是具體到每一本書,如何判斷其具有出版意義,則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我們更容易將暢不暢銷,有沒有讀者(也只是當下讀者)愿意購買,來作為決定出版與否的重要標準,甚至是唯一標準。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是出版的大眾化、娛樂化,乃至庸俗化。
在我個人看來,一本書值不值得出版,最根本的考慮標準是具不具有傳播價值。所謂傳播價值,首先是值得傳播——專家學者們的有創見、有思想、有新意的學術作品當然值得傳播;而非專業人士的創作,如果也同樣具有創見、思想和新意,也是值得傳播的。至于是不是有創見、有思想、有新意,出版者往往也會囿于自己專業知識的限制,需要請專家來幫助評判——這便是西方學術出版機構通常采用匿名專業評審制度的緣由。其次圖書是不是值得出版。這自然與每家出版機構定位有關系。以我們中央編譯出版社為例,我們盡管也有機會遇到許多值得傳播的好作品,比如原創小說等文藝作品等,卻始終是忍痛割愛的。再有,就是出版機構有沒有能力來傳播。即使那些值得傳播的作品,但是你沒有傳播能力也是枉然。例如,你支付不起高版稅、你的編輯力量不足、你的營銷水平不夠,甚至你承擔不了經濟風險和政治風險等等,這都是制約條件。
作家張愛玲認為愛情就是不問值不值得。但是,干出版是必須要問的。值得出版的,你沒有出,自然是遺憾;不值得出版的,你出了,即使賺了些散碎銀兩,恐怕也高興不起來。
猜你喜歡
新少年(2022年9期)2022-09-17 07:10:54
中學生數理化·七年級數學人教版(2022年5期)2022-06-05 07:51:50
華人時刊(2022年7期)2022-06-05 07:33:26
當代陜西(2021年13期)2021-08-06 09:24:34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英綜合(2020年6期)2020-12-16 02:56:41
文苑(2020年12期)2020-04-13 00:54:10
中學生數理化·中考版(2019年12期)2019-09-23 06:23:28
人大建設(2019年4期)2019-07-13 05:43:08
當代陜西(2019年12期)2019-07-12 09:11:50
北極光(2014年8期)2015-03-30 02:5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