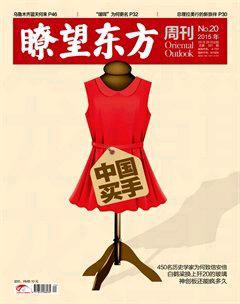“璦琿”為何更名
齊岳峰

黑龍江黑河市璦琿鎮,2015年5月19日清早,全鎮的人都沖著肖歧笑:“肖老師啊,新聞聯播都播了!”
人們為他高興,“這么多年沒白跑”。
5月18日傍晚的新聞聯播里,肖歧所在的鎮子被官方正式宣布恢復了它曾經的名字——璦琿。
對于一輩子研究地方史的肖歧來說,茲事體大。
在央視正式公布之前的3月份,黑龍江省政府已經批準,將肖歧生活了一輩子的黑河市愛輝區愛輝鎮政區名稱用字恢復為“璦琿”。
從璦琿到愛輝
相當長的時期內,“璦琿”為大多數人所知曉,還是緣于150多年前的那場戰爭——1858年清朝與沙俄簽署《璦琿條約》,該條約令中國失去了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約6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這件事被寫在中學歷史課本上。
璦琿歷史陳列館館長陳會學對《瞭望東方周刊》說,自清代起,璦琿已經是黑龍江中上游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作為清代軍事重鎮,黑龍江將軍的駐在地璦琿城又被漢譯為“黑龍江城”,所以肖歧說,當地其實是滿族文化的起源地。
陳會學由衷懷念康熙時期的雅克薩大戰,那時,璦琿是大清最重要的后備基地。僅僅百年后的1858年,中俄簽訂《璦琿條約》。1900年,沙俄軍隊大舉入侵東北,璦琿陷落,被俄軍焚毀。
陳會學說,作為中俄互市重鎮,當時璦琿城已經是“居民四萬、商賈三千”的繁華之地。《璦琿縣志》更稱當地為“黑龍江中樞之點”。
7年后,當時的璦琿副都統姚福升帶領民眾重建璦琿城,保留至今。
陳會學告訴本刊記者,自清代至民國的公文,使用的都是“璦琿”這兩個字,當地人與很多學者也大多用“璦琿”行文。
百年一瞬。眼下,鎮委書記王臣為自己治下的1.5萬人規劃了“農牧業與文化旅游產業綜合發展”的藍圖。可1956年根據國務院簡化生僻字的要求,璦琿在過去60年中變成了“愛輝”。
肖歧覺得,國家推廣簡化字無可非議,但“歷史很難寫”,尤其是涉及到條約與古城的文字,到底該用哪個寫法?
而在愛輝歷史陳列館工作的時候,肖歧總會被外地游客無數次質疑:“應該是璦琿吧?”
他發現,外來的人們大多知道“璦琿”,但并不理解“璦琿”和“愛輝”的關系。甚至一些黨政部門的牌匾也會有些差池——當地有一個醒目的標志牌寫著“歷史文化名鎮愛輝”,這不是違背歷史了嗎?
肖歧認為,“璦琿”之名可能源自“璦琿河”,亦有滿語“母貂”的意思(當地曾盛產貂),但讓他念念不忘的最美的釋義,來自康熙字典和中國辭源——美玉。
名字太美了
2009年開始,當地就躍躍欲試想恢復“璦琿”,因為這是一筆無形的文化遺產。2009年當地申報“愛輝區”更名為“璦琿區”,同批次還有三個地方也要申報改名,其中就包括那次唯一獲得成功的湖北襄陽(襄樊改為襄陽)。
肖歧起初自信滿滿,但在國家組織的答辯會上,他發現,改一個地名不是那么容易——“12個專家問我一個人”,民政部地名司司長說,改名涉及交通、國土等多部門,還要改地圖。
也是在那次會議上,地方史研究者肖歧首次聆聽了文字專家對于“璦琿”的講解:“這兩個與玉有關的字,不能分開用。”
對本刊記者回憶至此,他不由感慨:“多美、多有意義的名字!”
愛輝更名提案2009年未獲通過。
后來有人說,如果不改“愛輝區”,改愛輝鎮呢——一個鎮更名,只需要省級部門同意,而一個區級單位更名,就要上報國務院。
3年后,王臣擔任愛輝鎮委書記。
他也關注到了“璦琿”這個名字的問題,他覺得,當地擁有全國最大的知青精神傳承基地“知青博物館”,有全國文保單位璦琿新城遺址,還有被列入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的“上元節”……如果能恢復鎮名,可謂錦上添花。
而且,鎮政府辦公室的三塊牌子上,“黨委和政府用的是‘愛輝,但2013年掛牌的‘璦琿古城歷史開發管理處則使用‘璦琿。”
王臣更在意的是,當地每年迎來30多萬名海內外游客,“恢復璦琿政區地名用字,有利于消除歷史隔斷,促進北部邊疆歷史文化的繼承和傳播”。
批下來了
在王臣等人的籌劃下,2012年以來,當地連續三年舉辦了“璦琿上元節”,2013年,“璦琿上元節”入選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在次年6月的“璦琿歷史文化論壇”上,“滿學專家”閻崇年應邀作了關于璦琿歷史文化的專題報告,“論證了‘璦琿是清始祖發祥地和在北方少數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王臣說。
他向本刊記者回憶,從2015年2月開始,當地下發了1700份調查問卷,開了40次座談會——就為了征求對改名的意見。
同時,當地黨委政府在《黑河日報》向社會各界進行了為期7天的征求意見公告,“得到了社會各界人士的全面認可,紛紛以電話及手機短信的方式表示支持與贊同。”
2015年2月12日,由愛輝區維穩辦、法制辦組織召開了社會穩定風險分析評估聽證會,“對可能出現的不穩定因素進行逐項科學分析、準確預測、客觀公正地作出評估。”
所有的因素最終都“達成共識”。鎮上隨即向黑河市民政、黑河市政府、省民政廳區劃處及省政府辦公廳進行了更名申報,并迎來了黑龍江民政廳組織召開的一個座談會。
那次座談會上,73歲的中國民俗協會會員白長祥感慨,“如果沒有‘璦琿,從歷史角度看是可怕的”,“若干年后,我們的孩子將無法找尋‘璦琿的意義”。
黑龍江省同意更名的文件傳到璦琿鎮已經是夜里10點,王臣給肖歧打電話:“批下來了!”已經入睡的肖歧爬起來跑到鎮委看文件,他記得文件最后一句話是“費用自理”——改一個地名涉及很多費用,比如,所有與這個地名有關的牌匾都要更新。
王臣說,這次“一刀切,不惜一切代價改”。
2000年退休的肖歧,而今是黑河市檔案館地方史顧問。他總在古城里作民間調查,“清代9個黑龍江將軍,其中8個死后葬在璦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