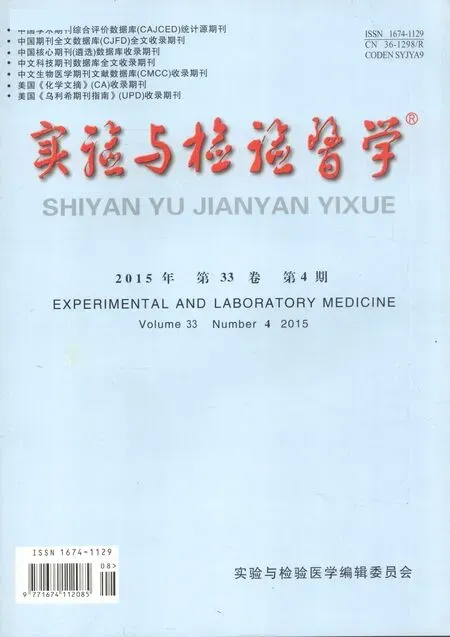膽道感染患者膽汁病原菌分布及耐藥性分析
鄧懋清,張琳清,黃浩南,吳定昌
(1、福建醫科大學附屬龍巖第一醫院檢驗科,福建 龍巖364000;2、福建省龍巖市新羅區衛計委,福建 龍巖364000)
膽道感染一般是由結石阻塞膽囊膽管,造成膽內膽汁繼發細菌感染而引起炎癥,是普外科的常見疾病[1]。為了給臨床合理選擇抗菌藥物提供參考依據,我們對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臨床356例膽道感染的膽汁培養出的295例病原菌的分布及其藥敏結果進行回顧性分析,現報道如下。
1 材料與方法
1.1 菌株來源 菌株均來源于我院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住院各科送檢的膽汁標本。同一患者多次分離到的菌株不重復計入。
1.2 菌株鑒定和藥敏試驗 按照細菌檢驗常規方法培養分離,采用美國BD Phoenix100全自動微生物分析儀的配套試劑操作;藥敏紙片采用OXOID公司產品,試劑都在有效期內;藥敏試驗判斷標準參照CLSI 2014[2],嚴格按照操作規程進行操作。產超廣譜β-內酰胺酶(ESBLS)菌株均用微生物分析儀進行初篩,再用CLSI推薦的確證試驗進行確證[3]。
1.3 質控菌株 為大腸埃希菌ATCC25922、銅綠假單胞菌ATCC27853、金黃色葡萄球菌ATCC25923、糞腸球菌ATCC29212。
1.4 統計學處理 用WHONET5.6軟件進行統計與耐藥性分析。
2 結果
2.1 病原菌分布 356例膽汁培養共培養出295株病原菌,有5例為混合感染。其中革蘭陰性桿菌181株(61.4%),革蘭陽性球菌 113株(38.3%),以大腸埃希菌和糞腸球菌檢出率最高。具體菌種分布,見表1。

表1 295株膽汁培養病原菌的分布及構成比
2.2 病原菌對抗菌藥物的耐藥率 革蘭陰性桿菌對碳青酶烯類藥物、阿米卡星和頭孢派酮/舒巴坦耐藥率低,見表2;革蘭陽性球菌對氨芐西林、阿莫西林/克拉維酸、萬古霉素、替考拉寧、利奈唑胺仍比較敏感,見表3;真菌對伊曲康唑、氟康唑、兩性霉素B的耐藥率為0%。

表2 主要革蘭陰性桿菌對常用20種抗菌藥物的耐藥率(%)

表3 主要革蘭陽性球菌對常用20種抗菌藥物的耐藥率(%)
3 討論
健康人的膽汁是無菌的,但在患有膽石癥、膽道腫瘤等疾病時,腸道內的病原菌會逆行或經血液、淋巴液進入膽道和膽囊而致感染。膽道細菌來源于腸道且與腸道正常菌群相吻合[4]。我院356例膽道患者膽汁培養出295株病原菌,陽性率為82.9%,同以往報道基本一致。膽道感染致病菌仍以革蘭陰性桿菌為主,占61.4%,其主要病原菌依次為大腸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和陰溝腸桿菌;革蘭陽性球菌占38.3%,主要為糞腸球菌和屎腸球菌,與以往的文獻報道檢出的主要菌群相似[5,6]。革蘭陰性桿菌感染率與廖國林等[7]報道的65.3%一致,革蘭陽性球菌感染率高于汪麗等[5]報道的27.5%,,與李佳俊等[8]報道的34.62%相似,提示腸球菌日益成為膽道感染的主要致病菌。氣單胞菌、普羅威登斯菌、摩根菌等病原菌的出現,表明引起膽道感染的病原菌種類不斷增多。膽道感染病原菌譜構成的變遷,除與采集膽汁的方法、培養技術等有一定的關系外,也與抗生素的廣泛的使用和用藥環境有關。
膽道感染除需要解除梗阻和通暢引流膽汁外,對抗菌藥物的合理選用也很重要。依據膽汁培養及藥敏結果指導用藥最為合理,是臨床治療膽道感染的重要措施[9]。從表2可看出,革蘭陰性桿菌對碳青酶烯類藥物、阿米卡星、頭孢派酮/舒巴坦耐藥率低,可作為臨床治療膽道感染的經驗用藥,與陳紅衛[10]推薦的相似。但阿米卡星有腎毒性和耳毒性,應慎用,特別是老年病患者[11,12]。大腸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中產ESBLs株的檢出率分別為42.7%和18.5%,這與廣譜抗菌藥物的廣泛使用密切相關,從而也增加了臨床的用藥難度,應引起重視。從表3可看出,革蘭陽性球菌的腸球菌對氨芐西林、阿莫西林/克拉維酸、替考拉寧、利奈唑胺仍比較敏感,耐萬古霉素的腸球菌(VRE)檢出率依然較低,糞腸球菌、屎腸球菌對萬古霉素的耐藥率分別為1.6%、0%。由于腸球菌屬的固有耐藥和獲得性耐藥,可用藥較少,臨床治療時輕癥者可以選用青霉素類抗生素,嚴重者可選用萬古霉素、替考拉寧或利奈唑胺,必要時聯合氨基糖苷類獲得協同作用[13]。有5例為混合感染,都為大腸埃希菌與腸球菌引起的混合感染,因此臨床用藥應聯合使用不同抗菌譜的藥物[14]。真菌的感染率低(0.3%)且藥物敏感性好。
另外,因設備及技術有限,我院并未開展厭氧培養,但是膽道感染有很多是厭氧菌感染引起的[15],與需氧菌共同引起混合感染,建議在治療時應加用抗厭氧藥物。
綜上所述,隨著廣譜抗生素的廣泛使用,膽道感染的病原菌譜不斷變遷,多重耐藥菌株也日趨增多,臨床在治療時應根據膽汁細菌培養和藥敏結果,充分考慮細菌對藥物的敏感性、藥物在膽汁中的濃度以及膽道感染中存在混合感染需聯合用藥等因素,正確合理選擇抗菌藥物以提高膽道感染治愈率。
[1]林君榮.95份膽汁細菌培養與藥敏分析[J].淮海醫藥,2007,25(1):72-73.
[2]張雅薇,王輝.2014年CLSI M100-S24主要更新內容解讀[J].中華檢驗醫學雜志,2014,37(4):256-260.
[3]吳紹蓮,池春燕,胡辛蘭,等.血培養常見病原菌的變遷和耐藥性分析[J].實驗與檢驗醫學,2013,31(2):138-140.
[4]田道容.65例膽汁培養結果及藥敏結果分析[J].臨床合理用藥雜志,2011,4(06):77-78.
[5]汪麗,王峰,陳瑜.膽道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藥性分析[J].中國衛生檢驗雜志,2008,9(18):1816-1818.
[6]應建飛,呂火祥.膽道感染患者膽汁中病原菌分布與藥物敏感性分析[J].中華醫院感染學志,2012,22(15):3289-3290.
[7]廖國林,王海紅,王穎翔,等.膽道感染患者膽汁培養病原菌分布與耐藥性分析[J].國際檢驗醫學雜志,2013,34(22):3077-3078.
[8]李佳俊,何江,李國剛,等.膽石癥患者膽汁中病原菌培養結果及耐藥性分析[J].中華醫院感染雜志,2007,17(6):746-748.
[9]姚俊,許亞平,孟鑫,等.114例膽道感染患者膽汁細菌培養分析[J].臨床內科雜志,2006,23(10):677-678.
[10]陳紅衛,汪家輝,徐國強.膽道感染患者膽汁中病原菌的分布與耐藥性分析[J].中國醫藥導報,2013,10(34):1673-1675.
[11]黎沾良.外科患者陽性革蘭球菌感染的抗菌藥物治療[J].中華外科雜志,2006,44(3):146-148.
[12]楊雪英,鄺潔如,楊斌,等.126例膽汁細菌學分類及其耐藥性分析[J].中華醫院感染學雜志,2002,12(5):394-398.
[13]廖國林,劉建,李芳等.腸球菌屬醫院感染分布及耐藥性分析[J].中華醫院感染學雜志,2009,19(13):1935-1936.
[14]張雪青,潘欽石,周鐵麗.膽道感染的病原菌耐藥性分析[J].肝膽胰外科雜志,2003,15(3):0182-0183.
[15]薛國杰,鄒鳳梅,魏蓮花,等.膽汁標本436份細菌培養結果分析[J].中華檢驗醫學雜志,2000,23(2):11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