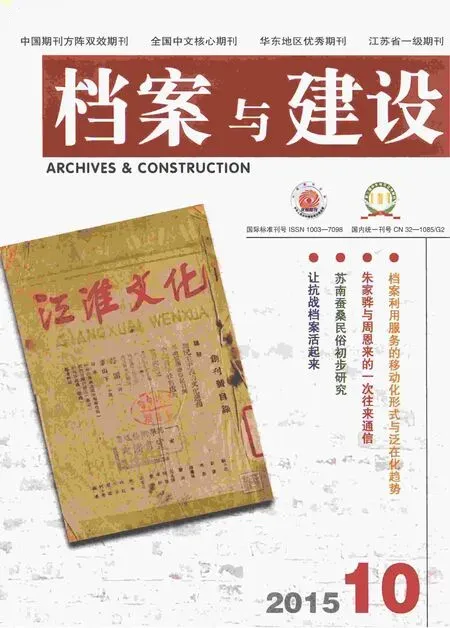蘇南蠶桑民俗初步研究
沈建東
(蘇州博物館,江蘇蘇州,215000)

王禎《農(nóng)書》中的蠶神
蘇南養(yǎng)蠶植桑起于何時(shí),史無(wú)可考,從考古發(fā)掘材料看,吳越先民從新石器時(shí)代開(kāi)始就飼養(yǎng)家蠶了,在吳興錢山漾遺址、河姆渡遺址、蘇州唯亭草鞋山遺址等地發(fā)現(xiàn)了家蠶絲織物和紡織工具,充分說(shuō)明蘇南養(yǎng)蠶歷史的悠久。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江南的絲綢生產(chǎn)得到了長(zhǎng)足的發(fā)展,固守江東的孫權(quán)曾專門頒布“禁止蠶織時(shí)以役事擾民”的詔令。隋唐時(shí)代,江南絲綢業(yè)發(fā)展更快,據(jù)《吳郡志》載唐之土貢,考之《唐書》所貢,有絲、葛、絲綿、八蠶絲、緋、綾布。明清蘇州絲綢生產(chǎn)不斷向周圍農(nóng)村地區(qū)擴(kuò)散,促進(jìn)了江南市鎮(zhèn)的興起。據(jù)清《吳江縣志》、《震澤縣志》記載:“綾綢之業(yè),宋元以前惟郡人為之,至明熙宣間邑民始漸事機(jī)絲,猶往往雇郡人織挽,成弘而后,土人亦有精其業(yè)者,相沿成俗。”
從古至今江南一帶慣養(yǎng)兩蠶,即春蠶、秋蠶,尤其是春蠶在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jì)生活中占據(jù)重要作用,有“春蠶半年糧”之說(shuō)。蠶桑民俗豐富而多樣,茲簡(jiǎn)述如下,以求教于大方。
一、祭蠶神與祛蠶祟
蠶神,考之中國(guó)史籍,名稱甚多,有西陵氏(嫘祖)、馬頭圣母、寓氏公主、天駟星君、菀窳夫人、蠶花娘娘……在江南民間流傳祭祀最廣的還是嫘祖和馬頭娘娘,鄉(xiāng)民稱為“蠶王菩薩”“蠶花娘娘”,鎮(zhèn)上有蠶王廟專門供奉。據(jù)當(dāng)?shù)乩先嘶貞洠饾尚Q王殿為五花蠶神,相傳她三眼六臂,一只豎眼位于額中央,盤腿而坐,手捧蠶花。震澤蠶農(nóng)每當(dāng)蠶事之前,皆備香燭前往蠶神廟祭蠶神,祈求豐收。不僅如此,蠶農(nóng)還要到鎮(zhèn)上南貨店買“神馬”,稱之為“馬張”,是一張印在紅紙上的木刻蠶神像,請(qǐng)回家貼在蠶室里,在孵蟻、蠶眠、出火、上山時(shí)都要備供品供奉。可惜震澤蠶王殿已不存。
盛澤鎮(zhèn)至今還完整保留有先蠶祠,位于盛澤老街。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座高大而精致的磚雕門樓,正門上方掛著“先蠶祠”豎匾。大門兩側(cè)各有一個(gè)輔門,門頭分別刻著“織雪”“繡錦”描金方匾。先蠶祠俗稱蠶王殿,也是當(dāng)?shù)氐慕z業(yè)公所。清道光二十年(1840)當(dāng)?shù)匦Q農(nóng)為祭奠蠶花娘娘而建,是蘇南乃至全國(guó)絲業(yè)公所規(guī)模最大的建筑,曾因一年一度的“小滿戲”而名噪江南。
蠶農(nóng)除祭蠶神外,還有到杭州燒香祈蠶桑豐收的習(xí)俗,流傳至今不衰。而且往往是蘇錫常的蠶農(nóng)到杭州燒香,而浙江桐鄉(xiāng)、湖州等地蠶農(nóng)到蘇州來(lái)燒香。她們結(jié)伙成隊(duì),坐香船赴杭,自備糕粽為食,喜歡購(gòu)買泥貓,稱之為蠶貓,或在臘月購(gòu)買蘇州桃花塢木刻年畫之蠶貓圖,放在蠶房中辟邪驅(qū)鼠。并購(gòu)買竹籃、飯籃作采桑、送飯之用。如今,除了年紀(jì)大的婦女到杭州燒香外,大多數(shù)年紀(jì)輕的婦女、姑娘只想趁初春春蠶前的空閑到西湖游玩一番而已。
二、照田蠶、念蠶經(jīng)
解放前每年歲末,蠶鄉(xiāng)有照田蠶習(xí)俗,“田間縛藁條于長(zhǎng)竿擎而燃之以祈絲谷”。立春迎春牛,“民間爭(zhēng)取春牛土置床下,云宜田蠶。”在震澤農(nóng)村,每逢清明節(jié),有民間藝人用稻草扎一馬形,身披胄甲,騎在馬上,敲打木魚(yú)、小鑼,來(lái)到蠶農(nóng)家門前,說(shuō)唱吉利話,祝蠶繭豐收。這種說(shuō)唱形式當(dāng)?shù)胤Q為“念佛句”,念完后蠶農(nóng)給米一升左右或現(xiàn)金若干。這種說(shuō)唱形式可能是受佛教出家人化緣習(xí)俗的影響,故而當(dāng)?shù)匦Q農(nóng)稱之為“念佛句”。當(dāng)?shù)孛耖g藝人預(yù)祝豐收的吉利話,又十分符合蠶農(nóng)祈望蠶繭豐收、發(fā)財(cái)富裕的心理,所以在當(dāng)?shù)睾苁軞g迎,今已少見(jiàn)。筆者曾和其他采編人員在震澤的徐家村采錄了一篇完整的《馬明皇菩薩念蠶經(jīng)》,經(jīng)文從蠶的孵出到上山結(jié)繭,發(fā)財(cái)致富,描繪了蠶成長(zhǎng)的全過(guò)程。全文如下:
馬明皇菩薩到門來(lái),身騎白馬上高山,
上海城里出東門,勿是今年出來(lái)明年出,
宋朝手里到如分,馬明皇菩薩勿吃葷來(lái)勿吃素,只吃點(diǎn)金針、木耳、素團(tuán)筍。
蠶室今年西南方,曾出東南對(duì)龍蠶,
清明過(guò)去谷雨到,谷雨兩邊堆寶寶,
頭眠眠來(lái)齊落落,二眠眠來(lái)嶄嶄齊,
九日三眠蠶出火,楝樹(shù)花開(kāi)促大眠,
促好大眠開(kāi)葉船,來(lái)順風(fēng),去順風(fēng),
一吹吹到河橋洞,毛竹扁擔(dān)二頭尖,
啷啷挑到蠶房邊,喂蠶好比龍風(fēng)起,
吃葉好比陣頭雨。
大眠回葉三晝時(shí),小腳通跑去上山,
東山木頭西山竹,滿山繭子白滿滿,
廿四部絲車二面排,當(dāng)中出條送茶湯,
東面?zhèn)鱽?lái)鶯哥叫,西面?zhèn)鱽?lái)鳳凰聲,
紅袱包,綠袱包,一包包了十七、廿八包。
東家老太要想閌,西家老太要想放,
亦勿閌來(lái)亦勿放,上海城里開(kāi)爿大錢莊,
收著蠶花買田地,高田買到寒山腳,
低田買到太湖邊。(注:吳語(yǔ):閌:藏的意思)
在蘇南一帶民間信仰的神靈大多稱“菩薩”或“老爺”,馬明皇菩薩又稱馬明王、馬明菩薩,即蠶王馬頭娘。古代神話傳說(shuō)如《山海經(jīng)》所載,說(shuō)是據(jù)樹(shù)吐絲之女子。荀子《蠶賦》稱蠶為其身柔婉而馬首。民間流傳最廣的神話當(dāng)是該神為民間女子,為馬皮裹身,懸于大樹(shù)間,遂化為蠶,說(shuō)明古人認(rèn)為蠶與馬有相似之處,蠶頭似馬頭,因而稱之為馬頭娘。民間受佛家影響又稱之為馬明皇菩薩。蠶與女子關(guān)系密切,如袁珂先生所言:“吾國(guó)蠶絲發(fā)明甚早,婦女又專其職任,宜在人群想像中,以蠶之性態(tài)與養(yǎng)蠶婦女之形象相結(jié)合。”故稱蠶神為蠶娘娘、馬頭娘娘。
在節(jié)日飲食上,震澤、盛澤的蠶農(nóng)有清明日吃螺螄的習(xí)俗,但這天吃螺螄不能用嘴吸出而用針挑吃,稱“挑青”。相傳蠶寶寶有病稱“青娘”,吃空的螺殼要向屋頂上拋,要使“青娘”無(wú)處藏身無(wú)法作祟,因而起到壓邪作用。同時(shí)還要在蠶室門前地上用石灰畫弓和箭的形狀,謂可驅(qū)蠶祟,求得蠶寶寶順利成長(zhǎng)。此外,家家蠶室門上要貼紅紙條,掛桃葉、楝樹(shù)葉驅(qū)鬼,求得蠶寶寶無(wú)病無(wú)災(zāi),然后家家閉戶,不相往來(lái),專心育蠶,直到蠶寶寶“上山”結(jié)繭。如清顧祿《清嘉錄》卷四所云:“環(huán)太湖諸山,鄉(xiāng)人比戶蠶桑為務(wù)。三四月為蠶月,紅紙黏門,不相往來(lái),多所禁忌。治其事者,自陌上桑柔,提籠采葉,至村中繭煮,分箔繅絲,歷一月,而后弛諸禁。俗目育蠶者曰‘蠶黨’。或有畏護(hù)種出火辛苦,往往于立夏后,買現(xiàn)成三眠蠶于湖以南之諸鄉(xiāng)村。諺云:‘立夏三朝開(kāi)蠶黨。’開(kāi)買蠶船也。”以此說(shuō)明明清以來(lái)蠶習(xí)俗成,相沿至今。
三、育蠶習(xí)俗
育蠶前須先打掃蠶室,洗滌晾曬蠶具,給蠶寶寶創(chuàng)造一個(gè)清潔的環(huán)境。蠶婦無(wú)論老少皆頭戴紅彩紙折成的花朵,稱為“戴蠶花”,以祈蠶繭豐收。
育蠶先要孵蟻蠶,蠶娘穿棉襖,將蠶種焐在胸口,靠體溫孵蠶,稱為暖種,蠶娘在養(yǎng)蠶期間須獨(dú)宿。當(dāng)蠶蟻孵出后,蠶室內(nèi)須置火盆,保持溫暖,但又不能太熱,太熱則傷蠶,當(dāng)?shù)赜小按盒Q宜火,秋蠶宜風(fēng)”之諺。桑葉揉碎喂食,當(dāng)蠶蟻開(kāi)始吃葉后,用鵝毛拂蟻蠶,大約是為蠶蟻打掃衛(wèi)生。然后晝夜須謹(jǐn)慎小心,室溫的冷熱,蠶寶寶的饑暖,全由蠶娘細(xì)心感受與照顧。葉不能喂得太快,亦不能太慢,太飽太饑皆于蠶不利。蠶一生要蛻四次皮,才變成老蠶,每蛻一次皮叫一眠。三眠后,天氣轉(zhuǎn)暖,蠶也漸漸長(zhǎng)大,火盆撤出蠶室,稱“出火”,蠶皆過(guò)稱以便結(jié)繭時(shí)計(jì)利。這時(shí)家家做繭圓,繭圓用糯米粉捏成,長(zhǎng)圓形,中間略凹,實(shí)心,蒸而食之,象征蠶繭豐收。
又過(guò)五、六天蠶眠,稱大眠,這時(shí)須不斷供應(yīng)新鮮桑葉,不能使蠶寶寶餓肚子,因?yàn)檫@時(shí)是蠶絲質(zhì)量好壞的關(guān)鍵,諺語(yǔ)有“蠶老到熟,葉要吃足”。如當(dāng)年天氣晴好,則本地桑葉不夠,蠶農(nóng)常從桑葉行里購(gòu)買來(lái)自洞庭東山和烏鎮(zhèn)的桑葉,在外來(lái)桑葉進(jìn)蠶室前,蠶農(nóng)先用桃枝在桑葉上拍打幾下以驅(qū)邪祟。
六、七日后,蠶的身體變得透明且不吃桑葉,則把早已準(zhǔn)備好的稻草編的蠶簇,也有用竹制的花簇,一排排架好,蠶要上簇了,蠶農(nóng)稱“上山”。但此時(shí)仍須薄鋪桑葉,恐期間尚有未熟之蠶。鄰里親戚間開(kāi)始恢復(fù)串門,評(píng)看結(jié)繭情況,并互相饋贈(zèng),稱為“望山頭”。贈(zèng)物多為鲞魚(yú)及方形米粉糕,中央置糖或肉餡,稱之為水糕。“鲞”意為“想”,期望蠶繭豐收;“水糕”吳音與“絲高”同音,即生絲高產(chǎn)。如這時(shí)天氣寒冷,則要在山棚下生火盆,叫“灸山”。七天后蠶結(jié)繭完畢,開(kāi)始采蠶工作,稱“落山”。然后把采下的繭子稱一稱,將“出火”時(shí)所稱蠶的分量與繭子的分量比較,計(jì)得利失利。按清《震澤縣志》:“以每出火蠶一斤收蠶十斤為十分,過(guò)則得利不及則失利。”我們常聽(tīng)蠶農(nóng)說(shuō)蠶花廿四分,只是一種好的口彩而已。
自此養(yǎng)蠶全過(guò)程結(jié)束,蠶家大門打開(kāi),稱為“蠶開(kāi)門”,蠶月大忙暫告一段落。接下來(lái)是煮繭,分箔繅絲,“……不中織染,亦另繅絲為絲縛,惟細(xì)長(zhǎng)而瑩白者,留種繭外,仍以繅細(xì)絲。”清時(shí)進(jìn)士錢儀吉的鄉(xiāng)風(fēng)詩(shī),其中有專詠蠶開(kāi)門風(fēng)俗的,其詩(shī)曰:“二月掃蠶蟻,三月伺蠶眠。四月蠶上箔,五月蠶開(kāi)門,落山土地初獻(xiàn)祠,鄰曲女兒從笑嬉,今年去年葉貴賤,上浜下浜眠早遲。桑影初稀榆影繁,蛹香塞屋旋繅盆。新絲長(zhǎng)落知何價(jià),城中人來(lái)索蠶罷。”其詩(shī)雖詠嘉興風(fēng)俗,相鄰震澤亦如此。
四、養(yǎng)蠶的禁忌
因?yàn)樾Q很嬌貴,而蠶民全年的日用開(kāi)支多賴養(yǎng)蠶賣絲所得,所以稱蠶為“蠶寶寶”。吳語(yǔ)地區(qū)有生男稱寶寶的風(fēng)俗,所以蠶農(nóng)視蠶為自己的兒子,可見(jiàn)其呵護(hù)之親。古人為了專心致志地養(yǎng)好蠶,在養(yǎng)蠶時(shí)節(jié)是不許人來(lái)客往的,各家各戶都緊閉大戶,謝絕親朋,怕外人會(huì)帶進(jìn)什么不吉利或不干凈的東西,影響了蠶的生長(zhǎng),這就形成了蠶鄉(xiāng)許多獨(dú)特的禁忌。“三吳蠶月,風(fēng)景殊佳,紅貼粘門,家多禁忌,閨中少婦,治其事者,自陌上桑柔,提籠采葉,村中繭煮,分箔繅絲。一月單棲,終宵獨(dú)守。每歲皆然,相沿成俗”。
蠶月里禁忌頗多:忌油煙薰;蠶婦忌吃腥辣食物;忌飼霧氣天摘的桑葉;忌喪服產(chǎn)婦入蠶室;忌生人闖入;忌在蠶室周圍動(dòng)土鋤草;忌拍打蠶箔,防止財(cái)氣拍光;如有死蠶,只能悄悄揀出,不能言語(yǔ),更不能說(shuō)“死”字。在言語(yǔ)上的禁忌就更多了,在平時(shí)的生活中,忌說(shuō)“僵”(姜)“亮”,因?yàn)榻┬Q、亮蠶、醬色蠶皆是蠶病,說(shuō)“姜”叫“辣烘”,避“醬油”說(shuō)“顏色”;因豆腐諧音“頭腐”而忌說(shuō),雅稱“白玉”;甚至忌“伸”“筍”“爬”“扒”,因扒蠶即倒掉死蠶,又稱倒蠶;忌用破損的蠶匾,“坍匾”就是倒蠶。
這些禁忌有許多是蠶農(nóng)在實(shí)際養(yǎng)蠶過(guò)程中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總結(jié),如忌生人闖入,忌在蠶室周圍動(dòng)土鋤草,忌吃腥辣食物等。大部分語(yǔ)言上的禁忌則反映了蠶農(nóng)寄希望又恐懼的心理,其中有一定的科學(xué)成分。這些禁忌是為了蠶有一個(gè)良好的成長(zhǎng)環(huán)境,以減少疾病的發(fā)生。隨著時(shí)代的發(fā)展,這些語(yǔ)言禁忌已逐漸失去了它原始的意義,人們相沿成習(xí),成了一種語(yǔ)言習(xí)慣,或者說(shuō)是“俗語(yǔ)”化了,已成了當(dāng)?shù)孛耖g語(yǔ)言的一部分。
五、婦女與蠶絲
人類創(chuàng)造蠶神,不管蠶花娘娘、馬頭娘娘,還是先蠶圣母西陵氏嫘祖、寓氏公主……都是女性,這足可以說(shuō)明蠶與女性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以及傳統(tǒng)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男耕女織”的生產(chǎn)方式在民間信仰習(xí)俗上的反映。
在蘇南地區(qū),蠶家女兒自幼跟母親養(yǎng)蠶繅絲,“女未及笄,即習(xí)育蠶”,十幾歲時(shí)已經(jīng)是個(gè)熟練的養(yǎng)蠶能手了。在震澤、盛澤地區(qū),蠶家有女兒人家,娘家在女兒出嫁時(shí)必打制新絲車為陪嫁,新婦到婆家第一年蠶月須獨(dú)自養(yǎng)蠶、繅絲,讓村里人評(píng)看養(yǎng)蠶與繅絲的技藝。養(yǎng)蠶繅絲業(yè)中,婦女是主要?jiǎng)趧?dòng)力,她們獨(dú)擋一面,從養(yǎng)蠶到繅絲而勞動(dòng)耗費(fèi)的體力固然比耕作漁獵勞動(dòng)輕,但更需要細(xì)致與堅(jiān)韌的忍耐力,所以當(dāng)?shù)胤Q之為“蠶娘”。且蠶繭的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占重要比例,“春繭半年糧”“蠶好半年寬”,所以蠶桑地區(qū)的婦女家庭地位相對(duì)江南其它純稻作生產(chǎn)地區(qū)為高。栽桑、養(yǎng)蠶的能手,繅絲技術(shù)精湛的婦女,尤其受婆家的喜歡和村鄰的稱贊,而且還是當(dāng)?shù)毓媚铩⑾眿D養(yǎng)蠶繅絲的好老師,在當(dāng)?shù)氐纳鐣?huì)地位亦比較高。
[1]清《震澤縣志》卷二。
[2]清乾隆《吳江縣志》卷三十九。
[3]清《震澤縣志》卷二十五。
[4]清·郭麟:《樗園清夏錄》卷下。
[5]清·顧祿:《清嘉錄》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