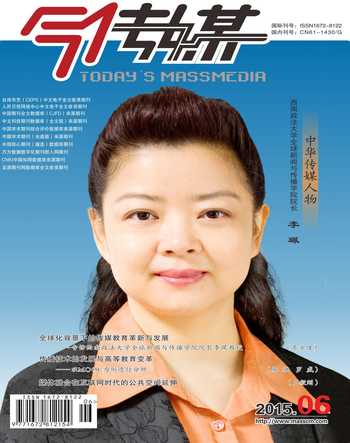“抗日神劇”的傳播倫理研究
張倩
摘??要:“抗日神劇”因無底線地戲說抗戰(zhàn)史、過分美化抗日英雄、過度迎合部分電視受眾的偏激趣味而廣受詬病。之所以受到質疑,歸根結底是因為“抗日神劇”違背了我們的社會道德;無視了廣大中國人民對抗日戰(zhàn)爭這段歷史的價值判斷,傳達出一種低俗的藝術審美觀;從傳播倫理分析的角度來看,它違反了孔子的中庸之道和亞里士多德的中道倫理原則,不利于在國家話語建構中正確地表述中國人民對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一貫立場。這些藝術創(chuàng)作、表現(xiàn)和消費方面的不規(guī)范和價值判斷上的不合理,正是通過電視劇傳播主體的道德倫理而表現(xiàn)出來的。本論文將分析“抗日神劇”所關涉的傳播主體的道德倫理或法規(guī)政策,梳理“抗日神劇”與國家話語的關系,指明“抗日神劇”對跨文化傳播的負面影響。
(三)演員道德
演員是電視劇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者。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很多演員在名利的誘惑下忘記了對社會的影響。一些專家指出,“抗日神劇”的演員更注重自己是否走紅和片酬是否漲價,而不是對表演本身的鉆研[3]。“抗日神劇”出現(xiàn)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不要太扎實的劇本和一線演員”[4],可以節(jié)約成本。像橫店影視城的群眾演員史中鵬,2012年參演了30多部抗日戲,甚至一天在不同劇組“死”了8次。2013年他登上了《中國夢想秀》的舞臺,在節(jié)目里大演特演日本兵的死法。這位演員是抱著何種態(tài)度對待抗戰(zhàn)史的,人們不得而知。毫無疑問,演員除了在劇中塑造人物形象之外,作為一名公眾人物更肩負著為受眾樹立模范榜樣的重任。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著其歷史素養(yǎng)和價值認知。然而當前“重名利輕責任”的眾多演員展現(xiàn)的卻是幼稚的歷史認知和輕浮的歷史態(tài)度,這都在解構著中國社會道德體系,并且影響著中華民族的主流價值觀。
(四)媒體道德
如今社會上有人認為,收視率是媒體的生命線,所以應一切向收視率看。某衛(wèi)視電視劇采購部門負責人邵先生透露說,“我們是根據(jù)收視率和市場調查來采購的,抗日劇的收視率總體還不錯。[5]”眾所周知,媒體是傳播國家意志和民族主流價值觀的重要媒介,其傳播內容直接影響受眾的認知、態(tài)度及行為,具有直接建構或解構社會道德體系的作用。面對“抗日神劇”傳播媒體唯利是圖的傾向,我們應該認識到:電視劇市場的健康發(fā)展,僅僅靠市場自行調節(jié)是遠遠不夠的,在發(fā)揮市場機制的同時,也需要國家適時、適度的調控。
(五)受眾道德
在傳播過程中,受眾不單單是被動接受信息的一方,他們可以發(fā)揮能動性,通過反饋作用于傳播者。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受眾往往被認為處于電視劇傳播的核心地位。“迎合觀眾的口味,滿足觀眾的需求”,便成為了電視劇市場的一種規(guī)則。“抗日神劇”恰恰符合了部分受眾偏激的趣味:欣賞鬧劇的娛樂、享受暴力的刺激、沉迷感官的快感。“抗日神劇”培養(yǎng)出大批低俗的受眾,受眾對?“抗日神劇”的追捧使得這類電視劇擁有廣闊的市場,導致編劇和導演變本加厲地創(chuàng)作和拍攝,從而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huán)。娛樂是必要的,受眾可以借助多種渠道獲得精神愉悅,但是通過抗戰(zhàn)劇尋求刺激和快感,這不是電視劇受眾應有的行為,而是對歷史的背叛和侮辱。因此,增強媒介素養(yǎng)、提高文藝欣賞水平、強化社會道德意識,是中國每一個受眾應當具備的公民素質。
(六)監(jiān)管方的法規(guī)政策
監(jiān)管方,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是國務院主管新聞出版、廣播影視和著作權管理的直屬機構。2009年5月26日,當時的廣電總局指出了一些抗戰(zhàn)劇和諜戰(zhàn)劇的創(chuàng)作問題[6]。公示的發(fā)布在短時間內遏制了抗戰(zhàn)劇和諜戰(zhàn)劇的傳播,但是,2012年中日兩國矛盾因釣魚島的歸屬問題而被激化。日本政府“國有化”釣魚島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中日關系跌入冰點,與此同時,種種嚴格的審查制度限制了穿越劇、古裝劇和涉案劇。在中日關系惡化的背景下,抗戰(zhàn)劇受到了受眾的追捧。2013年開始,“抗日神劇”一部接一部登上熒屏。2013年4月10日,中央電視臺《新聞1+1》欄目盤點并且批評了近期出現(xiàn)的一系列“抗日神劇”。之后國家廣電總局舉行會議,嚴肅批評了部分抗日劇過度娛樂化的現(xiàn)象[7]。2013年5月16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視劇管理司表示已著手對抗日劇進行整治[8]。
以上我們從文藝傳播倫理學的角度,分析了“抗日神劇”在制作和消費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原因。從傳播倫理分析的角度來講,孔子的中庸之道和亞里士多德的中道原則也是“抗日神劇”傳播主體的價值判斷基準。中庸之道和中道原則都主張“無過無不及是最好的,最理想的”?[9]。在本案中,“抗日神劇”是違背這些原則的。針對這一現(xiàn)象,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通過行政手段進行了干預和調節(jié),及時制止了“抗日神劇”的過分行為,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娛樂至上”的偏向。
所以,這些措施符合道德原則或倫理原則,但是如果這種監(jiān)督和管理可以從不定時轉為常態(tài)化,并實現(xiàn)法制化,那么,國家將能夠把控正確的輿論導向和創(chuàng)作導向,“抗日神劇”的傳播就會受到限制,電視劇市場也就可能得以凈化。
三、“抗日神劇”與國家話語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當今,抗日題材的文藝作品通過對內傳播向國內受眾傳播歷史價值觀,宣揚社會道德倫理觀;同時又通過對外傳播向國際受眾傳播中國國家信息,塑造中國在國際舞臺中的形象。更為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抗擊日寇的侵略,是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一部分,是保衛(wèi)祖國、爭取世界和平的重要之舉,這本身就是一種超越國境、超越民族的行為和壯舉,因而勢必引起國外受眾的注目,特別是發(fā)動侵略行為的日本一方。可以說“抗日神劇”的制作和發(fā)行本身就擔負了國際傳播的使命。
“抗日神劇”作為一種傳播形式,其實質是一種國家話語形態(tài)。國家話語是指“國家話語權利實施的具體表現(xiàn)形式,是一種國家傳播現(xiàn)象及信息形態(tài),是一種以傳播國家信息、塑造國家形象、提升國家軟實力、解決國際國內問題為目的的國家傳播行為。[10]”如今,國外受眾可以從中國媒體平臺獲取與中國相關的信息,也可以通過觀看電視劇了解中華文化、中國的國家意識和國家意志。可是,歷史觀扭曲、故事離奇、內容荒誕的“抗日神劇”?表現(xiàn)出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強化了中國人民對日本的憎恨。對此,日本政府也表示強烈的關注。日本官房長官關注中國報紙有關批評抗日劇的報道,“菅義偉官房長官在15日,在議會后的記者采訪會上,就中國政府有關報紙登載了批判抗日劇的文章,發(fā)表了以下見解‘我們關注中國國內這次呼吁展開冷靜的議論的報道。[11]”日本政府由于歷史的原因,不便于直接公開言及抗日題材作品,在回應媒體的時候,也只是曖昧地表述。但這足以體現(xiàn)出日本民眾對這些“抗日神劇”的懷疑態(tài)度,以及日本政府對這些“神劇”負面因素的擔憂。
一名日本大學生在采訪中表示,尊重歷史的抗戰(zhàn)劇將會幫助日本人認識那段歷史[12]。《每日新聞》網(wǎng)頁版登載了《中國媒體報告:抗日劇有變化?批評煽動反日情緒的過度表演》[13],日刊網(wǎng)登載了《中國報紙也批評——中國流行抗日劇亂象叢生》[14]。以上報道表示“抗日神劇”不利于改善中日人民的感情。一些學者主張,“抗日神劇”的缺陷在于“把日本帝國主義與今天的日本人民混同,讓今天大多數(shù)日本人民、尤其是對華友好的日本人民來承擔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zhàn)爭的罪責。[15]”《紅高粱》導演鄭曉龍認為,抗戰(zhàn)題材作品應該表現(xiàn)的是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批判,而不是對日本人的仇恨[16]。可是“抗日神劇”中的國家話語塑造了一個幼稚的中華民族形象,傳遞出來的是用虛幻逃避屈辱的怯懦,這樣不僅達不到弘揚民族精神的目的,適得其反,只會被外部世界懷疑甚至失去別國的尊重。
作為國家話語的一種形式,“抗日神劇”承載著跨文化傳播的使命,也影響著中日友好關系。鑒于此,電視劇的傳播主體須以國家話語理論為指導,提高國家傳播意識,正確面對歷史,增強社會使命感,傳播符合中國社會倫理道德和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信息。面對國外受眾,應有理有節(jié)地宣示中國的民族情感,以理服人,爭取得到國際世界廣泛的尊重,從而塑造一個包容、強大、正義、理性的中國國家形象,提高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
四、結?語
編劇創(chuàng)作傳奇化劇本,投資方過度追求經(jīng)濟效益,演員丟棄職業(yè)道德,媒體一味追逐收視率,受眾享受低俗趣味,監(jiān)管方進行突擊式監(jiān)管,共同造就了“抗日神劇”。市場經(jīng)濟的自由競爭和利益追求也為“抗日神劇”的傳播提供了溫床。但是,謀求經(jīng)濟利益并不意味著可以忽視和放棄社會道德倫理。反之,電視劇的編劇、投資方、演員、媒體、受眾須在遵守社會道德倫理和主流價值觀的前提下,進行規(guī)范的市場活動和傳播行為;監(jiān)管方須予以常態(tài)化的監(jiān)督和管理,保持電視劇市場的有序發(fā)展,調節(jié)和控制社會輿論的走向。抗戰(zhàn)劇不僅僅是一種電視劇形態(tài),更是一種國家話語、一種國家傳播行為,它擔負著跨文化傳播的職責,影響著中日關系,塑造著中國國家形象,擔負著提高中國國際地位的重任。因此,抗戰(zhàn)劇容不得無底線戲說和過度娛樂,不能單純地成為獲取經(jīng)濟利益、宣泄憤恨的廉價劣質產品,更不應淪落為無道德、缺乏理性的、對歷史重大事件肆意曲解或褻瀆的工具。
參考文獻:
- 韓松.抗日“神劇”的神話何時終結?——兼談電視劇評價體系的建設[J].視聽界,2013(2).
- 中央電視臺《新聞1+1》.“抗日劇”可以這么拍?[EB/OL].?2013-04-10.
- 張斌.抗日神劇是怎樣煉成的?[EB/OL].深圳新聞網(wǎng),2013-03-20.
- 韓松落.“抗日神劇”的死循環(huán)[EB/OL].騰訊網(wǎng),2014-01-22.
- “抗日雷劇”頻出?業(yè)內人士:邊看邊罵好過沒人看[EB/OL].新華網(wǎng).2013-04-12.
- 廣電總局關于2009年5月全國拍攝制作電視劇備案公示的通知[EB/OL].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官網(wǎng),?2015-03-06.
- 廣電總局叫停“抗日神劇”?熒屏古裝劇比例也將減少[EB/OL].中國新聞網(wǎng),2013-05-21.
- 劉陽.廣電總局確認整治抗戰(zhàn)雷劇?過度娛樂化將停播[EB/OL].騰訊網(wǎng),2013-05-17.
- 陳汝東.傳播倫理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 陳汝東.論國家話語能力[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5).
- 官房長官、反日ドラマ批判の中國紙に留意[EB/OL].日本経済新聞,2014-08-15.
- 中國抗日ドラマに日本メディアも注目,チャイナネット,?2013-05-28.
- 中國媒體報告:抗日ドラマ、変化の兆し反日感情をあおる過剰演出に批判[J].每日新聞,2013-05-06.
- 共産黨機関紙も苦言…中國で流行「反日ドラマ」のハチャメチャ,日刊ゲンダイ,2014-08-27.?
- 陳國恩.抗日神劇傳播的錯誤價值觀[J].文學教育,2013(10).
- 橫店劇組再掀抗日熱?新一輪抗戰(zhàn)劇積極“去雷”[EB/OL].新華網(wǎng),?2014-11-30.?
- 楊琪.消費文化語境中的熱播抗日題材電視劇研究[D].蘇州大學,?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