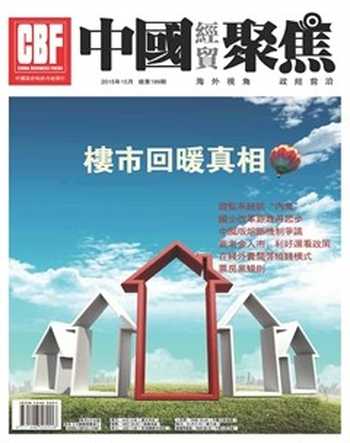存準考核松綁
郁風
央行9月11日宣布,自15日起改革存款準備金考核制度,由現行的時點法改為平均法考核。同時,存款準備金考核設每日下限,即維持期內每日營業終了時,金融機構按法人存入的存款準備金日終余額與準備金考核基數之比,可以低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但幅度應在1個(含)百分點以內。
這是自1998年存款準備金制度改革后,央行首度對這一重要貨幣政策工具的考核方式進行大幅調整。業內人士表示,此舉將增強金融機構流動性管理的靈活性,平滑市場利率波動,它也相當于變相釋放短期流動性,但作用或非常有限。
17年來首度調整
所謂存款準備金,是指金融機構為保證客戶提取存款和資金清算需要而準備的在中央銀行的存款,央行要求的存款準備金占其存款總額的比例就是存款準備金率。存款準備金已成為央行貨幣政策的重要工具,是傳統的三大貨幣政策工具之一。
按照此前沿用了17年之久的時點法考核,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需每日達到法定要求。即維持期內每日營業終了時,金融機構按法人存入的存款準備金余額與準備金考核基數之比,都不得低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
目前,商業銀行需要每旬進行一次法定存款準備金的補、退繳,每月的5日、15日及25日是商業銀行按照規定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余額的時點,每個調整日所對應的存款基期分別是上月月底、當月10日與當月20日,在每個調整時點采用多退少補的方式進行調整。
民生證券固定收益分析師李奇霖稱,時點法考核的缺陷是可能會放大資金面波動。由于受到業績考核等因素影響,月末往往成為銀行存款余額的高峰期,一般性存款余額往往增多,那么對應下月5日就需要補繳一大筆準備金,從而放大資金面波動。
改成平均法考核后,只需維持期內存款準備金日終余額算術平均值與準備金考核基數之比,不低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即可。“每月三次的繳準時點不復存在,銀行繳納準備金的方式更為靈活,不需要提前準備資金頭寸集中應對‘沖時點。”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也認為,“時點”改“平均”之后,商業銀行日常經營中可以更自由地安排資金頭寸,其在資金調度和流動性管理上將獲得更大的自主決策空間。
具體舉例來說,此前,假定某銀行在旬末計算準備金的存款基數為100億元,以20%(今年2月5日降準0.5個百分點后,大型金融機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為19.5%)存款準備金率計,5日后要足額繳納20億元的存款準備金。在此后的整旬內,存款準備金金額都不能低于此數,這是一個硬規定。
而在新政下,銀行每旬末算好要繳納的法定準備金金額(比如20億元)后,后面一旬內不用天天都備著20億元,只要日均達到20億元即可。允許某一日達不到20億元,但也不能比20%低出1個百分點,即不能低于19%。
這意味著,銀行如果遇到意外的流動性需要,可以先把存款準備金支付出去(只要剩下的余額不低于19億元),然后在后面幾天抓緊籌錢,使這一旬內的日均存款準備金達到20億元即可。
東方證券銀行業首席分析師王劍形象地說,這相當于“央媽”給了銀行1個百分點法定準備金(例子中對應1億元)的透支額度,或說信用卡。
釋放短期流動性有限
存款準備金考核松綁,某種程度上可以達到類似降準的效果。有觀點據此認為,這等于央行變相降準1%。就此,央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表示,這是一種曲解。此次改革是考核方法的改革,不是降法定存準率。
有人舉例說,“每個月我孝敬我媽2000元,有一天我媽說,‘哪個月你手頭緊少給我一點也行,但你一年孝敬我24000元不能少,而且每個月也別少于1900元。于是你們就傳說我每月變相少給我媽100元,你們咋想的?”
馬駿稱,新的考核方法與降低法定存準率1個百分點對流動性的影響是不同的。對某些銀行來說,新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囤積流動性的傾向,從而可能降低超額備付金,釋放出一部分流動性,但對整體流動性的影響有限。
據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測算,允許日間低于法定存準1個百分點,而以前必須每日日末達到,相當于給了商業銀行1.1萬億隨時可動用的緊急備付。
齊魯證券研究報告則指出,由于存準率的平均法考核仍在,新政釋放資金的久期很短,因此難以對信貸需求構成支撐。
王劍也分析說,準備金可小幅透支,超額準備金(實際準備金超過法定準備金的部分)需求下降,說“變相降準”未嘗不可,但影響不會太大。尤其目前經濟形勢不太好,銀行是處于流動性過剩狀態,所以超額準備金比較多,在經濟形勢好轉前,這一局面也不會改變。新政后,超額準備金率(目前在2%左右)會出現下降,但別指望下降很多。
銀行資深人士表示,此次考核辦法的改變,不會產生戰略性影響,某種程度上,其影響還不如取消存貸比來得多。實際上,之前取消存貸比也并沒有產生太大影響,原因同樣在于,目前經濟形勢下,銀行面臨的問題是貸款需求不足。
月末高收益理財或不再
盡管對整體流動性影響有限,但存準考核改革被認為還是能起到平抑銀行間市場利率波動的作用。
《中國經貿聚焦》記者拿到的一份方正證券研究報告稱,2013年的“錢荒”事件,促成了一系列“穩利率”政策的出臺,例如去年8月出臺的存款偏離率新規,實質上就是降低了銀行短期杠桿擴張的能力,使得當“季末效應”或“跨節效應”出現時,減少了銀行突發的支付需求或報表應付考核需求,從而使得利率出現了明顯地“被平滑”。從銀行間利率的走勢來看,去年三季度以來其波動率明顯下降。那么,該“平均法”考核的出臺意即當這種“突發需求”真正沖擊到短期銀行資金面時,可以通過這種“彈性準備金率”制度釋放一部分短期資金,從而也起到平抑利率的效果。
王劍還指,特別是在利率、匯率“兩率”市場化進程的背景下,面對或由此導致的存款波動加大,也需要更有彈性的監管指標來應對。此次存準新政,很可能是央行為銀行設計的一種應對“兩率”市場化的措施。
不過,方正證券報告同時指出,“平均法”難以改變利率中期趨勢。這次考核新政的推出也隱含著央行平抑利率中樞上升的壓力,尤其是目前這個時點,利率具有巨大的上升壓力。外匯占款超預期流出(8月末,央行口徑與金融機構口徑外匯占款分別環比下降3184億元和7238億元,均創歷史紀錄)、“穩匯率”操作以及CPI(8月份CPI同比上漲2.0%,創下一年來新高)的未來趨勢,都可能會帶來利率的明顯上升。此舉不太會改變利率上升的事實,一是因“平均法”而多投放的資金為短期資金,短期資金本身就對利率趨勢扭轉的效果不強;二是這種政策真正可以補充資金面的概率偏低。排除短期支付需求的情況,銀行很難通過“平均法”釋放的準備金來長期維持自身的流動性。
齊魯證券研究報告稱,可以預見的是,新政后,在銀行間市場中不同交易主體的資金充裕程度將進一步分化,同業拆借規模將現顯著增長。
王劍亦認為,對于銀行本身而言,減少了超額準備金(目前收益率為0.72%),將其投向更高收益的資產,能夠增加收益。節省的超額準備金流入銀行間市場,有利于壓低銀行間市場利率。這些都是實質性的利好。
而就存準考核改革對投資理財的影響,郭田勇表示,新的考核辦法實施后,將會熨平銀行存貸款的波動。同時,改革以前,銀行以及各種“寶寶們”通常在月末發售高收益理財產品以吸引客戶,不過在新的考核制度下,在月末及季末沖時點高息攬存的動力不復存在,投資者也就很難在月末及季末買到高收益理財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