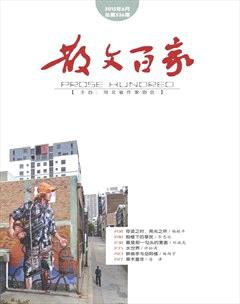《論語》新得: 從小人到君子
●子 君
孔子在《論語》中說“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謙稱自己沒有達到君子境界。我也不得不承認,自己仍未真正擺脫“小人”境地——首先,身份地位是;其次,道德修養是。下面談談如何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
反省·懺悔
竊以為,這是提高道德修養的基礎和前提。
在《論語·學而第一》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曾子說:“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為別人謀劃考慮,盡了心沒有?交朋友,有沒有不誠信的地方?所傳授給別人的東西,自己實踐過嗎?”他提醒我們,反省的功課要勤做多做,尤其在關涉仁愛、誠信、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等重大的道德問題上,更是要時常反省、深刻反省。
再看《論語·里仁第四》,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述而第七》,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對此,我們常常重視前半句,忽略后半句。我們常說“見賢思齊”,卻不言“見不賢而內自省”;我們愛談“擇其善者而從之”,卻不論“其不善者而改之”。是無意地疏忽?還是有意地避諱“自省”和“改”這樣的字眼呢?
比如失眠問題,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可見問題的嚴重和人們的重視。可是有幾個人承認失眠和自己的罪有關,解決失眠首先要認罪悔改呢?人們把原因歸咎于工作壓力大、人際關系復雜、社會矛盾增加等諸多因素,有誰會說是因為我太貪心,太自負,太不遵守上帝制定的規律和原則,太喜歡自以為是地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與己斗、與時間斗呢?又有誰會認為自己違背天道天時也是犯罪,應該認罪悔改呢?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被贊美詩引進教堂,讀到了《圣經》。《圣經》中的罪是廣義的,包括內心的罪惡意念,如貪念、淫欲、嫉妒、驕傲等等,都要認罪悔改。在《論語》中,孔子也對我們提出了“悔改”的要求。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教導我們有錯必改,千萬不可“過而不改”,否則就是大過特過了。《論語》當中還有一段相關的話,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進一步向我們展示了“悔改”的光明前景:“只要反省改過了,就會進入無憂無懼的君子境界”。
孔子是古代的哲人,他十分重視“吾日三省吾身”、“見不賢而內自省”。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也說:“未經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我們現代人難道不更應該反省和懺悔自己所犯下的罪嗎?
出死·入生
孔子在《論語》中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還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圣經》里也多處講到,認罪悔改,就會出死入生,成為一個平安喜樂的人。
只有出死,才能入生。只有在罪里徹底死掉,才能獲得一個圣潔的新生命。
然而,我們卻竭盡全力逃避死亡,甚至對“死”這個漢字也避之唯恐不及,還搬出孔老夫子的話作擋箭牌。孔子確實講過“未知生,焉知死”,可是他也說過“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一般來說,人最“遠慮”的就是死亡。如果把此“遠慮”放到孔子這句話中,就可得出如下結論:人如果不思考死亡這個“遠慮”,就必然會給自己的生活帶來“近憂”。如果再引申一下,把“死亡”引申到“在罪里死”,又可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不治死自己的罪,就會有憂慮愁煩。
以上兩種都提示我們:死,不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須的。我們的肉體生命總有一天要死,這是必然的;我們的罪也總有一天要死,這是必須的。這兩種死都應該得到特別重視。否則,我們現今的生活就會受到影響,就會既憂愁又恐懼,正好與孔子所講的“君子不憂不懼”的境界相反。而一旦我們解決了“死”的“遠慮”,那么我們生活的“近憂”也就迎刃而解了。擺脫了死亡的恐嚇和糾纏,掙脫了罪惡的捆綁和羈絆,還有什么值得憂懼的呢?
從小人到君子
如果我已經“死”了,那么,現在“活”著的就不是原來的我。原來那個“小人”的我已經死了,現在活著的是一個嶄新的“君子”的我。
君子謀道。《論語》中多處講到“道”和“君子謀道”。此道大抵是指人道和政道。他教導我們“君子謀道”,是要我們追求有道德的生活,把主要精力放在“治國平天下”的大事上。我們今天學習“君子謀道”,就是要發揚先人那種執著的“謀道”精神,注重道德,關心大事,追求真理,堅持真理。
君子畏天命。孔子也講天道,在《論語》中,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鮑鵬山教授將此“命”解釋為“天命”,即“天道、自然、宇宙法則”。注重現實、主張入世的孔子,為什么把“知命”也視作“為君子”的必要條件呢?因為一個人如果不知天命不懂天道,即不知道老天為人類設定的規律和界限,他就會無所敬畏,就會無法無天、為所欲為,就會貪得無厭、欲壑難填,就會心理失衡、怨天尤人……總之,他可以做出許多可怕的事情。因為沒有敬畏之心,他無意控制自己,也無法控制自己。這樣的人怎能稱作君子呢?
為了強調敬畏之心的重要性,孔子在《論語》中還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把“畏天命”放在首位,說明“三畏”的分量是不一樣的。“大人”和“圣人之言”之所以也可畏,是因為他們是由“天命”決定的,是符合天道的。一旦違背了天道,凌駕于老天之上自以為是、為所欲為,那么,就會應驗孔子說的“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的話,失去“大人”和“圣人”的地位,淪落為“小人”。另外,在《論語·八侑第三》中,子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就是說,“如果得罪了老天,再怎么巴結祈禱,也是沒有用的”。看來,孔子對老天是敬畏的,對天命是順應的。
君子愛人。《論語·陽貨第十七》,孔子說: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他告訴我們,君子學道德、教化,就會愛人;小人學道德、教化,就容易聽從使喚。他提醒我們,學習道德的目的是為了擁有愛心,獲得愛的能力,去愛別人;而不是讓自己變得更加唯唯諾諾、戰戰兢兢,更加容易被別人指使、奴役和利用。孔子還說“君子不器”。就是說,君子不是供別人使用的器具,而是有思想、有人格、有道德、有愛心的人。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雍也第六》說:“夫仁者,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論語·述而第七》還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說,仁很遙遠嗎?我如果真的想要它,它就會來的。正如孔子在《論語·里仁第四》里說的:“茍志于仁矣,無惡也”。如果真的致力于仁的話,總是能做到遠離惡、棄絕惡的。所以,“從小人到君子”雖然很難,卻是可以實現的,只要踏踏實實地去做。
一旦“小人”的我已經死了、現在活著的是“君子”的我,那么,我就必定會因“欲仁”而“志于仁”,“仁”也必定會不“遠”而“至矣”。
正所謂仁者愛人,君子愛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