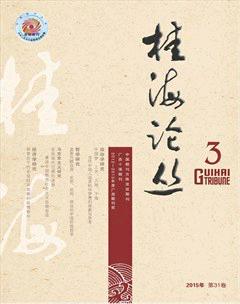論李宗仁“焦土抗戰論”的哲學思想
曾少文
摘 要:“焦土抗戰論”是李宗仁在抗戰時期提出的系統抗日救國主張,反映了他在軍事理論上所具有的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李宗仁的抗日主張是在全面客觀地考察了抗戰中產生的各種問題和分析批判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他運用發展觀端倪出戰爭的發展規律并推斷出中日雙方力量必然在戰爭進程中要發生變化,并提出了抗日是一個長期的發展變化過程,從而科學地預見到抗日戰爭必然是持久的消耗戰。他把中日戰爭過程區分為戰略防御階段和戰略總攻階段,并運用對立統一的辯證法思想制定了“焦土抗戰”的抗日戰略和戰術。李宗仁“焦土抗戰論”的哲學思想對于當時中華民族樹立抗戰必勝的信心,對于推動廣西抗戰和中國人民積極投入世界反法西斯斗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關鍵詞:李宗仁;焦土抗戰;哲學思想
“焦土抗戰論”是李宗仁提出的抵抗日本侵略的戰略主張,它散見于李宗仁在抗戰初期發表的一系列談話、講演和文章之中。以往在歷史研究中對“焦土抗戰論”的內涵、意義、作用及其局限性發表過許多評論,但對其哲學思想的研究卻顯得極為薄弱,特別是對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給予其應有的評價。筆者認為,“焦土抗戰論”充分體現了李宗仁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和軍事辯證法思想,它為推動中國人民積極投入世界反法西斯斗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深入研究李宗仁“焦土抗戰論”的哲學思想,對于我們深入研究以李宗仁為首的新桂系在抗日戰爭起始階段所倡導的戰略、戰術和策略思想及實踐導向所作出的貢獻有著特殊的歷史意義,對紀念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也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全面客觀具體地分析問題的思想
李宗仁考察和分析中日戰爭的性質和特點不是主觀片面地就事論事,而是著眼于從唯物論的方法論的高度去提出問題、認識問題、解決問題。
(一)李宗仁全面客觀地考察了抗戰中產生的各種問題,提出了“焦土抗戰”的戰略主張。“九·一八”事變后,面對日寇的瘋狂侵略,目睹蔣介石妥協退讓所招致的民族恥辱,李宗仁全面地考察了5年來的戰爭實踐,反省5年來慘痛的歷史教訓,痛斥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揭露和批判了“依賴論”、“機會論”、“唯武器論”、“準備論”、“亡國論”等等錯誤觀點的主觀性、片面性,深刻地揭示了日寇的侵略本質。他指出:“依賴論”和“機會論”的錯誤是強調“隱忍自重以徐待國際機會之到來”,期待日本侵略“一俟欲望滿足,中日關系即可調整”而看不到“國際聯盟無力解決中日糾紛”的事實,也看不到日本的侵略本質,不相信民眾自存自立之偉大能力。他批判“唯武器論”和“物質論”的錯誤在于:只看到敵人表面強大,看不到敵人虛弱的侵略本質,他們只相信物質的力量,不相信中華民族為解放而戰的偉大精神力量。他認為“準備論”的錯誤是片面強調中國國力不及日本,一切因亟須準備而放棄抵抗,不懂得“我準備,敵獨不準備嗎?”“其準備速度能低于我國嗎?”進而指出:“不抵抗論實為一切民族危機之厲階……恐中華民族將無解放之一日,更無復興之一日。”[1]17
李宗仁在分析批判的基礎上,提出了符合中日實際和比較全面的抗日主張,即“焦土抗戰”。它不僅包括對日的方針和政策(對日國策),而且包括抗日的戰略戰術(抗日國策)。在對日國策中,不僅指出了什么是我們的對日國策,而且闡述了為什么要確立這種國策,以及它的前途。在抗日國策中,不僅包括軍事戰略方針、而且包括政治戰略方針;不僅包括戰略戰術、而且包括作戰精神。
可見,“焦土抗戰論”是一個較為系統、全面而客觀的抗日主張。李宗仁提出的以“焦土抗戰”求民族復興、求國家救亡、求中日和平、求文化改進的思想是符合國情民意的,因而也是正確的和可取的。
(二)運用具體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日戰爭雙方的基本特點及其矛盾關系,揭示了抗日戰爭的發展前途。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切事物都存在和發展于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之中,一切都以時間、地點和條件為轉移。具體分析的科學方法就是要分析具體的情況,即客觀事物存在的矛盾,以及矛盾產生、存在的條件和特點。“焦土抗戰論”對中日戰爭的分析,雖然沒有能夠做到象唯物辯證法那樣全面和深入,但李宗仁對中日雙方的基本特點還是進行了具體的分析,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1)在軍事方面。他指出,軍事上,“中國軍事設備雖較遜日本,但戰爭勝負之決定,非純賴軍事設備”,“戰爭勝利之主要條件厥在被壓迫者之堅決犧牲精神”,中國的抗戰,是反抗侵略的正義戰爭,必能“踔厲奮發,萬眾一心”,取得最后勝利。就兵力而言,“日本常備兵力不過二十余萬,戰時可以動員者亦不過五百萬,中國之常備兵力,合民團計算當不下四百萬,而戰時可以動員者,至少可達五千萬。”加之中國幅員遼闊,山川險阻,“交通不便,資源未盡開發”[1]21。(2)在經濟方面。日本為資本主義國家,產業發達,“但近來經濟危機,愈形嚴重,赤字財政,超過八萬萬元,國債增加,亦將突破一百萬萬元。他如勞苦大眾生活之艱難,軍需工業之偏在景氣,世界市場對日貨之排擠,燃料糧秣被服軍需品原料之缺乏,在在呈露危機。”戰爭一旦陷于持久,“勢必釀成經濟恐慌,促使其政治斗爭激化。”我國雖經濟落后,民眾務農,日軍雖可占領我沿海城市,但并“不足以斷絕我全民族之生命線。我則農民仍可耕種勞作,力求自足自給”[1]22,(3)在政治方面。日本對外的瘋狂侵略,國內階級矛盾加深,統治集團內部斗爭加劇,使日本政局處于極度不安的動蕩中。反之,中國抗戰為民族自衛戰爭,各黨派,各團體和全國各族人民,均必在抗戰救亡的目標下團結起來,共同奮斗,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4)在國際方面。日本在遠東勢力的急劇膨脹,“與英、美、俄沖突日益激化”,日本與德、意法西斯結盟,日益威脅著世界和平,“浸假而成為全世界人類和平之公敵”。如我國奮起抗日,同時運用國際關系,當能取得國際上“有效之援助”[1]22-23。
李宗仁在具體分析中日雙方的基本特點之后,又在分析的基礎上進行綜合。主要是把中日雙方相互對立的特點聯系起來深入思考,進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概括。他從軍事、經濟和國際三個方面的特點得出抗日的國策是持久戰;然后又綜合四個方面的特點得出持久戰的最后勝利必屬于我。他認為:“我們中華民族無論在人口上、文化上、領土上都是世界上一等偉大的民族,我們民族固有的基礎是雄厚的,民族潛在力是強大的。在這個時候民族的氣魄正如旭日東升,求生的意志最熱烈,奮斗力最頑強。所以,我民族必須抬起頭來,成功為一個獨立自由的民族,實已成為世界上一種大勢,任何力量也是不能阻止的,不管日本武器如何優越,也不問一時戰爭的得失如何,但是中國要復興,這是世界上的大勢,誰也不能阻止,最后的勝利,必歸中國。”由此,李宗仁的焦土抗戰思想揭示了抗日戰爭的發展趨勢,科學地預見到,抗日戰爭必然是持久的消耗戰。這是符合抗日戰爭實際的正確認識。endprint
二、發展變化的辯證法思想
(一)用發展的觀點觀察和分析問題,弄清事物在發展過程中所處的階段。李宗仁在具體分析中日雙方的特點和戰爭的性質以后,又把這些基本特點放在戰爭進程中進行動態考察,端倪出戰爭的發展規律。他根據這些矛盾特點存在著質的不同,在“焦土抗戰論”提出了樸素辯證的發展觀;推斷出中日雙方力量必然在戰爭進程中要發生變化,提出了抗日是一個長期的發展變化過程,并把中日戰爭過程區分為戰略防御階段和戰略總攻階段。他認為,在戰略防御階段,是敵強我弱,是敵戰略進攻的速決戰,我戰略退卻態勢。在這個階段通過攻擊戰的防御,盡量消耗敵人的人力財力,破壞敵人后方交通,使敵人疲于奔命,顧此失彼,陷于泥沼之中。經過積年累月,直致敵人精疲力竭的時候,再做總的反攻,抗日進入總攻階段。總攻階段的結果是暴日必敗無疑,我則收復失地,將日寇趕出國門。李宗仁對抗戰過程劃分為防御和進攻兩個階段的分析,雖然有不科學的一面,因為他把戰略相持階段排除在過程之外,不符合戰爭進程的規律性,但他能夠運用辯證法關于事物是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的思想和觀點去認識問題,從矛盾運動中把握矛盾的特點和發展趨勢,這反映出他對辯證法已有了一定的認識和把握。
(二)體現量變和質變的變化發展的過程。李宗仁對中日戰爭發展過程的階段性分析較好地體現了辯證法關于發展變化過程中量變和質變的思想,從而揭示了中日雙方存在質的區別。他認為,這種不同的質在一定的條件下,必然會產生“彼此消長”的兩種變化。他預見到,在戰爭的防御階段,中國方面的兩種變化趨勢是:第一是向下的消沉變化。這就是地域、人口、資源、軍力和文化的消沉。第二是向上增長的變化。這就是民眾的逐漸覺醒,軍隊戰爭經驗的積累和軍力的壯大,民族的統一和團結向上的政治進步,文化事業在戰爭中創造前進,戰略戰術的適應和國際矛盾逐漸激化有利于我等。在日本方面也有兩種變化。一是向上增長的變化。表現在日軍占領地域的擴大和控制人口的增加,軍事化的經濟膨脹,軍事設備的優越,文化掠奪和政治壓迫加劇。將會引起中國政治格局和社會生活的巨大變異。二是向下消衰的變化。表現在敵軍傷亡增加,戰線越拉越長,兵力分散,士兵精疲力竭,武器彈藥消耗劇增,軍力消弱;對外侵略引起的國內階級矛盾加深,統治集團內部斗爭加劇,政局處于極度不穩的狀態,軍事化的經濟包含極危險的因素,危機擴大;國際矛盾加劇,必遭國際輿論譴責和制裁等。從這些分析中李宗仁看到了兩種趨勢的變化存在著質的差別,因而必然要產生“彼此消長”的變化,認識到我方消沉的東西不是本質的反映,而是舊的質和量,主要表現在量上,因而是暫時的;向上增長的東西是新的質和量,主要表現在質上,是本質的表現,因而在新的條件下,必然呈向上增長的趨勢和變化。日本方面向上增長的的東西是舊的質在特定條件下表現出來的暫時和局部的量;而向下消衰的變化則是本質的表現,因而隨著特定條件的變化而呈總的向下消衰趨勢。據此,李宗仁預見到:“我們實行持久戰,絕不屈服,使他們消耗過巨,補償毫無。那么他們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及國際環境上的危機,必一齊爆發,而陷入窘迫險惡的境地。結果,對華軍事,非全部潰敗不可!”[2]
由此可見,李宗仁的“焦土抗戰論”中對中日戰爭在發展過程中有兩種彼此消長變化的分析,寓含著在量變中包含著質變的辯證法思想。
三、對立統一的辯證法思想
李宗仁根據戰爭的本質和目的,從中日戰爭的具體特點考慮,制定了“焦土抗戰”的抗日戰略和戰術。這些闡述體現了他不自覺地運用對立統一的辯證法指導戰爭的軍事思想。主要表現在:
(一)用“兩分法”分析戰爭過程。世界上的任何事物、現象和過程都包含著相互矛盾的兩個方面,它們既相互對立又相互聯系,并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這是客觀事物的普遍規律,唯物辯證法稱之為對立統一規律。人們運用這一規律分析事物的對立統一關系的方法就是“兩分法”。戰爭進程中的敵方和我方、進攻和防御、主動和被動、持久和速決、內線和外線、運動戰和陣地戰、正規戰和游擊戰、計劃性和靈活性等等都是矛盾雙方的對立統一關系。二者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并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因此,分析戰爭進程能否運用兩分法進行分析和指導戰爭,這是軍事領域中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根本區別。李宗仁在當時雖然沒有自覺的辯證法思想,不知道什么是對立統一規律和“兩分法”,但他已經意識到戰爭中的矛盾關系。在戰爭目的問題上,他把戰爭目的歸結為“保持戰斗實力”和“持久消耗敵人”兩個方面,并對二者的矛盾關系進行了分析。一方面他認為:“要保持戰斗實力,就不必計較一域一鎮的得失,不必死守一條戰線”[3]28要設法誘敵深入,增加敵人不斷消耗;另一方面,他又提倡“不惜重大犧牲,對日長期作戰,不達勝利的目的不止。”[4]29這就是說,只有不惜重大犧牲,有效地消滅敵人,才能有效地保持戰斗實力。因為如不作出犧牲去消滅敵人,則自己的戰斗實力將被消滅。他這樣認識戰爭的目的是辯證的。這就把保存自己實力和消滅敵人去作出犧牲的這種互相排斥的矛盾關系辯證地統一起來了。如果不是這樣認識問題,把戰爭目的的一個方面絕對化,只講消耗敵人,不講戰術,不講保持戰斗實力,就會導致拼命蠻干;反之,如果為要保持戰斗實力,而不敢作出犧牲去消耗敵人實力,則會導致畏敵逃跑。這種只講一點,不講兩點的戰法,是不可能達到戰爭的軍事目的的。李宗仁還從這一戰爭的總的目的出發,具體分析了進攻和防御、持久和速決、內線和外線的矛盾關系。他指出:抗戰如果僅僅采取“抵抗防御的方式,那么我就完全站在被動地位”,我軍應主動求戰,“以攻擊精神代替防御精神,”設法吃掉敵人,從被動地位變為主動地位。他還說,就中日兩國軍事力量特點而言,日本利于縮小戰斗區,我則利于擴大戰線;日本利于兩國主力一決勝負,我則利于隨地抗戰分散敵人兵力;日本利于速戰速決的殲滅戰,我則利于延長持久的消耗戰;日本利于在攻占沿海重鎮,而我則利于內陸及堅壁清野。”[1]21
這就是說,我軍要根據中日戰爭的特點,揚長避短,發揮自己的優勢,創造條件,處理好內線與外線、持久和速決、運動戰和陣地戰等等矛盾雙方的關系。這些戰略戰術原則的提出,生動地體現了對立統一的辯證法思想。endprint
(二)注意區分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要和次要方面。“焦土抗戰論”從中日戰爭爆發以來所出現的復雜情況出發,進一步分析了戰爭過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他在分析了中日兩國之間的民族矛盾、日本國內的階級矛盾、日本上層集團內部的矛盾、中國國內的階級矛盾、國民黨內部集團利益的矛盾和國際上蘇、美、日之間的矛盾等等具體情況。1936年4月17日,李宗仁在廣州對記者發表關于中日問題的談話中首先闡述發動全民族抗戰的必要性,明確指出:“當前中國所最迫切需要者,為整個民族救亡問題,以爭取中華民族自由平等,保衛中華民國領土。”這就說明,李宗仁已經認識到在上述諸多的矛盾中,中日兩國之間的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的矛盾,并抓住這一主要矛盾,首倡“焦土抗戰”的國策,確定了持久戰的總戰略。不僅如此,“焦土抗戰論”還在中日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上對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作了粗略的闡述。李宗仁在分析消耗敵人實力與保存我方實力的矛盾時,提倡“不惜巨大的犧牲”“與暴敵戰到底”。表明了消滅敵人是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保存自己實力則是第二位的,是戰爭目的這一矛盾關系的次要方面。與此相聯系的進攻和防御的矛盾,李宗仁主張“以攻擊精神來代替防御戰”,認為攻擊與防御相比,只有以攻擊精神的防御才能達到有效的防御。李宗仁在這里把進攻看成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防御則是次要的方面。在作戰形式上,李宗仁根據我國地廣人多,但軍事設備和教養較遜日本;而日本則兵力不足,但軍事設備和教養優于我的特點,提出要“在全國四面八方廣泛開展運動戰與游擊戰,輔以必要的陣地戰。”[4]19即是說,陣地戰與運動戰、游擊戰相比,應以運動戰和游擊戰為主,陣地戰次之。并指出:游擊戰是“集小勝為大勝”,運動戰是“以空間換時間”,只有這樣,才能堅持持久的消耗戰,逐漸消滅敵人。說明抗戰的作戰效果,不論采取何種形式,都要以殲滅敵人為主。可見,“焦土抗戰論”對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認識已作出了實踐的初步概括,并成為焦土抗戰的戰略戰術指導原則,在抗日戰爭的實踐中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三)堅持創造抗日條件,促使矛盾轉化。矛盾的主次方面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這是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觀點。“焦土抗戰論”在戰略戰術的論述中較為生動地體現了辯證法這一思想。抗日是在敵強我弱的不利情況下進行的,要解決敵我力量不均、地位不等的矛盾,取得戰爭的勝利,必須實施正確的戰略戰術,創造有利于我方的條件。促使矛盾雙方地位的轉化。“焦土抗戰論”提出了較為實際的戰略主張,并著力在戰爭過程創造有利條件,促使進攻和防御、速決和持久、外線和內線等矛盾雙方地位的轉化。
為此,李宗仁提出了在戰爭實踐中的基本指導原則:
首先,在軍事上實行全面抗戰。就是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同敵人作全線抗戰、全民抗戰、全體抗戰、全國抗戰,用全面抗戰代替局部抗戰。李宗仁認為:這樣,我們可以利用廣大的地域和全國民族的優勢,以爭取主動的精神開展攻擊戰、運動戰、游擊戰、輔之以陣地戰,隨地抗戰或集中兵力主動攻擊一路,從戰場的外線突然包圍敵軍一路而攻擊之。于是,我方戰略上的內線的持久的防御戰,在戰役和戰術上轉變成了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敵人由于戰線過長,兵力分散,顧慮太多,在戰略作戰上的外線和進攻,在戰役和戰斗的作戰上就不得不變成內線和防御;敵人的戰略速決戰經過許多戰役和戰斗的失敗,就被迫改為持久戰。因此,李宗仁提出:“軍事技術落后而自然條件優勢的中國,不必與軍事雄厚的強敵在戰場上爭一日之勝負”,“不與敵人爭奪一點一線之得失”[3]23而是不斷地消耗敵人的力量,避我所短,揚我所長,實行持久的消耗戰,促使矛盾雙方地位的轉化,最終我軍由弱變強,由被動變主動,再實行戰略總攻,取得抗戰最后勝利。
其次,從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加緊配備各種條件,以幫助軍事的發展。李宗仁深入闡明了創造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條件的必要性。他說:要開展全面的持久戰,實現由弱到強的變化,決不是單純軍事的力量所能取勝的,必須實行全國的總動員,方能保障抗戰的最后勝利。為此,李宗仁提出了三點要求:(1)“要求中央領導全國,一致行動”。(2)“政府必須和民眾打成一片”。政府一方面要廉潔政治,鏟除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另一方面,成立民眾動員機構,組織受過教育的青年到鄉村發動民眾,并加以組織訓練。(3)必須有焦土抗戰的決心。就是要“舉國一致痛下決心,不惜流盡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國為焦土,以與侵略者作殊死之抗戰”[1]23李宗仁把軍事與政治看成是矛盾轉化的主要條件,并充分認識到軍事與政治之間相互作用,把二者辯證地統一起來;把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看作救國的希望和促使矛盾轉化的根本條件。堅信在這樣的條件下實行“焦土抗戰”的戰略,“不使日本有步步進攻的機會和步步充實其實力的余暇…則勝利必歸我國,無待預卜。”[4]29這些辯證法思想在國民黨統治集團中出現,是難能可貴的。
四、“焦土抗戰論”哲學思想的歷史意義
“焦土抗戰論”是李宗仁從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向樸素唯物主義世界觀和辯證法思想轉變的重要標志。這種轉變雖然不能說他是徹底的轉變,更不能說他所代表的階級立場和利益有什么根本轉變,甚至可以說,他或多或少地是在維護新桂系集團的利益。但值得肯定的是他這種承認客觀事實的觀點和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焦土抗戰論”所闡述的哲學思想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影響和作用是不可忽視的。當時有人把它稱謂為“成為一項最悲壯的抗日口號”,“行動的旗幟”、“當前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最高哲理”也是不無道理的。
李宗仁的焦土抗戰論發表以后,抗戰初期新桂系在“焦土抗戰論”哲學思想和軍事方略指引下,積極投入中國抗日戰爭,把“焦土抗戰”思想變成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實際行動。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中國戰場發揮了重要作用,有人稱之為“行動的旗幟”。實踐證明,李宗仁及新桂系的抗戰正是在“焦土抗戰論”哲學思想指導下進行的,具體體現在三個層面:
首先,從廣西本地的層面看,新桂系在廣西本地層面最大限度地動員了本省的人力、物力支援抗日。八年中共征調近100萬兵員補充部隊和組建新軍,出兵之多,在全國僅次于四川,而按人口比例則居全國第一位。駐守廣西的部分部隊,參加了桂南、桂柳會戰和光復廣西的作戰。戰爭中,廣西軍隊素質較好,作戰英勇,遵守紀律。endprint
其次,從中國整個戰場的層面看,盧溝橋事變以后,八桂大地即沸騰起來,從桂、邕、梧、柳四市到各縣圩鎮,群眾紛紛集會游行,到處響起“打到日本帝國主義!”“擁護政府領導抗戰!”“誓死保衛祖國!”“寧當抗日鬼,不當亡國奴!”的口號聲。1937年9月18日省府桂林舉行4萬多人的抗日宣誓大會,由李宗仁、黃旭初帶領朗讀誓言,聲震云天,慷慨悲壯。李宗仁親自率全部主力部隊開往華中前線,參加了滬淞、徐州、武漢、隨棗、棗宜等會戰,并依靠廣大的民眾開展了廣泛的抗戰實踐。抗戰中采用長期的消耗戰,以空間換時間。同時還靈活開展敵后游擊戰和運動戰,消滅零散小股日軍,使敵人作戰計劃受到很大牽制;在廣泛的游擊戰爭的配合下取得了臺兒莊戰役殲敵一萬余人的重大勝利;在大別山周圍地區廣泛開展游擊戰,收復了近40個縣,建立起了以大別山為中心的敵后根據地等。廣州淪陷后,我國為取得抗戰的急需物資,加快建設西南國際運輸線,廣西積極響應,被征調100萬民工建筑湘桂黔鐵路和河岳公路,征調200萬人次參加戰時各種勞役服務,為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作出了貢獻。
最后,從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的層面看,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時間最長、空間最廣的東方主戰場。八年中,廣西人民通過堅持持久戰的總體戰略和“焦土抗戰論”提供的思想武器,依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巨大威力和中流砥柱的作用,牽制和消耗了日本的大量軍力,與全國人民一道共同打亂了日本法西斯“北進”蘇聯戰場,南進太平洋戰場的戰略部署,推動和促進了中國戰場與蘇聯、太平洋戰場相持格局的形成,從而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可見,“焦土抗戰論”對于中國人民堅持曠日持久的艱苦抗日,對于歐洲和亞洲其他地區的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起到了戰略配合的重要作用。
總之,李宗仁的焦土抗戰論哲學思想,是抗日實踐與唯物主義哲學的統一。正是由于有了唯物主義思想作基礎,李宗仁的焦土抗戰論在一定程度上對國民黨的抗戰實踐起到了指導作用,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對此,我們應該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給予充分肯定。但是也應指出,由于受到自身階級地位的局限,他的“焦土抗戰”的主張,沒有也不可能象中國共產黨的抗戰主張那樣全面、深刻,既符合抗戰的客觀規律,又符合全民族和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實踐中,我們看到新桂系的抗戰最終走了一條由積極到消極最后走向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因此,對李宗仁及新桂系的“焦土抗戰”思想及實際行動表現,我們也不能估計過高。
參考文獻:
[1]李宗仁.民族復興與焦土抗戰[J].東方雜志,1937,34(1).
[2]李宗仁.焦土抗戰的理論與實踐--李宗仁言論集[M].桂林:全面抗戰周刊社,1938:30-31
[3]李宗仁.李德鄰先生言論集[Z].南寧:廣西建設研究會,1941.
[4]周 煥.李宗仁將軍言論:焦土抗戰[Z].武漢:一星書店,1938.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