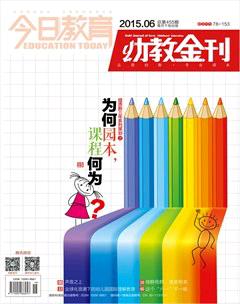聲音之上
胡福貞
家住鬧市,站在陽臺上看過去就是一所三層樓高的小學。從周一到周五,小學上下課的鐘聲鈴響、孩子們的喧鬧讀書聲等都會有節律地響起來,并壓過丁字形公路的車水馬龍聲,清晰有力地傳入家中。家里寶寶出生前,我并沒有太多注意到這些不請自來的聲音,也幾乎不受其影響。寶寶出生后,我很快便發現,窗外這些聲音儼然是一個非常有影響的兒童生活入侵者,其音響之亮、形式之繁、頻度之密,足以成為年幼的寶貝構建和調整自己生活節奏的外部標識。事實也是如此。每天中午12點,小學放學鐘聲響起,寶寶便開始午覺。下午兩點,上課鐘響,寶寶醒來。四點,放學音樂聲一起,到陽臺上去看放學情形是重要的生活內容。寶寶不會走不會說時示意我們家長帶他到陽臺去看那聲響起處。及至自己會說會走時,哪怕正在投入地游戲,也會立馬應聲而起,奔向陽臺,認真仔細地聽校園廣播里傳出的放學歌聲,看朝向自家陽臺的校門打開,小學生們列隊出門,分散開來跑向熙熙攘攘的家長們,然后又漸次走成一條長長的隊伍,迤邐地從不同方向消失,最后校門關上,寶寶像完成一件重要事情般滿足地回到剛才游戲的地方。
對此,我卻是喜憂參半。既然我和愛人打定了主意暫時不搬家,那么寶寶能如此這般地適應環境自然是件好事情。而且,即使只是旁觀,小學校園生活樣態也是社區生活豐富性的重要來源。然而,一旦當我意識到這聲音的有力影響,并開始有意識地關注它們時,我便常常感到了擔憂并開始了引導寶寶有意識的規避。這些聲音中,除了以兒童歌曲建構起的作為小學相對固定的時間性結構之外,不時會突然冒出些“大嗓門”來。特別是在周一升旗時、課間休息中、大型活動期。雖然具體內容我尚不得而知,但這些聲音之鏗鏘、語調之高亢、語氣之武斷,儼然橫沖直撞的巨人,每每讓我們很吃驚很不舒服,有幾次,寶寶就被突如其來的校園廣播通知聲嚇哭了。長大些后,寶寶聽到這樣的聲音就學會了捂耳朵。
同時,作為教育研究工作者,我更不由自主地為生活在這個校園里的孩子們擔些額外的憂愁。他們置身于校園中,并且絕大部分時候他們就是這些聲音的直接受眾,這些聲響是聽得更真切、感受更直接,甚至可以說這些聲音就是沖向他們奔去的。我時常懷著隱憂地好奇著:這些耳朵和心性都尚且很稚嫩、需要溫柔呵護的小學生們,會怎樣去應對那些巨無霸般入侵的聲響?而對于那些活躍在校園中的教師們,又是以怎樣的心態在生產和應承著“大嗓門”?
姑且不論“柔吾色、怡吾聲”是我國傳統文化中關于日常教養的基本要求。事實上,在我國中小學校園中,上課安靜、下課吵鬧是常態(這當然未必正常),而教師們也普遍有“大嗓門”的工作習慣。在大班額的班級和校園環境里,師生盡可能用力地喊出重要的內容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們不關心或顧不上這些“大嗓門”本身的負面功效,從而使這些“高大上”的聲響本身所傳遞出的“口氣與神態”“規訓與懲罰”,成為了頗有影響力的校園教學內容。事實上,這些橫沖直撞的巨人般的聲音不單是在師生身份間建構起了難以逾越的堅硬高墻,更是對兒童精神世界的粗暴侵入、有力示范與強力威脅。由此所營造起的校園文化氛圍,作為小學校園里兒童精神世界的實質上的訓練場,不知不覺地就強塞給了生活其間的孩子們很多東西,給孩子們的人格特質和教養習慣涂抹上了很濃重的色彩。
教育場域內的各種存在能否成為兒童成長的教育性資源,關鍵取決于教育工作者能否對其保持敏感,并能始終圍繞兒童成長的中心對其做出教育性處置。因此,教育專業工作者就像橋,其專業性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對兒童日常生活世界中存在和出現的各種介質保持教育性敏感,并能夠通過教育活動在兒童日常生活的現實世界和發展的可能世界之間架設起橋梁。由此,才可能使得聲音、話語、裝飾、行為等日常生活構件轉化成為教育性要素,發揮出超越日常功效的教育功能。學校教育如此,家庭教育也不例外。家庭教育品質通常也就取決于家長對各種家庭生活資源實際所抱持的教育性敏感。
說到這里,想起了一個禪宗故事。說的是:一個寺廟里住著一老一少兩個和尚。老和尚是修行的,參禪悟道;小和尚是負責日常生活的,灑掃庭除。小和尚從未讀過書,且有只眼睛是瞎的。有一天傍晚,寺廟里來了一個云游僧人要求“掛單”。照佛家規矩,云游僧侶是可以在任何寺廟按照符合該寺院規矩的方式要求食宿服務(即掛單)的。這個寺廟的掛單規矩是來者須贏得與本寺和尚的禪道辯論,否則只能另謀出處。剛好那天老和尚有事無法親自前去,便叫小和尚代他應對。他當然知道小和尚的底細,便囑咐他說要贏得辯論,只需一言不發、手腳比劃即可。小和尚是日常做雜事的,不會參禪辯道,聽說不用言語且也可以贏,就高高興興地代老和尚出門迎客了。
未幾,老和尚便見云游僧人來恭敬辭行。老和尚詢問詳情,云游僧人心悅誠服地說:“貴寺小師傅確實禪道高深。我們倆用的是沉默論答。我先伸出一指,表示大‘道。小師傅便伸出兩指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我又伸出三指,強調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沒想到他非常迅捷且激動的沖我伸出拳頭,分明在說‘九九歸一之根本大道,我服我服!”云游僧人別去不久,小和尚也來到了老和尚的禪房,生氣地嚷嚷道:“這個和尚太無禮了!他一坐下來就沖我伸出一個手指,笑我只有一只眼睛;我想對客人要有禮貌,就客氣地伸出兩個手指,恭喜他有兩只眼睛。可他立刻伸出三個手指,說即使這樣我們兩加起來也只有三只眼睛啊。我氣不過,就沖他揮舞起了拳頭,警告他再說我一只眼我就揍他!哼,我也不是好欺負的。結果,他嚇得立即認輸了。”
這個故事里,非常生動有趣地呈現出了個體的日常反應和知識背景的關聯,特別是話語詮釋系統和學養背景之間的關聯。小和尚和云游僧人同處寺廟場景中,面對同樣的身體語言,具體詮釋卻迥然不同,根本原因就在各自迥異的學養和日常經驗。對于云游僧人而言,他熟悉經典和相應的法道闡釋體系,在禪堂內把論道中的身體語言解釋為佛法之道是再自然不過的了。而小和尚即使身在寺廟,不修禪論道,沒有相應的法理話語體系和詮釋經驗。對于他來說,各色人等和場合都是一樣的,他只能根據日常生活經驗做出相應的現實性反應,難以做出超越性的專門解釋,也沒有相應的轉化意識和能力來逾越其自身的日常生活經驗拘囿。
由此可見,在教育場域內,包括學校、家庭和社會各大教育系統中,各種諸如聲音、話語、裝飾等日常生活存在,以及專門經營的教育設置,要切實成為兒童成長過程中富有滋養的教育資源,從根本上說,仰仗教育者們(教師和家長)對這些資源的轉化意識和轉化能力,能用其教育素能特別是教養智慧將這些存在物做出超越日常存在的教育性詮釋。否則既使用經典圖書和其他優質資源將兒童團團圍住,缺乏資源轉化意識、經驗和能力的孩子們也很難自發地領略其妙處,因為這些客觀性存在物很難自動發揮教養功能。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教師和家長對各種資源的教育轉化意識和轉化能力不單決定著孩子們所能真正獲得的成長資源,也決定著相應的教育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