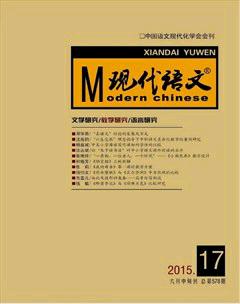現代文閱讀中“小人物”之鄉土農民的心理挖掘
從一般層面上來說,鄉土文學中的農民形象可看作是城市中“小人物”形象的雛形。如果說鄉土農民是中國文化的奠基物質,那么城市“小人物”便是他們的進化形式。所有的現實都不能與歷史相隔離,現當代文學的研究也不是一個獨立的實體,對于現實的研究必須追溯其歷史淵源,對一個民族文化心理的研究更離不開“歷史”,離不開源頭。中國的文學從農村中走來,根植于農村,因此農民的文化心態代表了我們民族的文化特性,從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道德觀念和心理狀態等。
在中國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家,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文化上,農村始終包圍著城市,農民是與自然和土地結合最為密切的人群,因此蔣巍認為“當中國的現代化、城市化影響全國每個角落時,我們的文學還處于‘農村包圍城市的狀態,帶有明顯的農業文明時代的痕跡”。在鄉土農民身上,人與自然相融合,純然的鄉土文學大都顯得和諧與唯美,即便湮滅了可能的深刻與尖銳。譬如沈從文的《邊城》、孫犁的《荷花淀》、蕭紅的《呼蘭河傳》、廢名的《橋》,這些文本中沒有環境作為異質性力量對人的壓迫,人作為主體本身也沒有個性的沖突與身份地位的漂泊差異,人的心靈是完整的,人與人之間是真誠純樸的,現代都市文本中的擠壓、異己、孤獨、惡心、變形等心理情緒在這些純然的鄉土文本中是少有甚至是沒有的。恰如趙園所確認的“廣義農民文化,即使不等同于傳統文化也是其重要部分,且因形態的穩定單純而具體,易于標本化”。這些鄉土文學中渺小的“小人物”們因周遭的和諧而非自主地消解了人生路上對自我對他人的徘徊與思索,因此他們雖然是文本的主體,卻在人格上缺乏主題深刻性。例如汪曾祺《受戒》里的明海和小英子、《大淖紀事》里的巧云和十一子等,他們沒有自主的個性,心中似乎有不如意,但趨于和諧和長久性,作者的主觀意識很快強調性地撫平了這些不如意。類似這種主題和諧引發了中國文學發展形式上現代文學中“小人物”的多重性格的生發,本質上的和諧融入浮華的都市,從而造成了心靈與城市的矛盾與沖突。
以2013年山東卷選取的余華《活著》一文為例,“我”遇到的那位名叫福貴的老人,身份便是一輩子生活在農村的鄉土農民。要深刻把握這一人物形象,就需要學生充分理解鄉土農民的心理特征。首先,老人與牛的和諧關系,包括給牛起了個與自己一樣的名字,文章最后的描寫“炊煙在農舍的屋頂裊裊升起,在霞光四射的空中分散后消隱了。女人吆喝孩子的聲音此起彼伏,一個男人挑著糞桶從我跟前走過,扁擔吱呀吱呀一路響了過去。慢慢地,田野趨向了寧靜,四周出現了模糊,霞光逐漸退去。”小說的環境描寫沒有對人物起到壓迫或扭曲的作用,而是反映了鄉土農民與農村與自然的融合,所以教師可以引導學生拋棄現代生活中夾雜利益的矛盾與爾虞我詐的尖銳,以便更好地理解這段景物描寫的作用。其次,小說講述的是一個人和他命運之間的友情,這是最為感人的友情,他們互相感激,同時也互相仇恨,他們誰也無法拋棄對方,同時誰也沒有理由抱怨對方。講述人講述了眼淚的豐富和寬廣,講述了絕望的不存在,講述了人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著,這就是對小說主題的把握。最后通過小說中的具體描寫,對人物的整體形象就有了深層次的理解。教師在引導學生把握文本的同時,始終要強調此類“小人物”的鄉土本性,抓住這類鄉土農民的本質心理特征。
除了現實意義中的鄉土“小人物”構建之外,另有虛構或記憶中已逝去的鄉土人物形象,也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鄉土形象,這類形象是城市“小人物”的生活對鄉土農民生活的想像,以孫犁的小說最為典型。孫犁的創作已經受到當時都市流行意識形態的干擾,但他的作品仍然以一種純樸與真誠喚起了人們意識形態領域中的美。《荷花淀》里的女人是坐在鋪滿月光的葦席上的,男人與女人爽朗而健康的笑聲都煥發著和諧的詩情,這并非純粹的現實的鄉村,而是富有鄉村味道的意境。孫犁曾說他創作《鐵木前傳》是出于對現實所刺激的童年的回憶,可是相反的是進入城市之后人與人之間卻日趨遙遠,便有了隔閡,于是在《鐵木前傳》里我們看到了兩種不同的格調:一種是童年記憶所給予鄉土的美麗和諧;一種是現實生活所給予異己壓迫的冷淡隔絕。這兩種格調在文本中被作者化為兩種意識的斗爭:就如趙樹理的《三里灣》、《鍛煉鍛煉》中,對農民中一些小人物的自私、狹隘、懶惰有惟妙惟肖的刻畫;《創業史》中梁老漢這一處于中間狀態的農民形象更是對中國農民的高度概括,意識形態的有意介入打破了鄉村固有的和諧性,從而使鄉土風情盡失。這種和諧的消除并不是現代都市對鄉土結構整體的破壞,因為這種和諧的消除是作者意識形態的沖突的結果,而孫犁作品中便保留著主體意識形態對鄉土形式的破壞。
2013年浙江卷選用的李清明的《牛鈴叮當》展示的就是水牛與“鐵牛”矛盾對比下,作者對水鄉的今昔變化的感嘆。“如今,利益的驅動讓這樣的老規矩開始面臨挑戰”、“自然,鑒定最后平息了糾紛,但花去的鑒定費、差旅費和訴訟費加起來遠遠超過幾頭小牛的價值,這一時成了人們茶余飯后談論最多的黑色幽默。”也就是說雖然作者描繪的自然環境還是鄉村,但是如今的水鄉,包括農民的意識已經更接近于城市形態,而這時農民的心理已經不再純粹,他們的心理充斥著自私、狹隘,利益化相當嚴重,于是作者便重構了記憶中古老的水鄉形態。因此,教師在指導學生閱讀文本時,可以在鄉村生活與城市生活的對比中做出褒貶、慨嘆,可以在中華民族的世俗心態的變化中做出褒貶,也可以在自然與社會的關系中做出思索。
無論是現實的鄉土紀實還是記憶中營造的鄉村意境,鄉土農民形象都以輻射狀態發散出現代文學中的多重“小人物”形象。他們身份卑微,以最簡單的勞動獲得生活的保證,常常委曲求全,心思狹隘。無論“小人物”們如何變化,這些精神特質都似靈魂般貫徹在他們的心中。
(范艷君 ?常熟市中學 ?215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