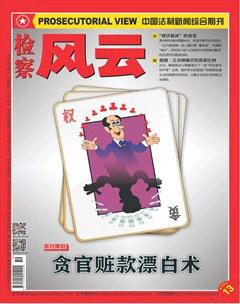德國:立法明確女性高管比例
梁曉軒
德國愈發嚴峻的女性職業發展情勢
歐洲女權運動以來,女性就業問題得到各國政府的空前重視,傳統主婦家庭數量急劇減少,與之相對的,女性群體中的就業人口不斷攀升。英國國際咨詢公司的瓦特和克萊恩·格蘭特·桑頓在2014年進行了一項女性職業發展研究,調查發現:女性的職業發展權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保障,決策層(主要指董事會等高管層)中有女性存在之公司的比例明顯提高,意大利是83%,美國是72%,中國則幾乎所有大公司都有女性高管。相比較而言,德國的數字低于任何一個電氣化國家——德國只有三分之一的公司在高管層有女性管理人員。令人驚訝的是,這一數字甚至低于阿聯酋——以歧視女性而著名的傳統伊斯蘭國家。
美國普華永道的一項調查顯示:2000年德國的職場女性占女性總數的63%,這一數字在2012年升至72%;恰恰與之相反的是,德國企業領導層中的女性數量卻顯著減少,2013年,德國30多家大企業(均為DAX指數構成的企業成員)董事會中女性成員的比例已經從7.8%下降為6.3%。也就是說,德國女性的就業權保障效果明顯,但是女性的職業發展卻狀況不佳。另據德勤的研究,美國女性占500強公司的董事會成員比例為15.7%,而德國女性只占500強公司董事會成員比例的8.2%。上述數據看起來還是比較讓人輕松的,除卻頂尖公司,把更多的普通大公司加入統計數據,其結果更加悲觀。德國經濟研究所2015年1月份的最新統計數字顯示,德國200家大型企業的女性高管數量僅為3.2%。由此看來,女性的職業發展權亟待法制政策予以調整。
眾說紛紜,社會各界呼吁尊重女性職業發展權
鑒于脆弱的女性職業發展情勢,德國民眾表示了憂慮:“一方面德國高舉尊重人權的口號,同時他們卻對許多發生在身邊不合理的事情熟視無睹。”
德國乃至歐洲的女權團體則不斷向企業抗議與施壓,她們呼吁通過立法的形式來保證女性高管的數量。觀點激進的德國的左派政黨和綠黨認為,有必要將企業女性所占比例設定為40%~50%。歐洲最大女權保護機構——歐洲婦女協會的負責人薇薇安·泰特鮑姆表示:“即使在當代,女性的職業發展權仍不能得到有效保障。”職業發展不公平集中體現在晉升機會不均等,也即女性職工缺乏進入職場高層的通道。從外部來看,似乎導致女性很難成為高管的原因在于企業不甚公開的招工和晉升制度,也即缺乏保護女性的細節構建。更深層次地,導致 “重男輕女”的思維大行其道的癥結在于德國社會文化仍然存在著對女性的偏見和歧視。
猶如“玻璃天花板”,女性的職業發展權無法得到有效保證。國際勞工組織頒布的一份報告顯示,通過對歐洲所在企業的雇員工作履歷、學歷、專業技能以及工作強度等因素做出綜合研判后發現,女性綜合得分高于男性。素質高于男性,但職場上卻很難晉升到管理層,這看起來就像一個可笑的悖論。
當然,也有觀點指出,并非女性的職業發展完全受限。致同會計師事務所《國際商業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盡管女性在高管層所占席位不多,但在人力資源總監和首席財務總監兩個重要職位占有絕對優勢,比例分別達到81%和61%,這恰恰反映了女性在特定工作中的特殊天賦——女性在溝通與細節上更具優勢。
默克爾政府強勢推動新法落地
默克爾政府上臺以來,不斷推動女性就業保證向前發展。德國的勞工部長烏爾蘇拉·馮德萊恩計劃通過政府項目增加女性高管的數量,到2018年,使德國企業中的女性高管超過30%。馮德萊恩還表示,企業應當出臺一系列具體計劃、數據和時間表。然而,德國的女性高管比例仍然顯著低于多數西歐國家。2015年的統計數字顯示,德國的女性高管比例僅為3.2%。對此,總理默克爾警告稱,如果企業內部沒有進展,政府將進行外部干涉。
事實上,此后僅僅兩個月,在政府的推動下,德國就出臺了《勞動者性別平等法》。根據該法規定,超過100家德國大型企業被納入監管范圍,30%以上的女性高管成為這些企業必須遵守的紅線。如果企業沒有按照法律規定的去做,則會被監管層介入并強制該違規公司騰出30%的位置以安排女性高管,甚至被處以巨額罰款。同時,該法案制定了一項定期“性別平等報告”制度,除小型公司外,多數企業都要承擔起定期報告女性就業者職業發展現狀的義務。此外,《勞動者性別平等法》還規定了一個過渡期,即2016年是為新法執行的初始年份。
社會的反響與大企業的應對
《勞動者性別平等法》落地后,德國社會給予其普遍的肯定評價。總理默克爾認為,“女性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終于來了!”德國《時代周報》則在3月27日(新法公布后第二天)將規定女性高管比例視為“歷史性的一步”。德國司法部長馬斯稱,新法出臺會將有效調整大型企業的治理結構,這將使德國更加“現代化”。德國家庭、老人、婦女與青年部部長施維斯格則表示,“我確信最終沒有椅子會空下來,因為具備資格擔任這些要職的女性足夠多。”
值得一提的是,在聯邦德國成立以前,民法典曾將烹飪、打掃和撫育后代歸為女性專屬工作。
新法頒布,不僅僅是德國社會的進步,也是對于歐盟消除性別歧視政策的本地化步驟。歐盟規定,最遲到2020年,企業高管中的女性人員比例不得低于40%,否則將面臨嚴重制裁。
如果歐盟成員國的企業未能達到女性高管的最低比例,可能面臨以下制裁:罰金、禁止參與某類公共項目投標、扣減歐盟補貼等。
法案落地以后,很多德國的大企業立即表態將調整公司管理層的女性比例,并著重發展女性高管。傳統的男性主導型企業如汽車制造和互聯網公司則表示了它們的憂慮,一些科技和制造業企業尤其擔心董事會成員性別比例的限制,部分原因在于某些國家的這些行業中女性員工數量相對不足。寶馬公司則認為,政府直接插手公司運營或干涉企業自由。同時,部分媒體和商界領袖也對新法的可行性表示了質疑:即政府如何平衡女性職業發展與商事自由二者的關系,而且如何能避免女性高管成為“政治”花瓶。
向左走還是向右走
“這只是象征,而不是政策”,一部分人質疑新法的微觀執行效果。德國工業協會負責人格里羅公開表達他對于強制規定女性高管比例的看法:“企業固然希望有更多女性擔任領導職務,但出臺硬性規定將適得其反。”部分媒體則認為,單純規定僵硬的數字并不能有效實現女性的職業發展權,應當從把女性從家務中解放出來入手,建設更多的幼兒園、嬰兒看護機構、洗衣場等公共設置,放開束縛女性的無形之手。
另一方面,還有一種聲音開始出現在以德國為代表的西歐,即“女性回歸家庭”。近年來,歐洲經濟呈現不景氣狀態,甚至部分歐洲國家出現負增長,這就帶來了高失業率。歐洲的公司在裁員時,出于避免“歧視女性”的考慮,往往裁掉同等條件的男員工。這樣的背景下,歐洲又一度出現“要女人回家”的聲音,甚至有人認為,不少男性因為政府彰顯女權主義的需要而失去了工作,對待女性就業權出現了消極的態勢。
當然,歐洲的主流仍然是朝著逐漸完善女權的方向發展的。但是,保證女性的職業發展權不僅僅是一個數字或口號。試想即使女性高管在數量上得到了保證,但誰又能確定女性高管能否得到同等話語權和同等待遇呢?如果女性的職業發展權受到侵害,應當通過何種途徑實現救濟?當然,能夠在法律層面上規定女性職業人的發展權,終究是邁出了艱難的一步。真正實現職場的男女平等,依舊任重而道遠。
編輯: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