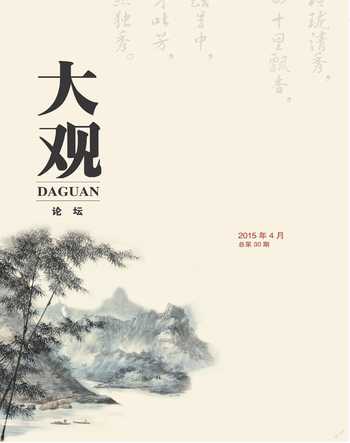淺析“傳神論”對后世美學理論的影響
摘 要:顧愷之的“傳神論”作為中國畫的一個基本理論,一直深刻影響著中國畫的發展。故本文旨在淺析“傳神論”對中國后世美學理論產生的影響。
關鍵詞:顧愷之;“傳神論”;美學理論;影響
在這個藝術覺醒的魏晉南北朝時代,出現了顧愷之的《論畫》、《魏晉勝流畫贊》和《畫云臺山記》這些畫論,標志著繪畫藝術走向覺醒。這些畫論是中國最早的專門畫論,也是中國最正式的畫論,可惜真跡已經流失,今存的均附載于唐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卷五《顧愷之》之后。在這三篇畫論中,顧氏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對當時和后世繪畫產生巨大影響的“傳神論”,使他成為畫史上最早運用“傳神”評價美學現象的大家。“傳神論”深刻影響著中國畫的發展,乃至被歷代美學史學所重視。總之,顧愷之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通過自身的一系列探索,確立了“傳神論”的基礎。以至于對多種形式創作和后世美學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中國繪畫創作具有重大的意義。
一、從歷史的發展角度
從歷史的發展看,從魏晉南北朝到清代出現了許多畫論,也促使中國繪畫理論體系得以形成。但是在眾多畫論中,對中國繪畫影響深遠的并不多。顧愷之傳神論的提出,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著后世美學理論的繼續發展。受顧氏的“傳神論”影響的就有魏晉南北朝時期宗炳的山水畫論,王微的“明神降之”,謝赫的“六法”論,姚最的“心師造化”、“立萬象于胸懷”;唐朝時期張璪的“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張彥遠的“以氣韻求其畫”;五代時期荊浩的“圖真論”;宋朝時期郭若虛的“氣韻非師”,郭熙的“奪其造化”,文同的“胸有成竹”,蘇軾的“身與化竹”;元朝時期倪瓚的“寫胸中逸氣”、“逸筆草草,不求形似”;明朝時期王履的“吾師心,心師目,目師華山”;清朝時期石濤的“一畫論”等。這是從歷史的發展來梳理的。
二、從邏輯關系角度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顧愷之的“傳神論”滲透到了宗炳的山水畫理論中,宗炳提出的“澄懷觀道”的美學思想是對“傳神論”的進一步總結和認識,更啟迪了他在山水畫理論中對“察理”、“存形”及“悟道”的認識。王微在《敘畫》中提出:“本乎形者融靈,而動變者心也。”也就是說畫山水的形時,其形是要融入神靈的,而只有這種具有靈氣生動的畫才能使觀畫之人受到感動。“形者融靈”其實是“以形寫神”的更進一步。謝赫在《古畫品錄》中提出:“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經營位置,傳移模寫”這六法論。此六法是中國繪畫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基本上是謝赫從顧愷之的畫論中條理出來的,但是比傳神論更全面,更精密。強調氣韻其實就是強調傳神。姚最在《敘畫品》中提出:“立萬象于胸懷”。也就是說胸懷中要立萬象,要求繪畫寫心。顧愷之的“傳神論”,宗炳的“以形寫形”,謝赫的“氣韻”說都只是談到了傳所畫對象之神,王微的“擬太虛之體”,“明神降之”談到了主觀作用,而姚最卻提出了主客觀結合。這代表著中國畫論的又一大進步。
在唐朝時期,顧愷之的“傳神論”還影響到了張璪和張彥遠二人。張璪的“外師造化,中得心源”是一個既講內又講外的美學思想,也就是說,由心出發,通過“師”走向造化,再由造化回歸到心源,二者是缺一不可的。他是對姚最的“心師造化”的更進一步發展。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提出的“以氣韻求其畫”的美學思想,更能代表受顧愷之“傳神論”的直接影響。氣韻即“神”,就是抓住氣韻也就是神不放,以神去寫形,就可以達到形神兼備了。
在五代時期,荊浩在《筆法記》中提出了“圖真論”,“圖真論”是《筆法記》的中心理論,“圖真”的本質其實就是“傳神”,是“得其氣韻”,而不同于一般的形似的。“圖真論”是繼顧愷之、宗炳、王微的“傳神論”,謝赫的“氣韻論”之后的更進一步說法。
在宋朝時期,郭若虛在《圖畫見聞志》中提出的“氣韻非師”的美學思想,從字面意思理解是氣韻是不可學習的。但是這里的氣韻實則是已經脫離了技法性的層次,轉移到了創作主體的“生知”方面。郭熙在《林泉高致集》中提出“奪其造化”,實則已經超越了宗炳,這是在強調創作主體的能動性。文同的“胸有成竹”揭示了理性對感悟,主體對客體的主動把握的認識規律。蘇軾的最能表現寫其生氣,傳其神態的思想是出自《蘇東坡集》前集卷十六《書鄢陵王主薄折枝二首》之一的詩句:“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蘇軾的“身與化竹”是文同“胸有成竹”的進一步發展,是由胸中之竹轉向手中之竹的重要一步。
在元朝時期,倪瓚的“寫胸中逸氣”,“逸筆草草,不求形似”的美學思想也是受顧愷之“傳神論”的間接影響。“寫胸中逸氣”是側重于作者主體方面的,明確地將主體心境,情感和思緒的表現提高到了首要的位置。
在明朝時期,王履的“吾師心,心師目,目師華山”的美學思想是姚最的“心師造化”,張璪的“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郭熙的“奪其造化”的更進一步發展。這是在強調創作過程是由一個心到物,心物契合的一個過程。
在清朝時期,石濤的“一畫論”在于主動把握繪畫的根本法則和原理,達到藝術創造的高度自由。石濤的“一畫論”其實就是提倡要尊重自然,尊重藝術家主體的體驗,也就是說畫山、水、林、人都是要生動傳神的。故他說:“畫于山則靈之,畫于水則動之,畫于林則生之,畫于人則逸之。”他還說:“夫畫者,從于心也。
三、結語
“傳神論”的出現,不僅推動了中國歷代繪畫的發展,而且促使中國的民族藝術美學達到一個很高的境界,對中國古代繪畫創作乃至現代繪畫創作及理論產生了極深的影響。所以顧愷之的“傳神論”對中國的繪畫創作意義重大。從邏輯關系來講,“傳神論”的確立,即揭示了繪畫中“形”、“神”之間的依存關系,強調了“神”的追求目標,又重視了“形”在傳神中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說“重神不輕形”。顧氏更提倡要尊重自然,尊重藝術家主體的體驗。以上列舉的受顧愷之“傳神論”影響的理論,其實都遵循著一個法則,就是尊重自然,尊重藝術家主體的體驗。以上各個朝代學者提出的理論都是直接或間接在“傳神論”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所以顧氏的“傳神論”對后世的美學理論影響極其深遠。
【參考文獻】
[1]朱良志.中國美學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陳傳席.中國繪畫美學史[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
[3]李一.中國古代美術批評史綱[M].哈爾濱:黑龍江美術出版社,2000
作者簡介:李金嵐,女,云南師范大學藝術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2012級美術學中國畫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