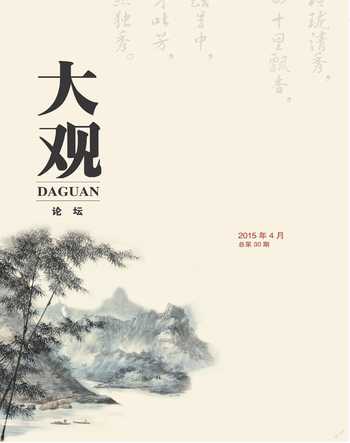自我蔓生長
胡衛(wèi)齊
摘要:中國當代藝術之所以在九十年代受到熱捧直接與國際政治關系的微妙變化分不開。它是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后殖民滲入,而政治波普的流行就是這種文化滲透和政治臆斷的最好例證。于此,對于后殖民文化和犬儒主義中國當代藝術理論界已經批評繁多,我無意再次綴訴。從八五新潮開始,中國當代藝術創(chuàng)作的主流方法論是以“集體經驗”作為切入口。而進入新世紀后,中國當代藝術主流創(chuàng)作的切入點由宏觀的“集體經驗”慢慢轉為“個人肉身體驗”的微觀敘事。其內在的動因一方面是因為藝術圈內部對后殖民文化和犬儒主義的文化反思和批判。另一個原因則是中國社會具體歷史情境的變化。伴隨通訊媒介的發(fā)展和城市化進程加速,在城市中人的個人生存問題越來越凸顯。高樓林立的背后是人的孤立與疏離,商品化的社會中宏大的人文拯救意識也逐步被淡化。每個人都是一種生活在微觀疏離彼此的小世界中。新千年以后,中國當代年輕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方法論則轉向個人微觀的肉身經驗為主,主動隱退了集體經驗在個人身上的烙印。以自我的微弱蔓生長來抵抗著某種不合理的現實,以此方式來表達一種自我對生命、生活的態(tài)度。
關鍵詞:互聯網思維;宅;微抵抗;個體覺醒
一、互聯網的普及與知識大爆炸
1994年中國獲準加入互聯網并在同年5月完成了全國聯網工作。但中國互聯網發(fā)展歷史的元年應該是1997年。在這年中中國三大互聯網門戶相繼破繭而出,拉開了中國互聯網的序幕。直至2010年,中國的網民人數已達四億。如今移動電子設備的快速開發(fā)與普及更讓互聯網滲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互聯網思維成為最新的思維模式,而互聯網成為另一個強大、真實的虛擬存在。
伴隨互聯網普及的同時是信息與知識的普及,也就是現在我們所稱之為“知識大爆炸”的時代。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發(fā)展,互聯網能實現同一消息在全球范圍內的共時存在。可以毫不夸張的說現在我們一天內所能接受到的信息量比80年代的人一年所能接受到的信息量還要多。作為年輕一代的80,90后他們是整個互聯網發(fā)展的見證者,直接參與者以及受惠者。互聯網在帶來諸多便利的同時也在悄悄改變以往人們的生活和交往方式。知識的大爆炸帶來的并不一定是個人知識儲備量的真正增長,反而,在海量的信息和圖像中個人更容易迷失,更容易喪失自我的主體性。
二、“宅”文化的發(fā)展
現在越來越流行的“宅”文化,便是一種互聯網時代下所產生的文化現象。在這高樓林立的時代,人與人的交往越來越陌生化,城市中能輕松給人娛樂的交際的公共空間越來越少。而互聯網的出現正好能快速,便利的滿足生活中各個方面的需求。如今我們足不出戶便可了解世界或得所需。這種便利的滿足也便使人成為一種“電子產品控”。這是一種新型的文化狀態(tài)也是一個由工業(yè)時代向電子時代轉變的特征。所以年輕一代的藝術家敏感的體驗到這一點。以電子媒介作為創(chuàng)作的切入點來體現個人在電子時代的生存狀態(tài)的作品越來越多。新媒體藝術的發(fā)展便是最好的特征,如我們所知的張小濤,廖曉春,胡介名,卜樺,他們的切入點是以一種個人的微觀敘事來體現人在當下社會中人的生存狀態(tài)。其創(chuàng)作方式和圖示都呈現出個人體驗的面貌而不是集體性的,擁有共同視覺記憶的符號。如張小濤所言,從2000年開始他已經從心理學,個人經歷和個人經驗的方法上追溯生命的原點。他的繪畫方法不再是做一個宏大敘事的歷史框架,然后再去找論據添磚加瓦。而是首先從個人的價值展開,其結果是“語言像一個個細胞一樣蔓延,當蔓延到一定的時候,就成長成一種個人的方法和語言系統。”[1]。也正如巫鴻先生所言“美術史就是一個故事,而美術史家要對這個故事進行敘事,每個藝術家都有自己的歷史,慢慢的都可以納入到研究范圍。”[2]
三、個人的蔓生長
2012年由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策劃主辦的“首屆CAFAM未來展”是對青年一代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一次比較整體的生態(tài)考察報告。從中我們不難發(fā)現在這一整體中年輕一代的藝術家對于藝術的思考方式以明顯不同過去老一代的藝術家。新技術和新型城市環(huán)境造就了新一代青年人的感知方式和表達方式,他們對于世界的了解和自我的發(fā)聲更多的是依賴新的電子媒介。生活中獲取信息的方式更便捷也更加呈現出碎片化的趨勢。他們的生活狀態(tài)呈現一種“無所謂”和“隨心所欲”的狀態(tài),是喪失了崇高的文化拯救意識之后的個體隨意表達,這種表達不是一棵如大樹般要給予社會以氧氣和陰涼,而是一種小草式的自我慢慢生長,講述著自我的小故事,敘事著自我的小內心。陳可的油畫始終在講述她自我的成長經歷,個人的孤寂世界是瑣碎的,是迷失在人生旅途中偶然拾起來的關于成長的點點記憶。正如她在今日美術館的展覽中的標題一樣“和你在一起,永遠不孤單”[3],這種不孤單是藝術家自我的內心解讀--她的畫便是她內心的外顯,一個靜態(tài)的自我的始終在場陪伴。焉醒、陶娜、陳蔚、馬秋莎等等藝術家的敘事方式也都是以私人方式在進行。以一種不確定的搖擺狀態(tài)在這個世界中蔓生長。以自我的“微抵抗”來表達一種自我對生活、生命的態(tài)度。當下青年的個體肉身經驗不斷片段的呈現,不斷閃現個人生命中的靈光。正如陳蔚自己說的“我樂于將自己的創(chuàng)作稱為”世界“。這個空間,是可以用來行走、游戲、試驗、研究和消磨的地方。”[4]
四、結語
在我看來以集體經驗作為一個藝術家創(chuàng)作的切入點總會帶有一種崇高的文化拯救意識,一種唐吉坷德式的自我認為偉大的行動。此種方式往往造成在凸顯一個強烈大精神的同時抹殺掉個人精神的自由,這種大同精神讓個人價值消失在它的幕后,始終顯現不出個人的偉大。以犧牲個人價值的集體必定會走向虛無,只有以強調個人價值的集體才能朝良性之路發(fā)展,當代青年藝術家的個體覺醒之勢,讓社會文化更為多元。以自我建構的差異性來逐步對抗主流文化發(fā)展中強調的共有經驗,人之存在本身的合理性和重要性超越一切意識形態(tài),當代青年藝術家正是從生命中出發(fā),強調生命先于其他意識而存在的價值。
【參考文獻】
[1]王婭蕾.重組的碎片:張小濤藝術檔案[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
[2]巫鴻.作品與展場[M]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5.
[3]陳可.和你在一起,永遠不孤單[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
[4]王針.陳蔚自我方式的“集合”[J].藝術匯,20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