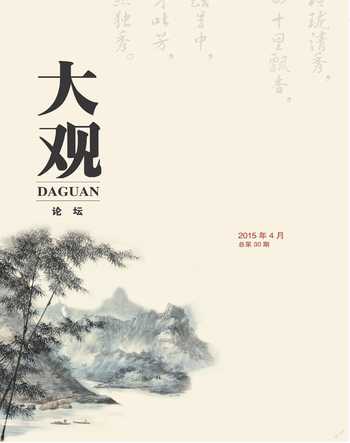《蘇亞人為什么歌唱》
摘要:《蘇亞人為什么歌唱》作為一部經典音樂民族志給讀者帶來一些啟示。文章從“音樂的人類學” 和“主位—客位”雙視角以及通過本書對音樂民族志寫作的一些看法等角度進行了闡釋。
關鍵詞:音樂的人類學;“主位—客位”雙視角
《蘇亞人為什么歌唱》至少給我一種先入為主的視覺沖擊,書名蘇亞人為什么歌唱?在我看來作者做到了“一語雙關”的效果,書名不僅給讀者帶來了好奇感,關鍵還突出了其主旨。本書采用實地考察與資料陳述相結合的形式,是一本關于研究音樂和音樂在社會化過程中角色的書,所試圖解決的問題是蘇亞人為什么以這種特殊的方式歌唱和表演,而不是以其他方式?作者分析蘇亞人歌曲的起源,用蘇亞人自己的音樂故事、神話來闡釋他們對歌曲的認知。本書獲美國音樂學學會獎——用其獨特的視角和方法把已有的觀念如何影響蘇亞人的生活,又如何在其社會生活中發現新的觀念和意義,敘述的很到位。
一、“人類學”的寫作風格是本書一大亮點
民族志是民族音樂學眾多音樂研究方法之一。志即關于人的描述。民族音樂學從人類學中吸收了田野工作的研究方式,并將研究結果以書面的報告的形式呈現,成為民族志。在作者看來,音樂民族志就是對“表演形式的描述”,對音樂表演的描述都離不開音樂人、表演場合、受眾這三個方面。音樂民族志是描寫人類創造音樂的方式,它更像是事件的分析和記錄。音樂民族志是融在民族音樂學中的一種對音樂的記述方式,使學科研究不僅描述聲音,還描述聲音產生和運作的過程。因此,音樂民族志既是理論性的也是描述性的。
“音樂的人類學”是本書一大亮點。在談及音樂人類學與“音樂的人類學”的區別時,音樂人類學是以人類學觀念、方法來研究音樂,通過了解人類族群的社會和觀念化的結構及改變的過程而發展起來;而“音樂的人類學“是從音樂的角度研究社會,認為音樂涉及多個文化和社會生活范疇,是社會和觀念關系的特別結構和闡釋,從文化和社會中的音樂來研究社會。1964年美國人類學家艾倫·帕·梅里亞姆發表《音樂人類學》。書中第一篇即名“民族音樂學”中闡述了民族音樂學的學科理論、歷史現狀(1964年此書寫作時)及研究模式并提出了核心觀念“對文化中的音樂研究。”并認為:“民族音樂學是由音樂學和民族學兩部分共同構成的,音樂的聲音是人類行為過程的產物,而人類行為的過程是由創造某一特定文化的人們的思想觀、價值觀決定的。因此對于音樂的研究兩方面都要相互滲透。而本書中“音樂的人類學”則認為音樂表演創造了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將社會生活看作是一種表演。因此作者的人類學亦可稱為“音樂表演人類學。”即從音樂表演的角度去理解和闡釋蘇亞人的社會。
相對于梅里亞姆的音樂人類學中“對文化中的音樂研究”而言,作者的“音樂的人類學”研究概念顯得比較“另類”,作者并沒有把蘇亞人社區當作一個文化大背景,而是在蘇亞人音樂表演中進行音樂文化研究。因為在蘇亞人的觀念中他們本土音樂的表演并不是我們意識中所謂的地方性的、傳統的音樂表演,恰恰出乎了作者和我們的意料,蘇亞人的歌唱已經成為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和必須長存的狀態。作者順勢而為就音樂是蘇亞人社會生活的真實結構與闡釋方式來勘察音樂。作者的“音樂的人類學”概念重點強調蘇亞人歌唱的表演性和過程性。類似于蘇亞人音樂表演的田野工作有很多,但在當代音樂民族志寫作中卻很少呈現給大眾,但注重音樂本體也是我們年輕學者在實際田野工作中值得學習的觀念。兩者產生于不同的時代背景,必然適應了當時音樂人類學的發展研究環境,存在即便是合理。
二、寫作背景下的“主位和客位”
《蘇亞人為什么歌唱》的創作時期,處于國際視野中音樂民族志理論與實踐過程的中期階段,即由宏觀向微觀的研究方法論轉化的趨向。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之間,美國出現了音樂人類學“音樂學視野”與“人類學視野”兩種觀念的對峙,胡德將音樂人類學的學科屬性定義為“音樂學”堅持學科的研究對象是音樂。民族音樂學田野考察的研究方式從定量的科學試驗轉向定性的經驗分析,即在文化背景中以參與觀察的方法研究局內人的行為。
胡德作為20世紀50年代美國學派的領頭人。最大貢獻是創造了“雙重音樂能力”理論。其理論來源是基于馬林諾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提出的“參與觀察”的理論與方法。受人類學、語言學的影響,人們假設一個文化的音樂風格,就學習過程而言其文化中的語言是相同的。因而,民族音樂學者長期處于某種母系文化就能成為一位地道的當地音樂專家。胡德認為:“在雙重語言能力的學習過程中需要大量地學識和實際操練,才能學好非母語文化語言。那么,在音樂方面我們亦必須用相當的時間經常接觸其他的音樂文化,才能獲得雙重音樂的能力。”胡德所謂的“雙重音樂能力”是“局外人”融入某種音樂文化的一條捷徑,在努力成為“局內人”觀察和研究音樂對象時,還需要不斷恢復研究者的身份。這種深入異文化環境,參與學習并體察音樂,并以當地所具有的音樂符號體系去闡述其音樂真諦,正體現了研究者在調研音樂對象時“主位—客位、局內人—局外人”雙視角相互轉換的能力。
基于本時期胡德“雙重音樂能力”理論實踐方法的盛行。研究側重于從微觀、音樂本體進行分析,對存在和即將消亡的異音樂文化積極進行音樂本體的考察、收集、搶救和描述,而不刻意去尋求和探討其音樂文化背景。安冬尼·西格爾作為美國民族音樂學家,深受其理論實踐方法的影響,本書較少地對蘇亞人音樂文化背景進行深描,只是以敘事的形式把蘇亞人歌唱、舞蹈及老鼠典禮等音樂表演的過程撰寫出來。作者將其“雙重音樂能力”理論實踐方法應用于田野工作中,“主位、局內人”自然是蘇亞人本身,而“客位、局外人”正是作者本人。但是,當蘇亞人告訴安冬尼·西格爾,他們喜歡他時,這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作者完成了身份、雙視角的轉換。作者用專業知識(或許有主觀色彩)解剖、認知蘇亞人獨特的音樂文化,作者起到了橋梁性的作用,至少作者學會了蘇亞人的歌唱,可以帶著歌聲走向我們年輕的學者。
三、結語
洛秦在《音樂中的文化與文化中的音樂》中寫到蘇亞人的“歌唱”并不是我們概念中的歌唱,蘇亞人并不認為他們是在歌唱或從事音樂活動。內在的意義體現在“歌唱”對血緣、家庭的維系,對生產、生存的作用,對宗教膜拜的渲染。外部意義是象征性的,是一種部落的符號,是自我存在的化身,是一種社會化、政治化的意義。從現象上說,這種“內在”和“外部”的意義是功能性的,但是本質上它們是觀念的產物。關于音樂民族志寫作必須具有被調查研究者社會的主題,在實地田野中收集可行性證據后,用自己社會所接受的文本寫作方式撰寫事項。而民族音樂學把人類學的民族志寫作方式應用到本學科上,開辟自己的新道路。音樂民族志就是通過田野工作對地方音樂文化進行系統的描述。它是一種寫作方法,而不是學科理論。
【參考文獻】
[1][美]安尼東·西格爾著.蘇亞人為什么歌唱[M].趙雪萍,陳銘道譯.上海:上海音樂學院,2012
[2]洛秦.音樂中的文化與文化中的音樂[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4
[3][美]梅里亞姆.音樂人類學[M].穆謙譯.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10
作者簡介:王淑華(1990—),女,山東濟南人,揚州大學音樂學院,2013音樂與舞蹈學研究生,研究方向: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