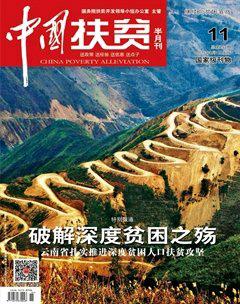村醫眼中的“村醫”
王富剛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作出“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重要指示,也就是中國醫療衛生史上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引起了全國上下對農村醫療衛生工作的極大重視。1968年第三期《紅旗》雜志上刊載了《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改革的方向》一文,隨后《人民日報》頭版轉載了這篇文章,由此“赤腳醫生”作為計劃經濟時期合作社中不脫產的初級衛生保健員逐漸進入了群眾的生活中。1985年,鑒于“赤腳醫生數量膨脹和質量低下,人員培訓、使用和考核缺乏規范,名稱與國際不接軌”,衛生部決定停止使用“赤腳醫生”名稱而改稱“鄉村醫生”(本文簡稱“村醫”)。
筆者印象中的村醫收入高且穩定、有文化、工作體面,在村子里屬于有頭有臉的人物,地位應該不輸于村干部。但是,通過與山東省多位村民的交談筆者發現,在市場經濟大潮下,這些年農村社會的地位觀念也在悄悄地變化著。
老馬今年40歲,1996年參加村醫考試,之后在縣醫院實習三年,1999下半年還未結婚的他就開始到村里任職村醫,到今年快16年了。
老馬在鄰村村衛生室上班,每天騎摩托車來回往返大約30分鐘,白天一直都在衛生室上班,晚上跟鄰村村醫輪流值夜班。因為工作忙,家務活和農活基本都由妻子打理。妻子覺得老馬的工作是治病救人,關乎生命,跟普通工作性質不一樣,所以慢慢也就理解了丈夫的難處,一般家務活不會等著靠著,而是主動幫丈夫減輕負擔。
工作連軸轉
前坡村是附近的中心村,衛生室也設在這里,包括老馬現有2名村醫在這兒工作,輪流值夜班,每2天一輪換,衛生室24小時服務,村民生病隨時可以聯系村醫就診。當問及值夜班是否是上面硬性規定時,老馬說:“縣城周邊的村子,衛生室按時上下班,人不多的時候就關門回家休息了,不是24小時值班制。”
因為工作,老馬的飲食非常不規律,晚上下班沒有固定時間,經常八九點才回家吃飯,要是值夜班的話吃完飯也就到了晚上十點左右。這也使得老馬的體重飆升到了80多公斤,而身高只有1.67米的老馬現在看上去已經“圓圓的”了,血壓也偏高很多。
“工作連軸轉,給身體帶來了傷害。那時候,老馬一個月工資500多元,而去青島打工的小青年一個月都賺到2000多塊了。”在剛結婚的那幾年,老馬的妻子沒少因為這個跟他鬧矛盾。
職業晉升難
交談中老馬反復說:“我們村醫也得參加正式考試”。
其實可以覺察到,老馬在對自己職業認同的同時也因身處農村醫療衛生網絡最底層,社會經濟地位得不到普遍認可,心存失落與擔憂。老馬深知,以后村醫都要向“助理醫師”逐步過渡,但是擔心“助理醫師”很難考,擔心自己的學歷背景會成為職業晉升通道上的一個障礙。“一般的醫學校國家不承認,像我們以前的學校就不一定承認,所以不確定會不會有資格參加考試。”通過考試晉升職稱,對很多學歷較低的村醫來說既是機遇也是難關。
現在村醫的技術水平相對鄉鎮醫院醫生的水平還是有不小的差距。老馬說:“為提高村醫的臨床水平,每年鄉鎮醫院都給村醫開展培訓,時間大約2個月左右,培訓形式類似于開例會,中間還會插入縣醫院1個月左右的培訓,主要是通過講座的形式,由專家分享臨床上的一些經驗。”
“以后隨著村醫與鄉鎮衛生院醫生差距的逐漸縮小,可能會逐步過渡到鄉鎮醫院醫生輪流到村衛生室執業”,老馬對這些未來可能的變化充滿期待。
心理不平衡
老馬的工資主要包括基本工資、診療費、公共衛生人頭費等。從最初的每月200多元到后來的500多元,直到現在的2000元左右,與全國GDP的增長速度相比是有些緩慢。老馬說:“基本工資大約每月四五百塊,打針輸液等能賺一些注射費,公共衛生在順利完成上面派的任務后能分一部分人頭費。但是,為了在公共衛生工作上對村醫形成約束,上面對完不成任務的村醫有很多處罰和扣費措施,人頭費對村醫來說,拿得并不輕松。”
提到央視的“尋找最美鄉村醫生”活動,老馬提高了語調:“你讓‘最美鄉村醫生上電視是個好事兒,但是村醫也是普通人啊,也得養家糊口吧?”
“國家光要求我們有高尚精神,無私奉獻,卻把改善提高村醫待遇擱置一旁了,‘文教一體成了句空話,村醫跟鄉村教師的工資現在相差太多了。”老馬妻子說。
老馬的很多同行也都在發牢騷,抱怨村醫跟教師在收入上的懸殊太大,這幾年村醫為此幾次集體上訪,大部分反映上去的問題最后也都不了了之。
訪談過程中,老馬夫婦不止一次拿鄉村教師與村醫作比較,并表示心里感覺很不平衡。對于工資待遇的期待,老馬說:“不指望有村里小學老師一樣長的假期,也不指望工資超過他們,只要能縮小一下差距,工資漲到3000元以上就謝天謝地了,我們的辛苦也算沒白費。”
筆者注意到,在農村,經濟收入的絕對數似乎并不能引起村民們多大的興趣,倒是親朋鄰里相互之間的比較無處不在,在這樣一個低頭不見抬頭見的熟人社會環境里,無論是金錢收入還是名聲榮譽,少人一點就是低人一等。農村人好像并不看重城里人在乎的生活水平、錢多錢少、有房沒房、做什么工作,而更重視通過這些方面的對比來獲取優越感和“臉面”。
妻子的埋怨
“丈夫原來在離本村更近的一個村衛生室上班,后來上面要求調到較遠的前坡村工作。以前前坡村調過去好幾個村醫,后來都走了,因為前坡村本村的村醫私下里開設‘家庭藥店賣藥,把上幾任同事都‘氣跑了。”老馬的妻子說,“私下開家庭藥店賣藥,影響了村衛生室的收入,市場被偷偷瓜分,其他村醫的收入無形中也就被侵蝕了。”
“自從調過去之后,丈夫一年到頭沒有休假的時候,白天都得去上班,晚上還經常值夜班。值夜班時他就睡在衛生室,村子里只要有人生病要求就診,就得半夜爬起來去村民家問診。”妻子說,這些年跟著丈夫吃了不少苦頭,尤其是每年除夕,只留娘倆在家過年,吃頓團圓飯都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endprint
丈夫的工作又苦又累又耗時間,一年到頭沒有休假,家里的農活顧不上做,孩子也沒時間照料,并且待遇較低。老馬妻子感嘆道:“沒尋思這輩子還干了這么個活兒。這兩年待遇改善了,前些年氣得我經常跟他吵架。” 筆者在其他村民那里得到證實,前幾年老馬妻子確實多次跟他鬧離婚,還有幾次甚至“逃回”了鄰村的娘家。在平常人看來本該生活寬裕而體面的村醫家庭,卻多次面臨破裂的危險。近些年老馬的待遇有些改善,妻子也在家人和鄰里的多次勸說下,慢慢習慣了丈夫這種工作模式,接受了現實。
公共衛生憂慮
老馬說,現在村醫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搞公共衛生上,雖然能賺人頭費,但工作壓力著實有點大。拿健康檔案來說,前坡村衛生室2個村醫需要完成周邊幾千口人的健康建檔工作,這占據了村醫很多本來用于診療的時間,給村醫增加了不小的負擔。
老馬說:“臨床診療的工作很輕松,看看病寫寫單子就完了,現在主要是這個公共衛生太累人了。現在除了健康檔案,高血壓和糖尿病等患者都得3個月定期隨訪一次,這么多人口,完全按照上面規范來根本干不完。”
“咱這邊2009年搞的居民健康檔案,一開始健康檔案的模板幾天換個樣兒,省里一個模板,縣里一個模板,導致咱們下邊無所適從,所以出現了大面積的‘糊弄公事現象,檔案信息都是胡編亂造的。那段時間都不知道改過多少遍了,天天往鎮上跑還是搞不明白,廢了很多精力!反而是偷懶的村醫省事兒了,要改的話就統一改一下就好了,像我們這些認真改的就得挨個重新核對。現在國家讓村醫對居民健康檔案進行重新核對、重新填寫,已經改過一部分,而且省縣監管機構這次進行了電話抽查。”
當筆者問到“現在檔案信息都是挨家挨戶進行測量填寫,實打實的嗎?”老馬先是支支吾吾,然后“嘿嘿”笑了一下說:“反正我是認認真真填寫的”。由此看來,雖然當地又重新對健康檔案進行了核對更正并加強了質量監督控制,但是健康檔案的質量仍然值得質疑。
控制大處方
現在的處方信息全都輸入電腦系統,鄉鎮醫院依據系統信息對村醫執業行為進行監督管理。當地監管部門控制處方額度最高50元,超了的就認定不合格。為了規避不合格處方帶來經濟利益損失的風險,實際操作過程中村醫不斷拆解處方,將超過50元的大額處方拆成多個小額處方,既避免了大額處方遭處罰,又獲得了更多的按處方數計算的診療費。村醫這種應對策略使得地方監管部門出于減輕村民醫療負擔的政策初衷完全失靈。控制大處方的努力反而產生了額外的財政投入,進一步加重了本來就捉襟見肘的地方財政負擔。
公共服務難題
老馬說,現在國家越來越重視村醫的公共衛生職能,可能以后會將基本醫療的職能全都收歸到鄉鎮醫院。“可是,村醫這個工作還很關鍵啊,雖然水平比不上城里醫生,但是大家有個小病都得指望村醫,不可能大老遠地跑到鄉鎮醫院縣醫院看感冒吧?再說,即便方便到鄉鎮醫院,一個鄉鎮那么多人口,小小的鄉鎮醫院也根本服務不過來!即便醫院擴建,現在鄉鎮醫院財政都管起來了,醫生吃死工資,根本沒有工作積極性,那么多人一下子涌到鄉鎮醫院里,還指不定會出什么亂子呢。”老馬妻子的一番話道出了農村衛生改革的很多現實困難。
對此,筆者的觀點同老馬妻子是一致的,認為門診應當下移,剝離鄉鎮醫院的門診業務,全都歸總到鄉村衛生室,只保留鄉鎮醫院的住院部。門診下移將為轉診服務建設創造環境,全面發揮村醫的“全科醫生”功能,發揮村醫向上推薦病人,給病人推薦醫院的轉診功能。這樣既能養活鄉鎮衛生院,減輕醫院負擔,又能增加村醫的門診業務量,從而增加村醫的收入。但要是按現在的政策趨勢“剝離村衛生室的基本醫療職能收歸到鄉鎮衛生院”,這樣衛生院服務能力不增加的情況下,難以收治那么多涌流上來的各村門診患者,并且現在財政給養體制下衛生院醫生很難有積極性去提高診療服務水平和質量。相應地,村衛生室基本醫療剝離的情況下,會大大降低村民就診的便利性,耽誤一些常見病的治療,使得“看病難”的現狀進一步惡化。村醫雖然會因此專注于公共衛生服務,但是收入提高難度大,不利于村醫積極性的提高。
村醫人才難留
“村衛生室就2個人,很多事情忙不過來。但是我寧愿累點。”老馬說。
從合理分工的角度來講,擴充人力是理所應當的事情,可是老馬為什么“寧愿累點”呢?
老馬說:“3個人倒是正合適,但是人越多掙錢越少啊!”
農村衛生室因為條件差,收入低,職業晉升空間小,所以留不住人才的問題常常為外界所詬病。村衛生室平臺低是其一,但老馬道出了一個更重要的原因:現有工資結構和盈利模式下出現了“僧多粥少”的現象,因為就醫需求總量基本固定,本地村醫對新進人員就有強烈的排外動機。各地嘗試定向培養等方式為農村輸送衛生人力資源的努力是對的,但是“種豆得豆”也需要合適的土壤,不改革工資收入結構,衛生人力資源不但留不住,也很難進得來。
基本藥物短缺
基本藥物實施零加成、雙信封采購等政策,當初基本藥物制度的設立由頭之一是藥物短缺。然而,“衛生室現在都是基本藥物,不讓賣非基本藥物,本地基本藥物目錄2015年新加了50種,但是兒童用藥物短缺還是比較厲害”,老馬說。低價藥物政府制定最高零售價限制,使得市場根據藥品生產成本和供求及競爭狀況調節價格的機制失效,很多藥企生產低價藥物的積極性受挫,難以保證藥品的供應。筆者了解到,2014年國家發改委宣布取消了533種低價藥的最高零售價。深入分析則發現,533種低價藥與520種國家基本藥物高度重合,276種藥物同屬于兩個目錄或清單,換句話說,53%的國家基本藥物供應得不到保障,需要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來保證供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