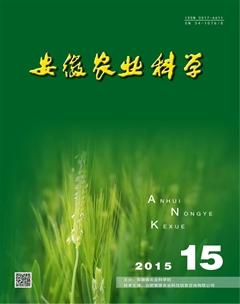河流生態環境需水量及關鍵技術研究
李昌文 康玲
摘要 綜述了河流生態環境需水量的國內外研究進展,從基礎理論和計算方法兩方面探討了熱點問題,圍繞生態水文模型、驅動機制與演變規律、河流生態資產與生態環境需水量的概念關系模型、生態調度模型和生態流量預警等關鍵技術,提出了河流生態環境需水量的研究模式;對未來的相關研究做了展望。
關鍵詞 生態環境需水量;關鍵技術;驅動機制;生態資產;生態調度
中圖分類號 S181.3;Q148;TV213.9;P34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517-6611(2015)15-222-04
Study on Key Technologies of River Ecoenvironment Water Requirements
LI Changwen,KANG Ling (College of Hydropower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Hubei 430074)
Abstract The advance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on riverine ecoenvironmental water requirements (EWRs) are reviewed.The theory and estimating method of EWRs are discussed.Based on the technologies including ecohydro model,driving mechanism,developing laws,conceptual relational model between river ecological assets and EWRs,ecological operation model and warning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flow,the research frame of EWRs is proposed.Finally,future orientations of EWRs are summarized.
Key words Ecoenvironment water requirements; Key technologies; Driving mechanism; Ecological assets; Ecological operation
河流生態系統是河道內、外生物與環境之間進行物質交換和能量流動的統一整體,是一個受自然和人為雙重影響的復合生態系統,是一個生物組成、結構和功能都依賴于水文情勢(或流量情勢)的連續系統[1]。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許多河流被大壩和水庫所攔截,用于調節年際、年內和區域不均的徑流情勢,以滿足發電、灌溉、引水等人類用水需求。這使得河流的天然水文情勢受到強烈干擾,致使全球范圍內河流生態系統日益退化,故需要在河道內預留適宜的生態環境需水量(Ecoenvironmental Water Requirements,EWRs),以維持水環境安全和河流健康。因此,河流EWRs的基礎理論、計算方法以及因此涉及到的關鍵技術研究將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尤其是在河流的水生態修復和水資源的科學配置實踐中。目前,該研究已從基于河道物理形態、水生物需水要求計算最小、最佳生態流量,發展到基于河流健康視角計算具有可變范圍的生態流量;尚存在的主要問題有河流EWRs的內涵不清晰,計算方法不完善,關鍵技術尚待開發等。總體上,目前的研究主要關注維持河流生態系統臨界條件下的單一EWRs,對河流的生態水文節律及生態需水量的演變規律關注不夠;需要調整研究重點,從河流生態系統與水循環的互動-適應性機制等方面入手,全面剖析河流EWRs。
1 研究進展
隨著對河流生態系統認識的不斷深入,河流EWRs的研究在國內外均得到了全面發展。國外的研究可分為萌芽、逐步發展和完善3個階段[2-5]。①萌芽階段:1960s之前,提出了最早的EWRs概念,并嘗試了EWRs的定量研究;②逐步發展階段:1970s~1980s末,相關概念得到普遍認同,人們開始從不同角度對其研究,先后提出了基于水文學、水力學和生境適宜性評價的系列方法,其中Tennant法奠定了該方向的理論基礎;③完善階段:1990s后,主要針對河流整體性展開研究,完善了相關理論和計算方法,許多國家將EWRs列入法律法規。基于生態-水文的耦合作用機理研究、基于3S的EWRs研究、河流生態系統與水循環的互動-適應性機制研究、基于水資源配置的EWRs優化調度等是近幾年相關研究人員關注的重點。
我國EWRs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初步認識、探索、理論研究、理論與實踐相結合4個階段[6-8]。①初步認識階段:1970s,開始探討河流最小流量問題;②探索階段:1980s,主要集中在宏觀戰略方面的研究,提出了生態用水、環境用水等概念以及相關計算方法;③理論研究階段:1990s,水利部提出在水資源配置中考慮生態環境用水,EWRs的理論研究逐漸展開;④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階段:2000s以來,隨著EWRs理論的日漸成熟,研究的視角與重點開始轉變為基于水循環、水量與水質耦合、自然與經濟系統用水關系的協調研究,研究范圍從西北地區向東北地區、南方地區和西部地區擴展,計算方法也不斷增多與成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和成果,其中《中國分區域生態需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近年來,圍繞EWRs的配置、水庫生態調度、時間變異性與空間移植性等方面開展了諸多研究[9-10]。
2 熱點問題
當前河流EWRs的研究熱點主要集中在基礎理論和計算方法兩個方面。
2.1 基礎理論研究
2.1.1 EWRs的理論基礎。河流EWRs是在多學科、多理論基礎之上逐漸形成、發展和成熟起來的。①系統論:從河流生態系統的思維揭示了徑流與生態相互作用的內在規律。②生態水文學:通過對水資源(包括“藍水”和“綠水”)空間分布規律的定量模擬與計算,為EWRs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論基礎和技術手段。③生態學:其中的整體性原理和物種耐性理論分別對EWRs的研究尺度和閾值特性進行了說明;物種多樣性原理要求EWRs應具有不同的等級和時間變化特性,以維持水生生物的多樣性;景觀生態學理論要求EWRs應包含一定的生態洪水,以維持兩岸一定寬度的植被帶。④水文學:水循環與水量平衡原理是開展EWRs研究的重要基礎,而通過EWRs的研究,可揭示水循環的內在規律,促使水文過程向有利于河流生態系統和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方向發展。⑤地帶性理論:要求EWRs具有空間變異性,而不同比例尺的專題地圖可為EWRs的計算提供本底數據。
2.1.2 EWRs的概念辨識。河流EWRs是一個復雜的概念,國內外至今仍沒有形成一個明確而又統一的定義[1,7,11],出現了諸如生態用水/需水/流量、環境用水/需水/流量、生態耗水、生態配水等許多概念。綜觀國內外EWRs的研究成果,筆者認為,河流EWRs是指基于河流健康的具有適宜數量、質量以及時空變化特征和閾值特性的水。該定義綜合了EWRs的水量、水質和閾值三重屬性,強調了時間和空間的變異性以及變化范圍,即認為EWRs是一個具有閾值的變量,EWRs的確定還應以維持河流健康為目的。
2.1.3 EWRs的機理分析。河流EWRs存在最大、最小兩個閾值:超過最大值將發生洪澇災害,低于最低值將使河流生態系統受到不可逆的損害,只有處于適宜范圍內,才能維持河流生態系統的健康。同時,河流EWRs受水資源的數量和質量、水體的生態環境功能、社會經濟的發展規模、水資源的開發利用程度、水生生物的水質水量要求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因此,EWRs的閾值和影響因素都將是研究的重點,尤其是如何科學合理地確定EWRs的閾值大小仍是一個世界難題。
2.1.4 EWRs的基本特征。河流EWRs是一個具有生態、環境和自然屬性的概念,反映了河流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承受和恢復能力以及維持社會經濟發展的能力,具有以下特性。①可持續性:EWRs的前提是維持河流的特定生態環境功能,以實現人水和諧共存。②時空性:空間性表現為EWRs在不同的地理分區(如干旱區和濕潤區、河道內和河道外、同一河流的上、中、下游及河口)有所差異;時間性表現為EWRs在年際和年內的不同時段有所差異,且隨環境治理、生態修復的實踐,EWRs的外延、內涵和計算方法都會有所改變。③臨界性:在特定的時空尺度內,應保證河流生態系統所需的最低EWRs。④經濟性:隨著淡水資源的逐漸稀缺,水資源的自身價值也將越來越高。而在河流污染物的稀釋自凈中,EWRs不僅需要考慮其自身價值,還應考慮污染物的處理費用。因此,EWRs應是最“經濟”的水量,而非越多越好,當然也不是越少越好。
2.1.5 EWRs的分類研究。根據河流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可將河流EWRs分為河道內和河道外兩部分;根據空間變化特點,可將河流EWRs分為區域空間和立體空間兩部分;根據所掌握的數據和水生棲息地維持水平的時間維度,可將河流EWRs分為歷史、現狀和未來三部分;根據要實現的目標,將河流EWRs分為維持不同情景、現狀水平、天然水平、最大目標、最低目標、適宜目標和優化目標的需水量。河流EWRs的具體分類如圖1所示。
2.2 計算方法研究
估算與評價河流EWRs一直是研究中的重點和難點,評價指標與計算方法還沒形成統一的體系。目前,全球約有207種評估方法[12],大致可分為水文學法、水力學法、生境模擬法、綜合法、整體分析法及其他方法,如表1和圖2所示。從表1可知,這些方法的復雜程度和對數據的要求總體呈增高趨勢,方法越簡單,操作越容易,研究得也越成熟,其方法種類也越多,如水文學法的種類(30%)遠多于整體分析法(7.7%),但是其生態驗證也就越欠缺;方法越復雜,對河流生態系統的需水要求把握越精準,但卻需要大量的人力、財力等支持,耗時長,不易操作,區域適用性強,不利于推廣使用。從圖2可知,澳洲、北美和歐洲的評估方法最多,研究最為廣泛和深入,其中水文學法、綜合法和其他方法在歐洲最多,生境模擬法和水力學法在北美最多,整體分析法在澳洲最多,相對而言,亞洲的各類研究方法較少。因此,我國應加強該領域的研究。雖然以上各種方法的種類統計會有所偏差,尤其是近年來又提出或改進了很多新的方法,但整體上還是反映了全球各洲的研究水平。不同的研究方法各有其優缺點和適用范圍,選定評估方法應考慮河流的類型、收集資料的費用和困難程度等因素。此外,先前的研究注重從應用方面選取適宜指標,近期的研究則開始注重從河流生態系統的整體性開展評價。考慮到我國生態水文數據較為缺乏的現實情況,簡單易操作的水文學法是目前研究方法的首選,而現有水文學法普遍存在區域適用性問題,方法選取不慎會造成計算結果不合理。因此,未來應加強能適用于不同空間的水文學法研究[10]。
3 研究模式
結合河流生態資產的研究成果[13],筆者提出了河流EWRs的研究模式,如圖3所示:
3.1 生態水文數據的觀測與計算
依托原型觀測技術,實施全流域水文、水力、水質、剖面生態、水生生物、河岸植被、河岸土壤等生態水文數據的觀測,并結合流域的社會經濟和水文資料,分析生態水文特征,并反演生態水文過程,為估算EWRs提供數據支撐。
3.2 河流分區及生態水文模擬
隨著數字信息和監測技術的持續迅猛發展,推動了將實地考察、定位觀測等傳統方法與GIS、RS、GPS等高新技術相結合,并通過計算機數值模擬方法建立具有統一物理機制和流域特色的分布式生態水文模型。目前相關的熱點研究包括EWRs數據庫與決策支持系統的構建、EWRs的數字仿真與可視化實現等方面,以動態地顯示河流生態系統的各種生物過程、水文過程及其相互作用和空間演變規律;基于GIS技術和河流資產特性,對河流生態系統進行空間分區,確定不同子系統的EWRs;選擇年際、年內、月內等不同的時間尺度和流域、河流、河段、斷面等不同的空間尺度,開展EWRs的時空對比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三維景觀模型、生態足跡法等各種數學方法對河流EWRs進行動態模擬與仿真計算。
3.3 EWRs的演變規律和驅動機制研究
河流EWRs具有時空變異性[10],目前關于河流EWRs的演變規律和驅動機制研究較少。隨著人們對河流生態系統認識的不斷深入,基于水循環的驅動機制研究逐漸增多。近幾年,研究人員開始結合全球氣候變化與人類活動的影響對EWRs展開研究。河流EWRs估算的核心是水分-生態相互響應關系、河流生態與水循環的互動-適應性機制。因此,開展EWRs的演變規律與驅動機制研究宜從河流的生態水文過程入手,主要包括EWRs的不確定性研究,水生生物的生存條件與水流條件的響應關系研究,變化環境下河流生態資產的演變趨勢研究,自然-社會二元水循環的驅動機理研究,不同時空尺度下土地利用方式對水循環和河流生態的作用研究,多重脅迫下河流生態系統的受損與修復機理研究等。
3.4 河流生態資產與EWRs的關系研究
人類從河流中獲取的各項服務可用價值量化,即為河流生態資產。當前研究更多關注河流生態系統對人類的經濟價值,而較少考慮河流的生態支撐功能[13]。河流生態資產的識別是開展EWRs評估的基礎,筆者建議根據河流的屬性和類型,從不同時空尺度上對河流生態資產開展層次化的辨識,并根據河流保護價值的大小和受威脅程度確定各類資產的優先級別。水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河流的正常生態過程,造成生態功能的損失和紊亂。河流EWRs短缺的損失價值可用對應的河流資產的缺損值進行評估。最后,根據自然流量情勢與水生生物生長繁殖的響應關系,確定河流資產各個目標與EWRs各項組分或要素的關系,并將其描述成一個概念模型。值得注意的是,當某個EWRs要素與幾個河流資產目標同時存在聯系,且其中一個目標又起著關鍵的限制作用時,就將這個目標視為“控制目標”,重點考慮EWRs要素與“控制目標”的關系。
3.5 河流EWRs的計算
根據觀測和模擬的生態水文數據及河流生態資產與EWRs的概念關系模型,采用適宜的EWRs計算方法,確定各河段不同生態水文季節具有量-水質兩重屬性的EWRs閾值范圍,以維持河流生態系統的整體健康。河流EWRs的計算應遵循以下原則:①多功能需求協調原則:對各生態環境功能在不同的時段和河段下的相對重要性進行加權處理,以確定各功能的優先級別,采用主功能優先、各功能協調的原則依次計算EWRs。②時空匹配原則:計算的EWRs應具有季節和年際的豐枯變化特征,并符合天然徑流的空間變化規律。③兼容性原則:對有兼容性的EWRs,以最大值為最終計算結果。④流域整體優化原則:兼顧河流上、中、下游的徑流特性和EWRs,對全河段的水資源進行綜合優化和科學配置,以使各河段都能健康發展。⑤效率最優化原則:EWRs應盡量使水資源的利用效率達到或接近最優,以減少水資源的不必要浪費。
3.6 生態流量預警與生態調度
根據生態水文節律,對計算的EWRs設立不同的預警值,如將適宜EWRs下限值和最小EWRs分別設為黃色和紅色預警值,以指導河流的調度管理。構建EWRs的危機管理機制,當河流的來水量<預警值時,河道的取水和排污管理進入非常狀態,水庫或湖泊則實施生態調度方案,通過下泄適宜的水量滿足EWRs。此外,還應研究生態價值的補償機制,預警線以下的水量,其生態價值要遠高于常規狀態的水量。對于生態調度模型,可以計算的EWRs為目標函數或者約束條件,并采用數學優化方法進行求解,得出適宜的生態調度方案,以協調生態用水與人類用水的關系。值得注意的是,計算的EWRs并非都是完全的科學合理,應對其生態效果進行監測,并根據監測結果分析其合理性,然后做出適當改進。此外,計算的EWRs也可能不利于水庫的調度操作,需要結合各項約束條件綜合權衡和優化,進而得到適宜的生態流量過程線或EWRs調度圖。
4 結語
綜述了1940s以來河流EWRs在理論和方法研究中的一些熱點問題及關鍵技術,提出了計算河流EWRs的研究模型。未來應加強以下研究:①基于河流健康理論的EWRs內涵辨識研究,綜合考慮水量、水質、時間、空間、閾值等屬性。②構建跨學科的EWRs理論體系,實現水動力學、水利工程、水文學、水力學、地理學、生態學、經濟學等學科的交叉發展。③在EWRs的計算方法上,一方面整合各種方法或模型的優點,開發集成的軟件平臺,從不同側面綜合評估EWRs,另一方面探索基于水文循環過程的EWRs驅動機制和演變規律,研究不同時空下的適宜計算方法。④結合模擬仿真與3S等高新技術,不斷發展和完善EWRs的評估模型,并將其計算結果可視化和人性化地展現。
參考文獻
[1]
王西琴,劉斌,張遠.環境流量界定與管理[M].北京: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10.
[2] ACREMAN M,DUNBAR M J.Defining environmental river flow requirements——A review[J].Hydrology and Earth System Sciences,2004,8(5):861-876.
[3] ALCZAR J,PALAU A,VEGAGARCI A C.A neural net model for environmental flow estimation at the Ebro River Basin,Spain[J].Journal of Hydrology,2008,349(1/2):44-55.
[4] MAZVIMAVI D,MADAMOMBE E,MAKURIRA H.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flow requirements for river basin planning in Zimbabwe[J].Physics and Chemistry of the Earth,2007,32(15/18):995-1006.
[5] CUI B,LI X,ZHANG K.Classification of hydrological conditions to assess water allocation schemes for Lake Baiyangdian in North China[J].Journal of Hydrology,2010,385(1/4):247-256.
[6] 康玲,黃云燕,楊正祥,等.水庫生態調度模型及其應用[J].水利學報,2010,41(2):134-141.
[7] 孫濤,徐靜,劉方方,等.河口生態需水研究進展[J].水科學進展,2010,21(2):282-288.
[8] 劉靜玲,任玉華,楊志峰,等.流域生態需水學科維度方法研究與展望[J].農業環境科學學報,2010,29(10):1845-1856.
[9] LI C W,KANG L.A new ecological flow assessment method based on spatial-temporal variability and transferability[J].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2014(522/524):791-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