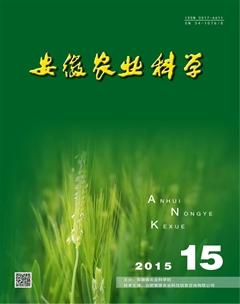土地利用規劃中公眾利益的弱化機理及其實現路徑
甘建文
摘要
以土地利用規劃編制和實施過程中利益相關者分析為切入點,通過分析各個利益主體的利益目標和行為選擇,探討公眾利益被削弱的過程機理,找出影響公眾利益實現的障礙因子。據此提出實現公眾利益保護的路徑:構建權利框架,提高公眾參與的效力;搭建第三方組織介入式參與平臺,實現公眾利益代表的多元化;成立地方土地利用規劃委員會,確保利益協調到位。
關鍵詞 土地利用規劃;公眾利益;弱化機理;實現路徑
中圖分類號 S-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517-6611(2015)15-289-02
伴隨著公民意識的增強,土地利用規劃的屬性由技術管制逐漸轉向公共政策。土地利用規劃作為一項公共政策安排,實際上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結果,要增進帕累托效率,必然要充分考慮公眾的利益,這也是由我國土地所有產權制度決定的[1]。
自2002年來,為了保護公眾的利益,在新一輪的土地利用規劃修編過程中公眾參與已有所體現。國家要求地方摒棄以前只有政府官員和專家參與的封閉式的“高層規劃”模式[2],要求規劃團隊實地調查,了解公眾的意愿和實際訴求。然而,由于公眾參與的主體、相關的制度保障和決策機制存在不足,公眾的集體意志難以上升到公共決策層面,公眾的利益容易被邊緣化。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如何在新的規劃方案編制過程中保護公眾的利益,對于提高規劃的權威性和執行力具有重要意義。
1 土地利用規劃利益相關者
1.1 利益相關者管理理論
1984年美國經濟學家弗里曼(R. Edward Freeman)在《戰略管理:利益相關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一書中,明確提出了利益相關者管理理論。隨著該理論的深入,利益相關者分析成為了人們制定戰略決策的常用工具之一。隨著利益相關者管理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該理論在公共管理中的應用逐漸興起。
1.2 土地利用規劃中的利益相關者分析
土地利用規劃涉及的利益相關者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官員、意圖用地者、公眾代表、公眾、規劃者、專家評審人,該研究分析了各個利益主體在土地利用規劃編制、決策、實施過程中的利益目標、行為選擇和角色擔當。
1.2.1
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的利益目標是實現土地的經濟、社會、生態可持續發展。在土地利用規劃過程中利用規劃管制權,通過綱領、制度、文件、指標等提出地方土地利用規劃的方向要求,下達約束性指標等剛性指標和指導性指標等彈性指標,實現對地方政府的總體控制。中央政府提出的要求對編制土地利用規劃方案既有宏觀指導性,又有強制性,是地方制定土地利用規劃的“指揮棒”。
1.2.2
地方政府。在“地方分肥”和“分灶吃飯”的分稅制下,地方政府作為有自身目標函數的公共經濟人,其根本的利益目標是地方財政收入的最大化。具體是要落實中央政府的要求,同時體現所在城市的發展計劃,滿足規劃年度內重大項目的用地要求,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地方政府的發展計劃是土地利用規劃的總綱領。
1.2.3
地方政府官員。在實際操作中,地方政府代表的公共利益往往容易被地方政府官員的私人利益掩蓋。地方政府官員利用權力資本,或通過主動政治創租,或受意圖用地者的影響,導致地方政府的經濟發展計劃被當權者凌駕。當有利益驅動的時候,他們利用政治權威加強對土地利用規劃的影響,有“一指定江山”的可能。在土地利用規劃中,地方政府官員往往充當“大喇叭”的角色。
1.2.4
意圖用地者。意圖用地者的利益目標是利潤的最大化。當有項目需要用地或者想通過變更規劃來實現更高利潤時,他們會通過動用自己的社會資本來影響規劃,使用的主要手段是通過利益輸送等方式與決策團體政治結伴。意圖用地者是地方政府背后最大的利益集團,在土地利用規劃中扮演“幕后推手”的角色。
1.2.5
公眾代表。
公眾代表既有反映群眾意見、為群眾代言的公共責任,又兼有為“功成名就”而討好上級的個人利益。他們善于為上級官員做群眾工作,當地方政府未能兌現公眾利益時,公眾代表則需要幫助地方政府開導、安撫甚至威脅、綁架群眾。在土地利用規劃中,公眾代表往往扮演“傳話線”的角色。
1.2.6
普通公眾。普通公眾的利益是提高土地利用的持續收益水平。但普通公眾因自組織化程度不高、公民參與渠道不健全、缺乏制度供給以及公民自身“搭便車” 和從眾心理的影響,使得公眾在決策行為的表現上屈從外部意志,很容易放棄意見的表達[3]。他們的利益往往不能有效表達,即便表達了也難以引起足夠重視和關注。公眾的意志甚至會被某些公眾代表、地方政府官員利用,成為其實現自身非法利益的耙子。普通公眾在土地利用規劃中扮演“幕后路人”的角色。
1.2.7
規劃者。規劃者是土地利用規劃方案的編制者,他們既想要想辦法落實國家的硬性指標,又要體現地方政府的經濟發展計劃,遇到地方政府官員干預時又要滿足部分地方官員的要求,還應該充分表達公眾的意志。在土地利用規劃方案編制項目外包的形式下,地方政府官員的利益往往會被規劃者重點考慮,優先實現。即便在土地利用規劃實施過程,如遇到有地方政府關于提出變更規劃,規劃者也需要為地方政府官員的規劃尋找正確的依據,使得規劃變更合情、合理、合法。規劃者在土地利用規劃中充當協調者。
1.2.8
專家評審人。專家評審人主要審核方案技術上是否科學可行、內容上是否與中央政府的要求和約束指標沖突、形式上是否清晰可讀。在評審會上,專家往往不作原則性修改。
2 土地利用規劃中公眾利益弱化的過程機理
以上分析表明,中央政府的命令和指標因為具有強制性,所以能很好地被地方政府、規劃者落實。另外,因為中央政府有方案的審批權和監督權,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乃至最終的方案編制者的管制效果沒被弱化。而由于地方政府官員存在創租、尋租行為且缺少必要的監督,受意圖用地者影響的地方政府官員利用自身的話語權,強力作用于土地利用規劃。就在此過程中,當公眾利益與官員的個人利益相沖突時,公眾利益往往被忽略。另外,由于公眾代表可能存在片面聽取部分公眾意見、選擇性反映群眾利益等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行為,公眾的利益訴求在公眾代表層面上被弱化。最后,由于規劃者本身也存在討好地方政府官員的公司利益,沒有真正起到協調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和凝聚社會共識的作用,最終導致最沒有發言權的公眾的利益被埋沒。因而,普通公眾的利益訴求在地方政府官員強力作用、公眾代表逆向“代議”、規劃人員選擇落實3個通道上被削弱,公眾在實際的土地利用規劃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公眾的利益在最大程度上被邊緣化了。
土地利用規劃過程中公眾利益受損隱藏著公眾利益表達機制不充分、公眾參與權利體系不完善、規劃主體工作不到位等深層機理。在土地利用規劃的實踐中,由于國家賦予公眾的權力不充分,導致公眾參與土地利用規劃的權利難以被重視。公眾的話語權與地方政府官員的話語權嚴重不對等,導致公眾的利益甚少能夠最終在規劃方案層面上得到反映。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公眾的權力未能受到法律制度的重視,公眾反而成為規劃實施的受害者[4]。
在土地利用規劃過程中,公眾的意志表達只有群眾本身、公眾代表2個主體,民眾意愿反映渠道的狹窄,導致公眾利益表達的機制不完善。由于受公眾代表個人利益的影響,公眾的真實意見很可能被公眾代表歪曲、利用,導致公眾參與的不全面。另外,普通公眾因為自組織化和社會化程度較低,所擁有的組織資源、人力資源和社會資源較小,因而公眾的意志很容易被官員的意志侵蝕,導致公眾意志不能很好地被實現。因而,安排多元的利益表達渠道,創新代議主體并提高公眾自組織化程度有利于全面反映群眾意見。
目前土地規劃團隊并不是一個公共部門,并不完全代表公眾意志,而是兼有私人利益的經濟部門。使得土地利用規劃還停留在“精英規劃”、“封閉規劃”、“高層規劃”的黑箱操作中,并沒有營造公開透明的利益表達氛圍,更沒有主動進行廣泛的試驗,形成“自下而上”的規劃思路。
3 土地利用規劃中公眾利益的保護路徑
3.1 構建權利框架,提高公眾參與的效力
法律法規是保障公眾有效參與土地利用規劃的前提,也是確保依法有序參與的必要條件。具體來說,土地利用規劃過程中應重點實現公眾以下幾個權力:
(1)話語權。在征求意見階段,政府要營造一個民主、平等的對話氛圍,讓公眾敢于真實表達利益訴求和傾訴意見。公眾提出保密申請時,需要對公眾的話語進行保密。
(2)論證聽證權。在初步的規劃方案出來后,公眾有權要求召開論證聽證會,就方案是否合理、存在的問題、改善的意見等表達自己的意見。而且,在最后專家評審驗收階段,公眾有權參與專家評審過程的聽證。
(3)同意通過權和否決權。通過這2項權力來實現公眾充分的決策權。規劃方案要獲得通過,必須經規劃范圍內2/3的公眾表決通過,并在意見書上簽字。公眾也可以對規劃方案行使否決權,只要規劃范圍內有1/3以上的公眾反對該規劃方案,則該方案需要重新進入聽證階段。
(4)選擇權與罷免權。如果在土地利用規劃過程中,公眾感覺到規劃人員不能很好地落實自己的合理意見,并且不能就某些不能達成的訴求做出合理解釋,在提交可靠證據后可以罷免規劃人員,要求政府重新選擇規劃隊伍,以保障自己的利益。
3.2 搭建第三方組織介入式參與平臺,實現公眾利益代表的多元化
實現在參與主體的多樣性,要尤其重視第三方組織的作用,這更有利于公眾參與到規劃中來并且能夠更有力的表達公眾的意見。獨立的第三方組織是非營利性的,有效避免了出現類似地方政府官員綁架規劃者的現象。在土地利用規劃中,第三方的專業知識能力能夠提升公眾的參與能力,影響公眾參與的方式,提升參與的效率,提高公眾話語的影響力。第三方組織還可以通過有效提高公眾的組織化程度,而組織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擴大公眾的參與優勢,通過影響決策,將大大提高公眾利益的實現程度[5]。另外,拓寬意愿表達的渠道,要進行理性的溝通,這依賴于第三方組織培育社會聯系交流的網絡、教育公民并提供規劃信息、鼓勵獨立地對以規劃范圍內所在地為基礎的項目進行反思[6]。
3.3 成立地方土地利用規劃委員會,確保利益協調到位
針對現有規劃者對各方利益協調不到位的情況,參考美國的經驗,成立地方土地利用規劃委員會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可能路徑。土地利用規劃委員會可以由規劃者、專家和社會公眾等組成,獨立于地方政府及其官員。土地利用規劃委員會的成立,打破了原有單一的“代議制”的代議決策和“首長制”的個人決策體系,通過委員會內部人員構成體系的優化完善規劃的治理結構。此外,成立地方土地利用規劃委員會還可以最大程度調動公眾參與的積極性,把碎片化的個人監督轉變成有組織的集體監督,從而保證公眾的利益與其他利益集團的利益在同一平臺上高效運轉。
參考文獻
[1]
吳未,黃賢金.土地利用規劃中公眾利益的價值取向[J].中國土地科學,2005(1):17-22.
[2] 段建南,胡瑞芝.縣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修編試點工作方法和技術創新思路[J].國土資源導刊,2004(2):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