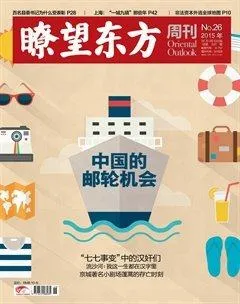京城著名小劇場蓬蒿的存亡時刻
陳莉莉

蓬蒿劇場上演的形體劇《我要安樂死》
最近5年里,每逢夏天,南鑼鼓巷都會有一個戲劇節。主辦者和出資人是王翔——蓬蒿劇場創辦人。
蓬蒿劇場就在南鑼鼓巷附近的東棉花胡同,四個白色字體嵌在正方形的藍色鐵皮上,與房屋幾乎等高。
黑色T恤上印著白色的“有”或者“冇”,年輕的面孔們正在彩排。這是中央戲劇學院戲文系2012級《戲劇構作》課集體項目。
前一天,這里上演了中國、以色列合作的《雪夜》。端木蕻良的這部小說,首次以戲劇的形式表現出來。
上午王翔是牙科診所的醫生,下午跑到東城區當起了場主。晚上8點多,在別人的提醒下,他意識到自己還沒吃晚飯,但要“趕緊去申請北京市文化局的一筆幾十萬元的項目基金”。

蓬蒿劇場咖啡廳及天臺外景
之所以被定義為小劇場,主要看座位數——通常300座以下,而小中之小、座位數少于100的,又稱為黑匣子劇場。
德國柏林世界藝術文化中心原藝術總監柯漢思曾評價說:“蓬蒿劇場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已經超過了一些大劇院和大劇團。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劇場?如果到了蓬蒿就明白了。”
可眼前,劇場租約即將到期,2000萬元的資金缺口還沒著落。
70萬元支撐的有意思人生
1985年的一部話劇作品《和氏璧》,讓牙醫王翔被戲劇的魅力感染。他認為“戲劇是藝術的最高表現形式以及能力”,與電影不一樣,“人與人之間需要面對面的相遇”。
結果一直到2008年,在北京奧運會的氛圍之下,他終于簽約了東棉花胡同35號一個6戶人家的四合院。
周圍遍布首都劇場、國家話劇院實驗劇場、中戲逸夫劇場、中戲黑匣子小劇場、中戲北劇場等劇場。“作為城市的中心空間,要有自己的文化。”王翔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那時北京最熱門的三個小劇場是人藝實驗劇場、東方先鋒劇場、朝陽9個劇場,都有國營色彩。
用120萬元個人資金進行保護性改造之后,蓬蒿劇場正式建成。
四合院前后共400多平方米、110個座位,主要空間分為劇場、咖啡館。重頭是戲劇演出,咖啡館用于舉辦沙龍、研討會等。
注冊時他曾想成為民營非營利組織,“但是對于戲劇類文化組織沒有這樣的細分”,蓬蒿劇場只能是“企業”性質。
7年過去后,房租從當初每年的24萬元,經過30萬元、60萬元,漲到了93萬元,還有每年作品制作費四五十萬元,10多個員工的薪酬三四十萬元,水電及辦公成本二三十萬元等。
但是開業至今,每年最低30萬元、最高50萬元的票房收入一直沒什么變化,“這是蓬蒿劇場唯一的收入。”王翔說,因為不走商業路線,“每年需要補貼70萬元”。
蓬蒿劇場80%的劇目不需要交付場租。或采用場制合一形式,由劇場投資、出品;或采取劇組制作、劇場監制,然后對票房分賬。
這70萬元補貼來自王翔的三個牙科診所,“我有兩個診所在西城區,一個在海淀區。一年流水有200多萬元,利潤全部補到了蓬蒿劇場。”王翔說,“這倒也是一個有意思的人生。”
蓬蒿劇場的鄰居、北京圓恩空間執行長劉文華對本刊記者說:“很多人說蓬蒿劇場是北京的驕傲,我卻認為是一種‘羞辱。70萬元,不過是700個人每人拿出1000元、7000個人每人拿出100元。現在卻要王翔獨自支撐。”
前些年,因為牙醫們聯合抗議,王翔才舍得拿出60多萬元,為診所添置了一臺新機器。
區政府出手
2010年,時任東城區交道口街道工委主任的李鐵生找到王翔,提出想做一個吸引游客、提升旅游品質以及精神生活品位的活動。第一屆“北京·南鑼鼓巷戲劇節”當年舉辦。
這一年,作為主辦方的北京市東城區政府支持了10萬元。2011年是80萬元、2012年120萬元、2013年150元,2014年原本預算180萬元。
“區政府看到了戲劇節的效應。除了孟京輝的青年戲劇節外,南鑼鼓巷的戲劇節可以說是中國第二大戲劇節,有那么多國際舞臺劇組織都來參加。”王翔說。
不過,2014年區政府縮減開支,投入猛降至50萬元,這時距戲劇節開始只有兩個月。而不遠處的民間劇場木馬劇場也搬離北京,讓王翔頓生“孤單無助”之感。
老一輩藝術家藍天野、王育生、朱琳、童道明、羅錦鱗等聯合發起了《支持第五屆“北京·南鑼鼓巷戲劇節”倡議書》,王翔也發起了“眾籌”。前者因蓬蒿劇場的“企業”性質,不能接受捐贈;后者收效并不顯著,一共籌得60萬元。
為了讓戲劇節如期舉辦,王翔準備賣掉翠微路附近的房子。結果接到新東方英語學校副校長徐小平的電話,徐小平拿出了70萬元。
贊助人的感謝名單中,除了徐小平,還有一些老藝術家和王翔牙科診所的同行。
“今年的戲劇節,因為資金不夠,原本不可能舉辦。但東城區政府想到一個折中的辦法,把劇場的一部分改為圖書館,同時租場地供街道退休人員跳舞,一年補償租金45.5萬元,租了5年。”王翔說,“一個區級政府能做到這樣,真難為他們了。”
2000萬元的可能性
雖然租房合同簽到2016年8月,但房東想在2015年底就結束合同。這處院子市場評估價3000萬元,王翔衡量了自己能動用的全部個人資產,“只有1000萬元”。
要么發動朋友買下房產,租給王翔;要么找到企業家購買房產,再建立租賃關系;要么高息貸款。
王翔說,自己沒想過更多,“只是經濟的問題,不管怎么樣,我一定會保住它”。
他有些固執,絕不考慮搬遷到房租便宜的地方。因為“如果在一個城市的中心空間,這個劇場都無法生存,到了邊緣地帶肯定就夭折了”。
東城區政府也希望能有所作為,但蓬蒿劇場既不是事業單位,也不是民營非營利組織。
“想明白,去堅守”,是王翔2015年6月5日在第六屆“戲劇節”上的致辭主題。它被做成了易拉寶,白底黑字,瘦瘦長長地放在劇場里。
劉文華有些忿忿不平:“是作為首善之地、文化中心,我們就看著一個裝了6個心臟支架的牙醫獨立支撐著中國最好的獨立劇場和最前衛的國際戲劇節,享受著豐富多彩的戲劇大餐,卻難有貢獻,于心何忍?”
蓬蒿劇場民間建設、民間經營、正式獲得社會公演資格的第一個獨立劇場,這些年來,上演200多部作品、2000多場戲,獨立出品了20多部戲。
“北京注冊的民間獨立小劇場不到10個,上海1個,其他城市如重慶、成都、武漢等一個都沒有。”這是2013年王翔調研的結果,“2014年北京地區增減持平,其他地方沒有增加。”
2010年2月,北京市東城區政府成立了戲劇建設促進委員會,又出臺了“關于戲劇發展公益補貼資金管理辦法”、“關于戲劇產業發展引導資金管理辦法”等政策。
盡管政策持續不足,但那時王翔真的感覺“文化發展的春天來了”。
蓬蒿劇場并非獨自面對困境,中國非營利性小劇場的生存境況約略如此。王翔覺得,目前阻礙戲劇文化發展的主要瓶頸在于劇場數量,如果沒有國家級財政立法層面的政策支持,經營性質不能變更為非營利,數量很難上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