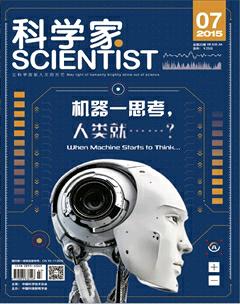撇不開的農藥
《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4年我國糧食再獲豐收,實現“十一連增”。全年糧食產量60710萬噸,比上年增加516萬噸,增產0.9%。糧食連年豐收,確保了國人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不僅對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的平穩運行發揮著“定盤星”的作用,也為世界糧食安全貢獻了中國力量。
中國用占世界約8.6%的耕地養活了約占世界20%的人口。在這則讓國人引以為傲的數據背后,還有這樣一則數據:中國在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上,化學農藥的單位面積平均用量高出世界平均用量的2.5倍-5.0倍。
該數據的呈現不免引起大眾對農產品質量安全和食品安全的隱患及由此帶來水體污染和土壤污染的擔憂。
一邊是吃飽、吃得安全,一邊是環境污染、可持續發展,其中的利害輕重需慎重權衡,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農藥——化學農藥——是導致問題的關鍵因素之一。
農藥就是毒藥?
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世界每年至少發生50萬例農藥中毒事件,死亡11.5萬人。
不論這些案例中導致人們農藥中毒的原因是什么,這些數據足可以刺激公眾的心理。在很多人心中,一直把農藥與毒藥等同起來,認為所有農藥都是高毒、高殘留的。那么農藥的毒性是如何衡量的?
衡量農藥毒性的大小,通常是以致死量或致死濃度作為指標的。致死量是指人、畜吸入農藥后中毒死亡時的數量,一般是以每公斤體重所吸收農藥的毫克數,用毫克/公斤或毫克/升表示。急性程度的指標,是以致死中量或致死中濃度來表示的。致死中量也稱半數致死量,用符號LD50表示,一般以小白鼠或大白鼠做試驗來測定農藥的致死中量,其計量單位是每公斤體重毫克。“毫克”表示使用農藥的劑量單位,“公斤體重”指被試驗的動物體重,體重越大中毒死亡所需的藥量就越大,其含義是每1公斤體重動物中毒致死的藥量。中毒死亡所需農藥劑量越小,其毒性越大;反之所需農藥劑量越大,其毒性越小。
根據農藥致死中量的多少可將農藥的毒性分為:劇毒、高度、中度、低毒和微毒五種。所以不是所有的農藥都是高毒農藥,農藥等于毒藥也必然是一個錯誤的結論。
它是如何毒害我們的?
農藥進入人體主要有三種途徑:皮膚、呼吸道和腸道。
對于農藥的生產、銷售和使用人員來說,皮膚吸收是農藥最常見的進入人體的途徑。大部分農藥都可以通過完好的皮膚吸收,而且吸收后在皮膚表面不留任何痕跡,所以皮膚吸收通常也是最易被人們忽視的途徑。不同農藥對皮膚的滲透能力不同。有的農藥是液體,且含有某種有機溶劑,比固相農藥和水相農藥更易于和更快于滲透到皮膚內部。一旦農藥進入真皮,到達皮膚的毛細血管,就會很快地進入血液,可在幾分鐘內就產生不利于人體健康的后果。
另外,在噴灑和熏蒸農藥,或是使用一些易揮發的農藥時,農藥都可以經過呼吸道進入人體。直徑較大的農藥粒子不能直接進入肺,而是被阻留在鼻、口腔、咽喉或氣管內,并通過這些表面黏膜吸收。直徑為1微米-8微米的農藥粒子可以直接進入肺內,并且快速而完全地被人體吸收。吸入農藥的量隨呼吸的次數和呼吸深度不同而變化。成人休息時呼吸次數每分鐘約14次,而在劇烈運動之后,可達到每分鐘25次到30次。
消化道吸收是農藥進入人體的一種常見途徑。各種農藥都可以通過消化道吸收進入人體,主要的吸收部位是胃和小腸,而且通過此類吸收方式吸收的農藥,大多吸收的較為完全。經消化道吸收進入體內的農藥劑量一般較大,中毒情況相對嚴重。一般消化道吸收的農藥主要是食物和飲用水中殘留的。
根據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的科研人員對人體污染量的調查測定:在密閉作物田間(棉田、保護地黃瓜等)采用大容量噴霧方法噴灑農藥,約有2%的藥劑沉積到施藥者身上,施藥人員皮膚污染的農藥量為呼吸道吸入量的1000倍;除人為因素外,經消化道和呼吸道中毒的機會很少,而皮膚吸收中毒則占中毒人數的90%以上。
觸目驚心的數據,不免引起人們的擔憂,但其實大可不必因此恐慌。
根據農藥的定義,它是用于預防、消滅或者控制危害農業、林業的病、蟲、草和其他有害生物以及有目的地調節植物、昆蟲生長的化學合成或者來源于生物、其他天然物質的一種物質或者幾種物質的混合物及其制劑。
冷靜分析農藥的定義,我們就能意識到,其實農藥本身并不可怕,它當然不是為了毒害人類而出現的毒藥,只是在使用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對人體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很多都是因為人為操作不當造成的。如農藥泄漏、誤服農藥,或是在高濃度的農藥生產車間工作及分裝和噴灑農藥的過程中錯誤操作造成的。
當然農藥中毒的案例中,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農藥殘留。
農藥殘留問題是隨著農藥大量生產和廣泛使用而產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農業生產中使用的農藥主要是含砷或含硫、鉛、銅等無機物,以及除蟲菊酯、尼古丁等來自植物的有機物。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人工合成有機農藥開始應用于農業生產。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化學農藥年產量近200萬噸,約有1000多種人工合成化合物被用作殺蟲劑、殺菌劑、殺藻劑、除蟲劑、落葉劑等。農藥尤其是有機農藥在農業生產中大量施用,造成了嚴重的農藥污染問題,也成為了人體健康的嚴重威脅。
為什么還有農藥殘留?
首先我們要弄明白一個道理,農藥殘留不等于農藥超標。中國工程院院士、茶學專家陳宗懋曾指出,“農藥殘留”和“農藥超標”是不同的概念,檢測出農藥殘留不等于就有危害。陳宗懋說,“就像去醫院體檢,通過對照標準值,才能知道指標是否正常。”
當然在農藥的使用過程中不排除一些農戶的不當操作。比如一些農戶為了殺蟲效果好、見效快,不講究用藥技術,一旦認為防治效果不佳,就加大藥量,結果致使病蟲害產生了抗藥性。當有了抗藥性的病蟲害又危害田間的蔬菜時,農戶會再次加大藥量來防治蟲害,如此惡性循環,蔬菜中的農藥殘留量就會大大增加。
但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片面地將農藥與毒藥劃等號。
農藥到底多重要?
近些年,食品安全問題不斷挑戰人們的想象力和心理底線,“農藥茶”“毒草莓”等事件都與農藥有關,由此公眾便患上了“農藥恐懼癥”,產生了 “能不能不使用農藥”的疑問。
農業部早在2012年5月就在其官方網站發布關于農產品農藥殘留及安全問答的文章,該文章指出,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耕地緊張的國家,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始終是農業生產的主要目標,而使用農藥控制病蟲害是必要的技術措施。農業部還引述相關研究指出,因為農作物病蟲草害引起的損失最多可達70%,通過正確使用農藥可以挽回損失40%左右。
農藥是人類科技發展的一種產物,更是一種進步的體現。農藥以其見效快、性質穩定、便于貯存、價格低廉等優點,促進了現代農業的發展。在1949年-1999年的50年里,我國的糧食產量由1029kg/hm2提高到了4439kg/hm2,農藥功不可沒。
農藥對于植物來說,猶如醫藥對人類一樣重要,身體出現了問題就需要相應的藥物有針對性的進行治療。只不過需要保證用量科學合理,只有規范安全用量和制定嚴格的管理制度才可以做到治病而不致病。
今年4月24日,經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以下簡稱《安全法》)。
《安全法》中明確規定,國家將對農藥的使用實行嚴格的管理制度,加速淘汰劇毒、高毒農藥和高殘留農藥。同時,法案禁止將劇毒、高毒農藥用于蔬菜、瓜果、茶葉和中草藥等國家規定的農作物。
截至目前,我國已對322種農藥、10大類農產品和食品規定了22933種非劇毒高毒農藥的殘留標準。不過,這個數據意味著,有兩萬多種非劇毒、高毒農藥仍可以使用,盡管其使用濃度和殘留量有嚴格限制。
相關專家也表示,首次寫入關于限制劇毒農藥和高毒農藥的內容,是帶有里程碑性質的。但是要真正做到以人為本,還要把化學農藥從農業生產中排除出去,禁止所有化學農藥在食品中使用。要在保證農作物產量不受影響的情況下,禁用化學農藥,就要加大對劇毒和高毒農藥替代物的研究。這也是《安全法》中所闡述的:“推動替代產品的研發和應用,鼓勵使用高效、低毒和低殘留農藥。”
農藥替代物的研究可以是保證未來農作物產量和降低環境污染的一個重要途徑。但是業內人士卻認為替代農藥研究屬于科技界的空白,在行業內做植物保護研究工作的人善于用化學農藥,通過修改農藥配方來保護不同植物;做土肥方面研究的人員,也只是單純地研究化肥,很少有人去研究農藥替代物。
農藥替代物的研究雖不容樂觀,但是在沒有找到明確的替代物的情況下,生物農藥也許是一條最為明智的選擇,只是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實現生物農藥的效用。
生物農藥
逆勢而漲的生物農藥
“2014年,全國農藥行業843家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為3008.41億元,同比增長7.5%,利潤總額為225.92億元,同比下降1.2%,是近6年來首次出現下降。其中化學農藥利潤總額下降3.6%,而生物農藥及微生物農藥逆勢強勁增長23.7%,形成兩極分化格局。國內隨著農產品質量安全重要性的顯現,綠色農產品的市場看好,生物農藥的應用出現強勁上升勢頭,井岡霉素、蘇云金桿菌、赤霉素、蠟質芽孢桿菌、阿維菌素、春雷霉素、白僵菌、綠僵菌等品種獲得越來越多的推廣應用,特別是國家對生物農藥實行政府補貼試點工作起到了示范推動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拉動了生物農藥的發展。生物農藥雖然出現了可喜的利潤增長形勢,但所占比例僅為10%左右,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專家建議要加大生物農藥研發投入,不斷開發出使用性價比高、一炮打響的產品。化學農藥落后發達國家幾十年,生物農藥不能再輸了。”
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農藥生產和使用國,每年遭受農藥殘留污染的作物面積約12億畝,其中40%污染嚴重,每年因蔬菜農藥殘留超標造成的外貿損失達10億美元。
鑒于此,生物農藥近些年關注度逐漸攀升。生物農藥主要來源于自然界中存在的、對農作物病蟲害具有抑制作用的各種具有生物活性的天然物質或其代謝產物。借助自然界生物相生相克的原理,生物農藥對人畜相對安全,與環境相容性較好,在世界范圍內已經逐漸成為農藥領域研究與開發的主流與方向,美國聯邦環保署新批準的生物農藥數量就遠遠超過常規農藥。
生物農藥的窘境
但即便如此,生物農藥發展仍是“叫好不叫座”,相關專家表示生物農藥是支撐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但在推廣過程中卻遭遇不少尷尬問題。
目前我國生物農藥登記品種只有40種,僅占全部農藥登記品種的3%;生物農藥年產量不到13萬噸,僅占農藥總產量的9%左右。生物農藥的藥效慢是制約生物農藥發展的一個根本原因。化學農藥的藥效達到80%屬于及格水平,而生物農藥藥效能夠達到80%的卻占少數,有些生物農藥的藥效甚至只有30%,并且用量要比化學農藥高得多。所以農戶為了立竿見影地殺滅蟲害,寧可違規使用高濃度、高殘留的化學農藥。
成本問題是生物農藥推廣中面臨的另一個問題。一些生物農藥的價格要比普通農藥貴出20%左右。比如200毫升的高毒殺蟲農藥氯氰菊酯售價只有10元,生物農藥的價格則為11.5元左右,比化學農藥的價格高出15%。單價高、用量多,農戶為了保證利潤多數還是會選擇化學農藥。
由于市場極難開拓,又是微利產品,已有大型生物農藥企業關停生產線,停止生產生物農藥,生物農藥科技成果和專利技術更難轉讓推廣。
不過相關專家指出,既然已經明確生物農藥既可以防治農作物病蟲害,又可以解決土壤健康修復這一世界難題,所以必須將生物農藥提升到國家戰略大計的高度,制定重大國策。
山東省科學院科技戰略研究所研究員呂兆毅曾說,“我國可以借鑒美國等發達國家,加快我國《農藥法》立法進程。同時,國家應將生物農藥作為防止農藥殘留、保障食品安全的治本對策,將發展生物農藥產業提升為重點扶持的食品安全戰略產業,作為食品安全源頭治理的關鍵行動。”
除了加快立法,我國還可以借鑒韓國相關政策,通過大幅度補貼農戶,間接促進生物農藥企業實現盈利,并逐步走向正軌。我國農業部近年來盡管已開展了低毒低殘留農藥示范補貼工作,但試點范圍和力度都比較有限。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最近對生物農藥實行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各補貼50%、免費發放、項目示范等辦法,取得了良好效果。
總之,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我們不能再為了吃飽飯、保供給而以犧牲資源環境為代價,采取過度開發農業資源、大量投入農藥等化學品這種飲鴆止渴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