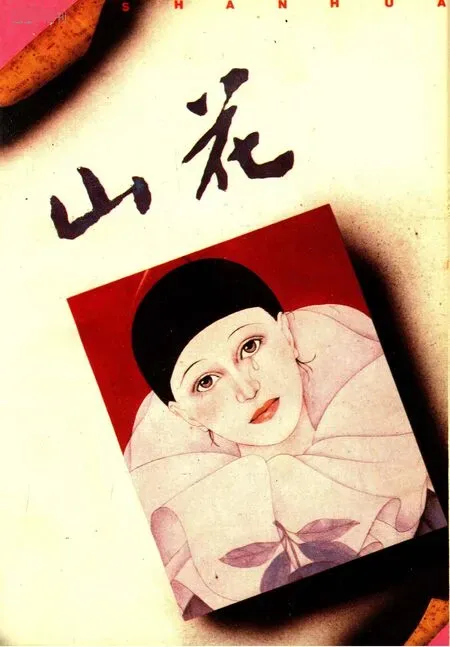杜甫與“喪家狗”
張東艷
杜甫自稱“喪家狗”的心理動(dòng)因是自居作用,自居作用在其詩歌中主要表現(xiàn)為兩方而:一是表達(dá)自己遠(yuǎn)大的政治理想或理想受挫的窘迫狀態(tài)時(shí),以孔子自居;二是表達(dá)對(duì)自己才華的高度自信或懷才不遇的失意時(shí),以屈原、賈誼、司馬相如、揚(yáng)雄、阮籍、嵇康、王粲等自居。
喪家狗的出處與含義
杜甫晚年曾兩次自稱“喪家狗”,一次是廣德元年(763年)冬,在《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諸公得柳字》詩中感嘆:“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一次是大歷四年(769年)在《奉贈(zèng)李八丈判官》一詩中又再次感嘆:“真成窮轍鮒,或似喪家狗。”“喪家狗”的典故來自于孔子。
孔子自認(rèn)為喪家狗的記載見于《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dú)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xiàng)類皋陶,其肩類子產(chǎn),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shí)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日:‘形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關(guān)于孔子自認(rèn)為喪家之狗,還見于《白虎通壽命》《論衡骨相》《孔子家語困誓》《韓詩外傳>。
“喪家狗”的含義,學(xué)界有兩種說法:一種認(rèn)為“喪”讀平聲,“喪家”為居喪之家,喪家狗為有死亡之事的人家的狗。如《史記集解》引王肅日:“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累然而不得意。孔子生于亂世,道不得行,故累然不得志之貌也。”又引《韓詩外傳》子貢把鄭人的話告訴孔子后,“孔子無所辭,獨(dú)辭喪家之狗耳,日: ‘丘何敢乎?…孔子認(rèn)為自己不敢承當(dāng)“喪家之狗”的評(píng)價(jià),日:“汝獨(dú)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槨,布席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qiáng)凌弱,眾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jì),是人固以丘為欲當(dāng)之者也,丘何敢乎!”這里“喪家之狗”指主人己死,但還想按主人原有的旨意做事的“狗”。孔子認(rèn)為此時(shí)王道衰,政教失,已經(jīng)無綱紀(jì),想做個(gè)這樣的“狗”也不可能了,以此喻流落失意,不受重用的人。另一種意見認(rèn)為“喪”讀去聲,錢鐘書先生《談藝錄》曾三次討論“喪家狗”,認(rèn)為“喪家”意為“無家”,喪家狗乃失去家園的狗。結(jié)合杜甫的思想和生平,本文采納第一種意見。
杜甫自稱“喪家狗”的心理動(dòng)因——自居作用
杜甫自稱為“喪家狗”,其心理動(dòng)因乃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xué)說中的自我防御機(jī)制的一種——自居作用。自居作用又譯作認(rèn)同、仿同作用等,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認(rèn)識(shí)到的人與人有情感聯(lián)系的最早的表現(xiàn)方式。
弗洛伊德認(rèn)為完整的人格結(jié)構(gòu)由三大部分組成,即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本能和欲望的體現(xiàn)者,遵循的是“唯樂原則”。“每個(gè)人都有一個(gè)心理過程的連貫組織,我們稱之為他的自我。”超我又叫自我典范,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從自我中分化和發(fā)展起來,遵循“至善原則”。自我經(jīng)常受到來自三方而的威脅:外部世界、本我、超我。它一方面設(shè)法滿足本我對(duì)快樂的追求;另一方面必須使行為符合超我的要求。“當(dāng)自我中有些東西與自我典范相符合時(shí),總是會(huì)產(chǎn)生一種狂喜的感情。而罪惡感(以及自卑感)也能被理解為是自我和自我典范之間緊張的一種表現(xiàn)。”弗洛伊德認(rèn)為自我為解決超我與本我之問產(chǎn)生的沖突,會(huì)使用心理防御機(jī)制避免危險(xiǎn)、焦慮和痛苦。自居作用是自我心理防御機(jī)制中的一種。
自居作用原指幼童在產(chǎn)生愛戀異性父親或母親的沖動(dòng)時(shí),將自己置身于同性父親或母親的地位,以他們自居,從而獲得替代性滿足。“當(dāng)一個(gè)孩子成長(zhǎng)起來,父親的角色由教師或其他權(quán)威人士擔(dān)任下去;他們的禁令和禁律在自我典范中仍然強(qiáng)大,且繼續(xù)發(fā)展,并形成良心,履行道德的稽察。良心的要求和自我的現(xiàn)實(shí)行為之問的緊張狀態(tài)被體驗(yàn)成一種罪惡感。社會(huì)感情在自我典范的基礎(chǔ)上通過與他人的自居作用而建立起來。”自居作用在人格的形成和發(fā)展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當(dāng)個(gè)體在現(xiàn)實(shí)中遭遇失敗,就將自己想象成幻想中的勝利者或崇拜的人物或與自己遭遇相似的人物,分享其成就與威嚴(yán),以減輕自身受挫后的痛苦或焦慮。
杜甫懷抱“致君堯舜上,再使風(fēng)俗淳”的偉大政治理想,一生中卻每每懷才不遇,報(bào)國(guó)無門,晚年漂泊荊湘,甚至于一家老小的溫飽都難以為繼。因而追求物質(zhì)滿足的本我和追求高尚人格,崇高理想的超我之間必然產(chǎn)生劇烈的沖突,從而使詩人產(chǎn)生種種焦慮。自我要緩解這些焦慮,就常常運(yùn)用自居作用來調(diào)節(jié),詩人于763年和769年兩次自稱“喪家狗”就是自居作用的典型表現(xiàn)。詩人晚年漂泊西南,不僅不得重用,連維持生活都要靠朋友的資助,其內(nèi)心的矛盾沖突可想而知。此經(jīng)歷與孔子周游列國(guó),道不得行,流離困窘的遭遇頗為相似,而孔子正是詩人的偶像,詩人以孔子自稱的“喪家狗”自居,有效緩解了本我和超我的矛盾沖突,舒緩了挫敗感,減輕了內(nèi)心的焦慮。
杜甫的自居作用在詩歌中的表現(xiàn)
人類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實(shí)際上是心理活動(dòng)的外化,可以作為對(duì)現(xiàn)實(shí)中被壓抑的欲望的一種補(bǔ)償。“詩人的心理沖突,構(gòu)成了詩歌創(chuàng)作的主要?jiǎng)恿Γ娙说亩嘀匦睦頉_突使他們永遠(yuǎn)有一種挫折感和焦慮感。心理上持續(xù)著嚴(yán)重失衡狀態(tài)。它要求滿足而又得不到滿足。這時(shí),詩歌成為詩人努力恢復(fù)心理平衡的一種方式。”自居作用向藝術(shù)家提供了托物言志、借題遣興的舞臺(tái)。在很多時(shí)候,藝術(shù)家是通過藝術(shù)創(chuàng)造中的自居作用來實(shí)現(xiàn)自己的情感寄托的。杜甫通過自居作用借題發(fā)揮,表達(dá)自己的政治抱負(fù),追求理想過程中受挫的失意,對(duì)自己才華的高度自信,等等,自居作用在其詩歌中主要表現(xiàn)為以下兩方面:
1.表達(dá)自己遠(yuǎn)大的政治理想或理想受挫的窘迫狀態(tài)時(shí),以孔子自居
杜甫服膺儒家思想尤其是先秦孔孟思想,不僅表現(xiàn)在忠君愛國(guó),還表現(xiàn)在對(duì)于孔子的言語、行事方式的崇拜和模仿。“自居作用就是一個(gè)人試圖按照另一個(gè)模特的樣子來塑造他自己的自我。”自我用自居對(duì)象的種種特點(diǎn)來充實(shí)自己,將對(duì)象“內(nèi)投”入自身中。杜甫在表達(dá)自己“致君堯舜上,再使風(fēng)俗淳”的政治理想,以及追求理想受挫時(shí)就常常以孔子自居。如“謬知終畫虎,微分是醯雞”(《奉贈(zèng)太常張卿垍二十韻》),在《莊子》中,孔子認(rèn)為自己就像甕中的醯雞,在這首給張垍的干謁詩中,困居長(zhǎng)安的杜甫也把赴試失敗的自己比作醯雞。至德元年(756年)在《送率府程錄事還鄉(xiāng)》一詩中杜甫稱“內(nèi)愧突不黔,庶羞以周給”,以忙于事務(wù),飲食無暇的孔子自居,“突不黔”語出《淮南子修務(wù)訓(xùn)》“孔子無黔突”。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在甘肅同谷居住不滿一月,因生活困難,只好南赴成都,作于途中的《發(fā)同谷縣》寫告別同谷的原因和場(chǎng)面,詩曰“賢有不黔突,圣有不暖席”,以四處奔走,忙得顧不上做飯的墨子和坐不暖席子的孔子自居,對(duì)自己漂泊凄惶的生活作自我寬解。大歷三年(768年),杜甫攜家離開江陵赴公安時(shí)作詩《舟出江陵南,奉寄鄭少尹審》留別老友,詩中表達(dá)了詩人道不得行打算像孔子一樣避世隱居,其中“東逝想乘桴”語出《論語·公冶長(zhǎng)》:“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大歷五年(770年),杜甫在長(zhǎng)沙舟中作詩《追酬故高蜀州人口見寄>懷念亡友高適,詩日“東西南北更論誰”,以東西南北人自稱。“東西南北人”語出《禮記·檀弓上》,孔子日:“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shí)也。”鄭玄注:“東西南北,言居無常處也。”后因以“東西南北人”謂居處無定之人。孔子自稱東西南北人,杜甫也自稱東西南北人,本質(zhì)上實(shí)以孔子自居。這年冬季,杜甫臥病湘江船上,作絕筆詩《風(fēng)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此時(shí)詩人貧病交加,異常窘迫,但詩中卻說“吾安黎不糝”,安于喝沒有一粒米的野菜湯。“黎不糝”語出《莊子讓王》:“孔子窮于陳蔡之問,七口不火食,藜羹不糝。”以上幾首詩中,杜甫都處于失意、困窘、落魄的生存狀態(tài)之中,遠(yuǎn)大的抱負(fù)和慘淡的現(xiàn)實(shí)之問的落差,使得詩人的自我常常在超我要求道德的至善和本我要求物質(zhì)的滿足的撕扯中煎熬,通過以孔子自居的方式宣泄了心理上的悲憤、壓抑,獲得了心靈的慰藉。
2.表達(dá)對(duì)自己才華的高度自信或懷才不遇的失意時(shí),以屈原、賈誼、司馬相如、揚(yáng)雄、阮籍、嵇康、王粲等自居
杜甫“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得到當(dāng)代名人的充分肯定:“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yáng)”(《壯游》),對(duì)于自己的才華高度自信,自稱“賦料揚(yáng)雄敵,詩看子建親”(《奉贈(zèng)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氣劇屈賈壘,目短曹劉墻”(《壯游》),自豪地以揚(yáng)雄、曹植、屈原、賈誼自居。
天寶五載(746年),35歲的杜甫懷著滿腔的政治熱情來到長(zhǎng)安,希望實(shí)現(xiàn)自己濟(jì)蒼生,安社稷的政治理想。第二年,玄宗下詔征求在野的賢才。杜甫滿懷信心地參加了此次考試。李林甫以“野無遺賢”為借口,使包括杜甫在內(nèi)的應(yīng)考者全部落選。杜甫在長(zhǎng)安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潦倒生活。天寶十載(751年),杜甫向玄宗獻(xiàn)了《三大禮賦》,終于引起玄宗關(guān)注,命其待制集賢院,但直到天寶十四載(755年)十月,才被授予河西尉的官職。杜甫懷著“會(huì)當(dāng)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抱負(fù),困守長(zhǎng)安十年,時(shí)常饑寒交迫,飽嘗人生的艱辛,最終卻得到這樣一個(gè)從九品的小官。這令期望“立登要路津”的杜甫大失所望,沒有就任,后又改任右衛(wèi)率府兵曹參軍。杜甫有著志在天下的人生信念和“致君堯舜”的偉大理想,并且為實(shí)現(xiàn)此理想做出了種種努力:參加科考,干謁權(quán)貴,向皇帝獻(xiàn)賦,等等。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頻頻受挫,杜甫常常感到失望、苦悶、迷惘,當(dāng)然也有牢騷。對(duì)現(xiàn)實(shí)感到失望的時(shí)候,詩人會(huì)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轉(zhuǎn)向古人,尤其是那些和自己遭遇相似的古人,通過自居作用,從他們身上獲得心靈的安慰,使自己壓抑的精神暫時(shí)得到緩解,同時(shí)獲得進(jìn)一步前行的力量。如“致君時(shí)己晚,懷古意空存。中散山陽鍛,愚公野谷村”(《贈(zèng)比部蕭郎中十兄》),以鍛鐵的嵇康自居,發(fā)泄進(jìn)士考試失利后,壯志落空,意欲歸隱的牢騷。“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敬贈(zèng)鄭諫議十韻》),“茫然阮籍途,更灑楊朱泣”(《早發(fā)射洪縣南途中作》),“至今阮籍等,熟醉為身謀”(《晦口尋崔戢李封》),以途窮痛哭、醉酒避禍的阮籍自居,表達(dá)現(xiàn)實(shí)中郁郁不得志,無路可走的迷惘。“永負(fù)漢庭哭,遙憐湘水魂”(《建都十二韻》),以苦諫的賈誼和因進(jìn)諫遭放逐的屈原自居,一方而感愧自己上疏救房琯未有所成,另一方而表達(dá)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的失望心情。“多病馬卿無口起,窮途阮籍幾時(shí)醒”(《即事》),“蒼茫步兵哭,展轉(zhuǎn)仲宣哀”(《秋口荊南述懷三十韻》),“去國(guó)哀王粲,傷時(shí)哭賈生”(《久客》),分別以抱病在床的司馬相如、途窮慟哭的阮籍、去國(guó)離鄉(xiāng)的王粲和傷時(shí)痛哭的賈誼自居,表達(dá)對(duì)時(shí)局紛亂的憂慮。“喪亂秦公子,悲涼楚大夫”(《地隅》),以王粲、屈原自居,表達(dá)晚年漂泊流徙,滯留江漢的悲涼心境。
綜上所述,自居作用作為自我的一種心理防御機(jī)制,有效安慰了杜甫人生旅途中遭受重創(chuàng)時(shí)受傷的心靈,成為其創(chuàng)作的一股強(qiáng)大動(dòng)力,推動(dòng)了詩人的創(chuàng)作。杜甫通過創(chuàng)作中的自居作用平復(fù)了失衡的心理。“一個(gè)人當(dāng)他不能通過自我本身得到滿足時(shí),就有可能從那個(gè)己從自我中分化出來的自我典范中尋得滿足。因而杜甫的自我用自居對(duì)象來代替自身最重要的成分,對(duì)象被置于自我典范的地位,表現(xiàn)在詩歌中就是常以孔子、屈原、賈誼、司馬相如、揚(yáng)雄、阮籍、嵇康、王粲等自居。這對(duì)我們進(jìn)一步探討杜甫的創(chuàng)作心理是一個(gè)有益的嘗試。